査建英笔下的弄潮儿 by 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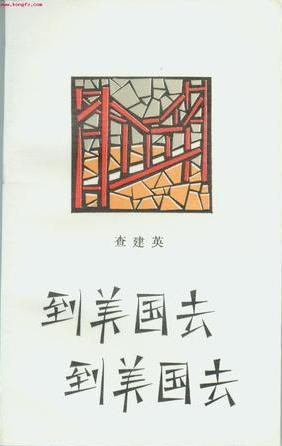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查建英/著
作家出版社
1991年
五年不见。
上一次见到作家査建英, 还是2006年。那时,她带着古根汉姆写作基金回到中国已经3年,每年在纽约和北京各住半年。
早在1995年,査建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非小说英文著作《中国波普》(China Pop)在美国出版,她描述和分析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该书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杂志评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还被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
1981年秋天,查建英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去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留学;1984年又拿着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英语硕士学位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在夏志清先生门下攻读比较文学,同门的有日后成为魏晋文学专家的唐翼明(历史作家唐浩明的兄长)。査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紧随其后。
旅居纽约、芝加哥、休斯顿之后,査建英和家人于2000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两年。此间査建英一直用中文为香港媒体撰写文章介绍北京,用英文向欧美介绍中国。近年的一些长文陆续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刊发,《读书》、《万象》也让她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字还乡”。
回到北京本来是为了新的写作计划,不料与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批“现象级”人物对谈,谈出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2006年5月在三联书店出版并迅疾畅销的访谈录,正是我五年前第一次采访査建英的缘起。
不见査建英的这几年,不时“见”她出现在《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席上。这是她获得“在场感”、参与国内公共讨论的重要途径。
除“写作个体户”之外,査建英另一个重要身份是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印度开了一个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就是中印比较,和中美比较很不一样”,査建英这八年来组织了大量中印比较的学术研讨,在纽约、北京和孟买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这位“地理文化决定论者”近年来格外关心的是,印度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殊途同归。
査建英1987年本来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口试,领了笔奖学金,说是要回中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革’小说”。临别前,时任比较文学系主任的萨义德曾疑惑地问:“你是不是真的还会回到我们这儿?”果不其然,査建英最后没有写出博士论文——夏志清先生或许有些失望,没有像研究自然辨证法的父亲査汝强那样走上治学之路,她选择了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写作——査建英自认为不适合做一个站在讲坛上的大学教师,“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再次见到査建英是2011年年底,她在美国出版的新著《Tide Players》(《弄潮儿》),刚被英国《经济学家》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该书集中采写了张大中、孙立哲、潘石屹、张欣和王蒙、张维迎等企业家与知识分子,试图立体描述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
于是,围绕着这五年的“见与不见”,我们再次一番畅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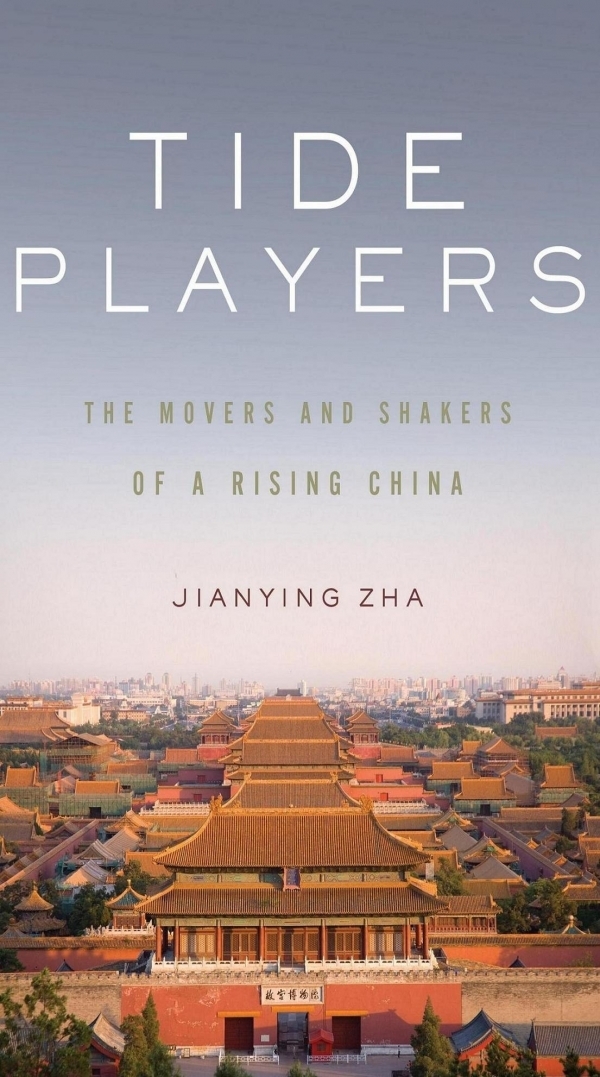
《弄潮儿》
( Tide Players :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
Jianying Zha/著
The New Press
2011年3月
访谈
Q=燕舞 A=查建英
弄潮儿
Q:《八十年代:访谈录》掀起热潮后,您更多地回归和介入国内思想文化界了。这几年在《纽约客》刊发的那些长文,都被国内网友第一时间主动翻译过来,像《纽约客》2010年11月8日封面头条那篇写王蒙的《国家公仆》。而2011年国内出版的《纽约客》前任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不少媒体将其排在年度图书评选榜首。描写中国最深入的非虚构作品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美国记者,这多少值得中国记者和写作者反思吧。
A:何伟是《纽约客》前些年的驻华记者,是专职记者,我是自由撰稿,跟他们没有长期合约。现在欧逸文(Evan Osnos)接任,他们都得一年内写几篇,我是没有的。最早,他们跟我约稿时,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让我改,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思路改,也不愿意由他们来给我定选题,我是一个天生的个体户,最后就变成自由撰稿了。
我2011年4月出的这本新书《Tide Players》(《弄潮儿》),还没有中文版。昨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碰见“东西网”和“译言网”的创办人赵嘉敏,他说我这本书在大陆全部刊发不可能,但他想组织翻译部分章节发表网络版,还说国内现在也有一些读者已经开始从网上的“苹果商店”(Apple Store)买书了,买那些国内买不到的书。
我这个集子里有三章是《纽约客》发表过的,但不是《纽约客》上发表的那个样子。比如写王蒙那篇,实际上《纽约客》删掉了将近一半,所以《弄潮儿》里面就长出来差不多一倍。《纽约客》只能是那么长,不可能再长了,我这几篇都是《纽约客》当期封面的头条,给的长度已经是最长的了。
其他几篇是没发表过的,就是专为这本书写的。《弄潮儿》是一个集子,基本上是人物系列,所以给《纽约客》的那几篇人物我收进去了。
Q:《弄潮儿》里主要写了哪些人物?
A: 《弄潮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家,即entrepreneur;第二部分是intellectual,算知识分子、知识人吧。我对知识人的定义比较宽泛,第一章是北大,我的母校。源起是一个个案,就是当年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2003年从美国搬回北京来,就碰上北大改革最白热化的时期,所以那是全书写得最早的一章。这个争论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又追踪,一直到前不久,这个改革有点无疾而终了。张维迎是这一章的主要人物,但里面是北大教授的群像:我在中文系的师兄比如陈平原、刘东,还提到甘阳、张永和这些人。王蒙那章的主要人物就是王蒙。张大中那章的二号人物是黄光裕,还有张大中的妈妈王佩英。
Q:我收到过王佩英慈善基金会赠送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和《王佩英评传》,其中收录的权威资料显示, 文革受难者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终于在2011年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
A:张大中其实很希望我写他妈妈为主,而不是以他为主,但是出于英文读者的考虑,我说还是得以你为主——你妈妈在里面只能是二号角色,因为她的事情是一个历史冤案,用中文写意义更大,跟美国读者讲起来比较费劲。
企业家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是孙立哲(亦可参见《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报道《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网址为:http://bjyouth.ynet.com/3.1/1110/21/6371869.html——采访人注),你们这个年纪的可能不知道,他是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钦点的五个模范知青之一,是全国最著名的赤脚医生。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1969年初下到延安插队,之后变成一个“神医”,特别有天赋,在当地治愈了无数农民。可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就把他打下去了,他的命运起伏极大。
后来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1982年出国,以后转行变成了一个出版家,又回来投资。中信出版社原来很糟的,他参与之后带来很多版权,出了很多畅销书。像《谁动了我的奶酪》、哈佛商学院的经管系列,都是他最先带动起来的,可他们后来发生了一场纠纷,他又被踢出去了。孙立哲是一个很“神”的人,精力非凡,一边经商一边满世界飞去修各种学位,业余时间还免费给人治病,甚至自己买进口药,送给贫穷的病人。很多这些老知青一代的人,一方面对知识,一方面对服务社会,有很深的情结,单是财富不能满足他们。
还有一篇是《纽约客》上发表过的,关于潘石屹、张欣的,就是以他们这个“土鳖”+“海龟”的组合,以地产这个行业为中心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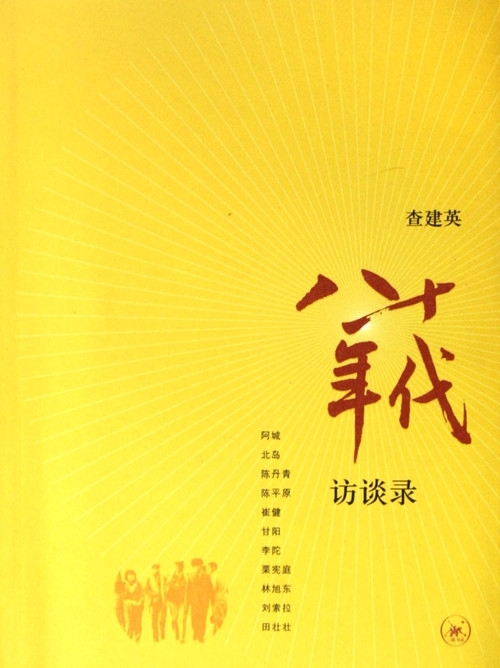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5月
企业家的human story
Q:写王蒙那篇我读得比较细。您和王蒙1990年代初就认识了,私下接触也挺多,但企业家这块儿可能就没那么熟,是后来再去访谈?
A:我对企业家的熟悉程度也都不一样。写潘石屹和张欣,开始认识的时候并没想写他们,是先认识张欣,就是几个女朋友洪晃、张欣、刘索拉、宁瀛和我,这五个人老在一起吃饭,号称“姑奶奶俱乐部”,一起神侃就认识了。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张欣是干什么的,刚从国外回来嘛,第一次跟她一块儿吃饭,她说“我是盖房子的”。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潘石屹,才开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后来才决定写他们,其实已经有点像朋友了,那时候再访谈就不是纯粹地拿着录音机,因为已经有一个阶段的了解。
孙立哲的第一任太太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关系特别好,但是她很早就得癌症去世了。我那时候就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混,他们都是老知青,我是班上最小的,因为我跟他太太好,所以有时候带着我玩,一块儿吃饭。史铁生、孙立哲都是一个圈子的,都特别熟,很多都是清华附中的子弟或者父母都是清华的海归教授。因为是陕北知青,他们回城后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后来孙立哲的太太去世了我们还联系着。
其中,最晚认识张大中,也不是我找他要写一篇文章,而是他找我。他的一个代理律师是北大法律系的,也是一个海归,他送给张大中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张大中那时候(2007年)刚把他的公司卖给黄光裕了,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有兴趣认识我,这个律师朋友就把我们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吃饭当中我才发现他有这么一个妈妈,由此对他更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企业家,好像也没有那么特别。
吃完饭以后他告诉我,他最有共鸣的是《国家公敌》,《八十年代:访谈录》他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有那么一个哥哥,他有那么一个妈妈,他愿意跟我谈。这样才约了一起再聊天,越聊越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把他作为故事主人公写篇英文的文章,最后我跟他也变成朋友了。关于她妈妈当年受迫害致死的采访,我推荐了郭宇宽去做,还给他们提供过见证人,恰好我的一个老朋友是他妈妈被押送刑场前的万人公审大会的在场者。
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可能他本来不是朋友,写完往往就变成朋友了,因为我不是一次性采访,会观察得比较长;或者是他本来就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值得写,他也同意,我就写了。你看《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很多年了,这种访谈就像朋友谈话一样。
Q:但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同质性,选题可能局限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
A:对,这个限制在于,我的写作前提是只写我熟悉的,我熟悉的当然就跟我平常的生活圈子、感兴趣的范围有关系。比如说,企业家其实是我相对不熟悉的,在我来说还是出了一下这个圈子。但是,我选的这些企业家,其实也是要有一段时间去了解,我不太愿意写一个没有深入了解的人。而且,就是写企业家,我一般写的是human story,是从人性的角度,以他们的成长和心路历程折射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历史的瞬间,而不是只写他们怎么赚钱、怎么成功,那种励志故事更有商业性、更流行,但那既非我的强项也非我的兴趣所在。
忠实于真相
Q:《国家公仆》追问得特别好,“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还是一位辩护士”,王蒙看到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A:发表之前他没有看过。这是美国的行规:发表之前你不能先给你写到的人看稿,否则会被认为你可能受到写作对象的影响、下笔不客观中立。发表之后,《纽约客》上的英文版和后来的中译版王蒙都看过,未予置评。但我们的友好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个态度我非常理解。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因为很多人来问我他什么反应,他真的是一句没说,我们照常来往,还一起上《锵锵三人行》;平常我们也有联络,发发电子邮件什么的,一切正常。
我觉得他不作评论挺好。有些时候,不说话最好。他知道这是我的文章,我会文责自负。无论他怎么反应,这个文章已经出来了。
Q:您写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顾虑?
A:我其实是很担心的,因为已经认识快二十年了,但也不能说是那么近的朋友,应该说是我很尊重和喜欢的一个忘年交。毕竟,他有官场的经历、 “放逐”新疆16年的右派经历。我当然非常担心这个文章出来以后会对他有伤害,如果他从个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或者是这个文章引起的议论影响到他某些方面,我都会很过意不去。但是,作为作家的第一考虑,就是我要忠实于真相、忠实于事实,我希望能尽可能的客观。
他又是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物。为这么一篇文章我看了很多资料。他是一个高产作家,好多东西我都要看,他那三大本回忆录我看了两遍;然后跟他谈,跟他周围讨厌他的和喜欢他的、佩服他的和感觉非常复杂的人都谈过。最后写出来的其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觉得还算实事求是吧。
但是文章出来以后,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喜欢王蒙的人觉得我下手太狠了,认识他这么多年,怎么能这么狠呢?不喜欢他的人,很多右派的朋友觉得我太同情他了,把他写成了忍辱负重的那种感觉,认为最后给他的评价其实相当高,太体谅他了,没有把他的所谓“嘴脸”写出来,还不够负面。
这是两极的反应,但还是有很多作家朋友、美国的读者,觉得把中国的复杂性写出来了。
Q:文中也提到,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或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您都会写邮件询问他的相关态度。比如,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演讲,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这引发国内互联网上的一片嘲讽,您事后立即发邮件表达对这场争论的失望,他简洁地回复道:“没事。随便。我顾不上这些事,也早习惯了。谢谢。”可在另一些更重要的历史时刻,您去信询问他的态度,他就“没有任何回复”了。
A:这些都是事实。他为什么不回我,也可以理解。他回什么、不回什么,就很说明他和他所处的语境了,我放在那儿就行了,用不着再过多地评价了,事实本身是最意味深长的。你看了以后,对这个人物的印象是更偏负面了吗?
Q:没有。我其实很少看虚构类作品,以前对王蒙的文本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他特别喜欢用排比句,这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煽情,有时甚至是一种语言暴力。他的回忆录中与访美有关的章节我倒是研究过,当然因为直觉或某种偏见,我觉得他比较圆滑或者说有“生存智慧”。
A:太多的人这样说他了,其中很多人自己也未见得有多么勇猛的表现。我持保留意见吧。
对他我已经非常感谢了,我写这么长一篇文章,在这么长的过程中没有给他看过一个字。《纽约客》有非常严格和繁琐的查证程序,他们直接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也不会告诉他这个文章是怎么写的,不可能给他念的,只会说这里面直接引用到他的话,问他说没说过这句话,这个话准确不准确。
他能够给我这么大的信任,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而且,文章出来以后,他并没有说什么,顶多说过感谢我花了这么多心血,这还是在看文章之前。
Q:写作期间,您要跟他谈什么,都会提前告诉他吗?
A:有过一次录音访谈。他知道我在写,但是怎么写、写成什么样,他完全不知道。
其实这些年我在挑选中国人物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精彩的、可以写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些我已经花了大量工夫准备甚至写了初稿,最后我都放弃了,因为考虑到这个被写的人可能承受不了我这种比较“狠”的写法。所谓的客观笔法其实相当重的,脸皮薄一点的人都受不了。
写王蒙的文章出来以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给我来了一封E-mail,他刚看了翻成中文的版本,说你居然写完这个还可以跟王蒙吃饭,简直不能想象。他就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他说这些年(写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个案时)是写一个就得罪一个就断交一个,所以不能想象我和王蒙还能吃饭。
我说,这正说明王蒙的大度,而且我的预计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我觉得他完全承受不了,这篇我就不写了。我想了半天,觉得他可以承受,他经历了那么多,那么稳妥和看透,会看得出我没有恶意,这么一篇文章也不会给他政治上带来什么打击。顶多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多少年来就是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承受得住,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有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所带来的特权,斤斤计较;另一些人把他捧上天,一天到晚叫他大师,让人起鸡皮疙瘩。这两种我都不是,是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这点,也能接受我对他的一些批评。
Q:《弄潮儿》里写到潘石屹和张欣的部分,他们也该读到了?
A:发表以后,他们才读到,之前没读到。《纽约客》给张欣打过电话,没给潘石屹打电话,因为他不懂英文,那时候《纽约客》还没有中文核查的专职人员。到了王蒙那篇,他们有了,就派了一个小时候移民去美国但中文很流利的人来查证。
《纽约客》向张欣查证过,还向相关的人查证过,但他们都是发表出来后才看到的。我说的客观也只能说是尽可能的客观,有些东西我在选材的时候也是要回避的,比如隐私;比如涉及腐败——你写了就可能把这个人抓起来了,那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得做一个考虑:他的腐败是不是到了某种程度,还是只是大环境的一个反映?如果只是一个反映,你必须要写到。
地产业有多少暗箱啊,我其实写了潘石屹、冯仑他们万通的第一桶金在海南是怎么淘的,当时整个环境都很疯狂,有点像开发西部时候的土匪。到后来拿地、拍地什么的,这在中国有很多暗箱、潜规则、权钱交易,要搞政府关系。但是我不会直接写到他们哪一次如何操作这么具体,我只是写了地产界的一般状况。我说的客观,也是有边界与分寸的,是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把握的。我不能因为发表一篇文章而去伤害一个人。
Q:以前采访您,好像您说上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那像微博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发展得这么迅猛,您上吗?
A:我Blog、微博都没开。前几年新浪曾邀请过我,我没接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那个时代的人对没有隐私这件事有一种很深的反感,什么《雷锋日记》之类的,就是为了给别人看。“隐私”这个词,以前汉语里听不到的,现在开始捡起来,我就非常在意,你私人写日记就不要放到网上去了。Blog已经有点儿这种嫌疑,现在发展到更琐碎的微博。老在那儿发布给别人看,你这一天在干什么、想什么。如果真的发表文章,应该是最公众的,不是私人日记、随想什么的。可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理障碍,我不习惯这样,这个公与私的界限太模糊了。
在这个高科技、大批量快速生产的时代,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80年代刚去美国上学我就开始用电脑,这都多少年了,我还是把电脑主要当作文字处理机,除了写、编文章,仅限于收发E-mail,近年才开始用网络做研究工具,查查资料什么的。
我本人对文字还是很挑剔的,对随手就写然后公布出去,是不太习惯的。我是一个低产作家,有些人很高产,我很佩服,但也发现好多人高产高得不太讲究。芝麻西瓜,什么都抓一把;一泻千里,泥沙俱下。文字应该是一个讲究的东西,应该沉静下来用心对待、舍得花时间打磨,应该沉淀、少而精。至少这是我自己更愿意选取的写作态度。也许文字才是我的真爱吧。如果你真爱一个人,你自然会珍惜、检点、细致地对待他,如果随随便便,不讲究时间地点、也无所谓装束举止,天天破门而出招摇过市,那不是一个糙人或者一个轻狂滥情的薄幸之徒吗?
所以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开微博、开Blog。但是,我不否定开微博,因为它由是各种人组成、各种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网络之外的言论、媒体空间很有限,有些公众事件的报道和讨论,只有网络和微博能做。在美国做,就没多大意义,美国主要是用它来社交,大家约会啊、八卦啊,中国当然也有一大批这样的,但微博在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透明度、自由度都很高的民间监督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尊重它。
Q:尤其像解救被拐儿童或其他公共事件的讨论,它即使在微博上被删掉,但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相关微博内容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传播出去了。
A:而且会被成几何级地无限转发。我也有不少“公知”朋友开微博,他们的言论要不受限制地直接发布出来,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报纸上开专栏受很多限制,在电视上说也受限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只不过我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性格使我不太适合选取这种方式去参与,所以选取了写作,这种方式是我能控制的。
写作完全是个体的事,我很少与人合写。像《八十年代:访谈录》我要跟每一个受访人合作,这在我是一次例外。我还参与过我工作的研究所编辑的论文集。其他时候我都是单干户,英文书也都是我自己写,文章也没有合写的。
Q:我也上微博,但有时又发现,国人在很多场合谈论的话题都来自微博,就觉得我们的话语资源太过贫乏,似乎不谈论微博上的话题就无话可说了。
A:对,但即使不开微博,也能听到无数的信息,所以我不缺这个。其实,我潜水去微博上看过,我注册了一个账号,看了一段连自己的账号都忘了。他们都说会上瘾,我根本不上瘾,看了看就烦了。我不看微博,信息也都到我这儿了。那些最敏感、最热点的事件,从别的渠道,从电子邮箱,很多人就转发给我了,或者在饭桌上就可以听到。
Q:前面的谈话中,您特别多地讲到“吃饭”,饭局是不是也是您回北京这几年了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A:当然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好吃之徒,所以好饭局、好饭馆我是不太容易拒绝的,在饭桌上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这些人对这些消息的态度。
信息源是多方面的,关一个,其他信息也足够了。现在我觉得还得关,你看我这里好多杂志寄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好多信息是重复性的、不必要的。你的脑子像一个装满太多杂物的阁楼,塞满了,反而你该看的书、该想的事、该认真对待的人,你没有时间也装不进去了。你成了信息的奴隶,对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反而麻木了,整天跟着时事跑、围着八卦转。所以,微博对我来说是不必要的。
Q:梁文道有个说法,他不愿意跟人在外面吃饭,因为在座一坐上来就都低头拿着手机发微博。
A:这太恐怖了,我最害怕这种人了,如果我的同龄人里有这么一个人,那更恐怖了。年轻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他们就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年轻人也容易不自信、爱跟风,需要群体承认、确认他。可是到了这种“微博控”的程度,坦率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病,就像“照镜狂”。如果一个中年人,一天到晚生怕一群陌生人不关注你、生怕“掉粉”,完全被你的所谓粉丝团控制住了,你还有什么自我,这也太可怜了。
而且这种行为实在太不讲究、太糙了,貌似他是高科技能手,他很in,但其实连基本的教养都没有,恶俗无比。这种人出现在饭局上何止是败兴,应该请他走路,out!因为他不经别人同意就把私人场所的门打开,搬到网络上的公众场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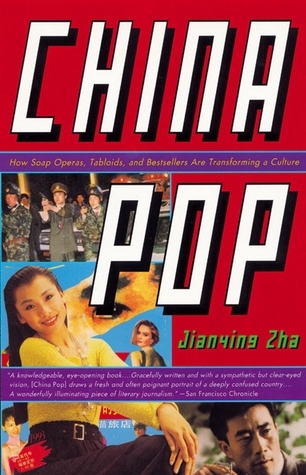
《中国波普》(China Pop)
Jianying Zha /著
The New Press
1996月4年
印度是中国的镜子
Q:我最关心的还是您作为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因为中印比较研究是国内近年来的一大热点。
A:The New School刚创办印度中国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受聘参加了。2004年开始讨论,2005年初正式成立。开始我对印度完全不了解,那时候印度也不太热。2004年,美国一个大基金会投了一大笔资金,放到这个大学里面,他们要找一个驻中国的、一个驻印度的代表一起来做项目策划和管理。此前一年,2003年我拿到了古根汉姆的写作基金,搬回来写关于中国的一本书,同时带着我女儿在北京上小学。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也不想回美国去。所以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他们需要这个人住在中国;另外那个印度代表驻孟买,但是都要两边跑,因为总部在纽约。我正好借此也可以常去纽约,就答应了。
那时我对印度一无所知,极不了解。好在我们只是出资花钱的单位,在纽约筹办项目,在中国、印度、美国三地分别、分批选拔相应的学者来合作做研究课题,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开始真是两眼一抹黑,我的一些朋友也很纳闷,说你怎么搞到印度去了,印度有什么好研究的?
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七八年变化非常大: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印比较、中印美三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都变成了热门话题。我们的课题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好几期不同的成员,课题组有些人也变成了朋友,比如第一期里面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姚洋,(记者)郭宇宽,我们一起去印度考察,也成了朋友。后来的中国成员包括许志永、卢思骋、李波等。印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由此不仅对印度增加了一些了解,而且印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中印比较和中美比较很不一样。
Q:具体怎么不一样?
A:印度与中国同为古老的亚洲文明,互为邻居,可是我们彼此的研究兴趣相当弱、相当差。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印度是在我们意识之外的,至少是在边缘上,有很多出于无知的偏见,我们老是盯着西方,主要盯着美国、欧美,对吧?
我们对印度其实是很漠视的,他们对中国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本来他们在历史上觉得自己是中国的老师,因为佛教就是从他们那儿传来的嘛,在文明交流中,中国受惠于印度很多。然而1962年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是战败者,他们认为中国背叛了友谊,尼赫鲁为此郁郁而死,所以他们对中国有一种伤痛的情结,不信任、有敌意。
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市场改革起步晚一些,至今走在中国后面,与我们又有一种竞争心理。但他们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优越感。不只政治制度,在价值观、精神文明、意识形态上,他们好像都有一种优越感。你别看它有那么长的被殖民史,很多印度人在文化上相当自我,认为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最优秀。
去实地考察以后,我发现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在这么一块与我们同样古老的亚洲文明土地上实行民主,实际运行的经验其实非常复杂,成败得失,一言难尽。它为什么跟欧美式民主不一样,英国人带去的民主、法治是怎样演变成了另一种样态的民主、法治?这当然与它的历史文化有关系。而印度可以作为中国追求民主的一面镜子。毕竟我们跟美国太不一样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地理文化决定论者,对地理文化是特别在意的,很多东西你得推到历史的源头上去看,不能光看现在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文明的主流是儒家传统,而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不是佛教呢?为什么我们历史上多数时期一直是王朝、帝国,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呢?有很多东西,都跟现在的问题直接相通、一脉相承,不看历史就看不清今天。去看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邻居,当然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
比如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很多印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是非常崇拜的,对中国革命持有非常浪漫化的观点,我认识的好多印度左派学者都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种性问题、不平等的问题。人们往往出于自己的问题,去从别人那儿取经或者抓别人的东西来,就像我们爱把西方的某些东西拿来批判我们自己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把西方浪漫化了。总之转了一圈,印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体,一个学习、借鉴和理解我们自己的镜子。这个工作让我获益匪浅。

查建英
作家,北京人,1978年-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90年代返回美国。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Tide Players》、《China Pop》、《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等,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China Pop》被美国 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