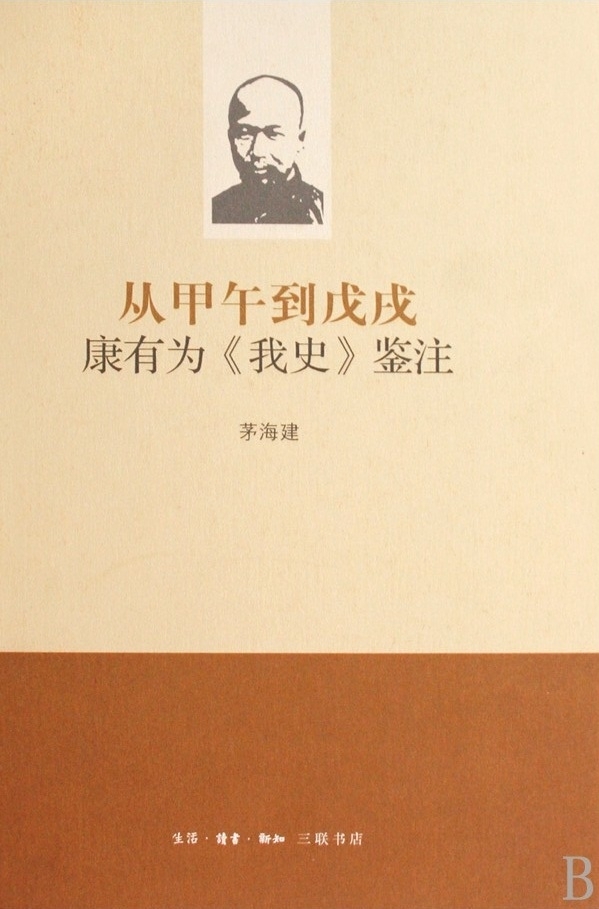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戊戌狂想曲 尹敏志/文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据其自编年谱所说,并非是从甲午战败后才开始的,而是始于更早前的一次顿悟。那是1878年,他还在礼山草堂苦读经史时,一次打坐的过程中“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恍惚间,他觉得自己是孔子再世:“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次通灵般的神秘体验后,康有为给自己起别号为“长素”:长于素王孔子。那一年,只有20岁的他立志像孔子一样改制维新,经世致用。
康长素的狂放不羁后来也传染给了他的学生。弟子们上行下效,纷纷给自己起了各种惊世骇俗的别号: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调侃道,这是“把曾参当马骑也”。康最钟爱的大弟子陈千秋的别号则是“超回”——事实证明,这个别号起得实在是有欠考虑。1895年年初,维新变法还没开始,26岁的陈千秋就跟当年的颜回一样早夭,吐血而亡。
1
一群带有宗教狂想色彩的康党所领导的变法运动,结果自然凶多吉少;但在清末那积重难返的局面下,又似乎只有这种反常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团体,才可能去发动一场真正的变革。1898年8月变法事败前夕,康有为南下逃亡,一路被悬赏通缉,九死一生,幸而被英国人营救才逃过一劫。参与营救的英人戈颁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康有为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并补充说,“我猜,光绪帝大概也和他相像。”
出于空想家的本色,康有为8月底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便已开始凭想象臆造另一个戊戌史。康在采访中夸大自己在变法中的作用,并声称有光绪帝的衣带诏,要去英日两国求救兵来恢复皇帝的权力,等等。到日本后,他便开始伪造《戊戌奏稿》,并自编年谱《我史》。幸存的康党成员们,比如梁启超,也积极配合康的造史行动,将相关记录系统化,使之不自相矛盾。与此同时,曾积极举荐康的翁同龢也由于畏祸,暗地里剜挖、芟改日记中关于变法的记录。真实的戊戌变法被人造的迷雾重重掩盖起来。
茅海建阅读大量史料和档案,考证了《我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旁及《戊戌奏稿》、《翁同龢日记》等,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解开这个历史罗生门。他认为,康的《我史》总体来说不失为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里面的不实之处与其说是故意作假,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的孤芳自赏。虽然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康有为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失败的所有原因在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阻挠。他在东瀛那“纸屏板屋孤灯下”的冬月夜里,“自我咏唱着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纯洁化美丽化的英雄史诗。”
2
戊戌变法通常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行的是君主立宪。此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戊戌奏稿》中的三篇另作中,康有为提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所”,建议清廷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民合治”。但实际上,在变法的过程中,康从未提出过类似建议,相反,他很明确地反对立即开国会,理由是“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因此“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
康有为在当时主张的只是设“制度局”,一个给皇帝提供治国建议的小规模精英智囊团,类似于枢密院,并不具备制约君权的功能。康认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变法必须由光绪帝“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保证皇帝和中央政府绝对权威的基础上,以强有力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变革,并镇压顽固势力。只有这样,变法才有可能成功,“中国唯有君权治天下而已”。
康有为并不反对君主立宪制,只是觉得还为时尚早。他有一套自己的政治学理念,即“公羊三世说”,认为在所有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都有三个必经阶段: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和民主共和(太平世),这三个阶段是不能随意跳过的。相信《戊戌奏稿》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按照这个理论,当时君主专制的中国的变法方向自然是君主立宪。
但现在看来,康有为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小心谨慎。在“君主专制”阶段,他还区分出了“绝对专制”和“开明专制”两个小阶段,后者是君主立宪制的预备期。也就是说,戊戌时期的康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立宪派”,而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取萧功秦的定义)。不得不说,在变法的战略层面,康有为确实比当时的很多人都要理性务实。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优秀战略家的康有为一进入到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就开始头脑发热,狂飙突进。
在和光绪帝的第一次策对中,康把中国比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殿,“小小弥缝补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统筹全局而变之”,从重从快,最好干脆把旧官员一并免职,然后“尽变旧法”。在保守派荣禄当面质疑这么激进的变法是否可行时,康有为的回答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其实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倾向或同情变法的,但由于康有为的狂傲,这些潜在的变革力量渐渐与他分道扬镳。除了康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想家性格外,维新派日益膨胀的权力欲也让他们渐失人心。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单纯,暗地里,他计划通过建立制度局让自己进入权力核心,让康党成员占据各个部门的重要位置;他与梁启超试图将汪康年的《时务报》“收归国有”,借此控制全国舆论,打压反对意见;对于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康有为被维新派认为是总教习的不二人选;康还试图将他的孔子改制说确立为学术正统,一跃成为全国学界领袖——这样,他就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集丞相和教皇为一身的人物。
康有为的弟子在变法时期也是飞扬跋扈。他们有一次在上海街头遇到了古文经学的领军人物、康有为的论敌章太炎,于是便上去将其殴打一顿。改革的大忌,乃是其设计者与得利者几乎为同一批人。这不仅会使很多人对改革者的目的产生怀疑,而且那些致力于革除弊端的人自己,也有可能因此堕落为政治黑暗的渊薮。
对戊戌变法的另一个误读,是认为维新派走的是“和平改良”路线,而革命派则是“暴力革命”路线。实际上两派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对民主共和制缓急的不同认识,维新派对于暴力手段并不排斥。在变法末期,维新派其实已经开始谋划军事政变,他们对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人都有策反计划,最后则锁定袁世凯,要求他率兵入京,一路入颐和园“执西太后而废之”,另一路则入宫“密救”光绪。但袁世凯始终对维新派虚与委蛇,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知道大势已去的康有为于八月初五离京,同时,杨深秀决定放手做最后一搏。杨经光绪帝之手辗转上折给慈禧太后,称颐和园的滈化殿下有先帝埋下的“黄金纹银各一窖”,既然现在赔款弄得我们财政紧张,何不派几百个人进去试着挖挖看?“万一罗掘得之,岂不大济其用,胜于票借万万耶?”这个说辞实在是拙劣得可以,不要说老谋深算的慈禧了,就连当时北京的普通市民都对之“诧为奇异”,大家都看出来,这不过是行刺的借口罢了,杨深秀“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
所以,与其说慈禧太后自八月初五起的一连串行动是一场军事“政变”,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反政变”;慈禧对于维新变法本身的厌恶,远远不及她对维新派那废黜她权力,甚至取其性命的意图的仇恨。若意识到其实是维新派先伸手摸刀,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慈禧的人身安全,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慈禧后来会怒不可遏,冒着激怒“友邦”的危险,近乎疯狂地抓捕康梁,废除所有新法,并且不经提审,就将杨深秀等“六君子”刑于菜市口了。
3
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合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思想基础的福泽谕吉说过:“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毛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但康有为呢?他一上来就说:“惟方今之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在将所有旧官员都排挤出去同时,也早早地给戊戌变法判了死刑。
1899年,慈禧召见李鸿章,称有人上章,举报他有同情康有为变法的言行。没想到,一向逢迎的李鸿章竟未辩一词,大大方方地承认指控属实,并称:“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无以对。而这一切,早已非在海外四处流亡的康有为所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