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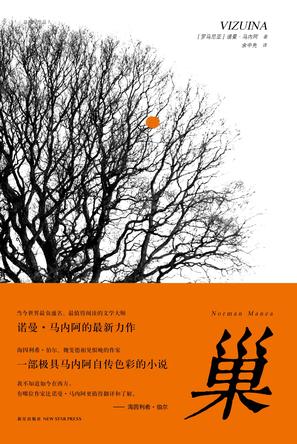
作者: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 余中先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by李静睿
尽管诺曼·马内阿早就得过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并且被视为罗马尼亚语写作中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他却依然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正是来自他这本书,“彼得·加什帕尔意识到,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
2011年8月,马内阿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Against Simplification(反抗简单化),文章读起来有点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Claudio Magris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可以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巢》有一个甚至算不上故事的故事线: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还有一个主角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戈拉教授,戈拉教授在妻子露的家族帮助下才能拿到护照,但是露却并没有跟他来到美国,反而是几年后跟着加什帕尔一起来,露是加什帕尔的表姐,后来成为了情人,而戈拉的前前妻爱娃则是加什帕尔的母亲。总而言之,马内阿成功创造了他的复杂:一团乱麻。
《巢》有浓厚的自传性质,虽然马内阿到底把自己栖身于戈拉还是加什帕尔无法辨清,书中的大师迪玛却明显以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为原型。伊利亚德是著名的罗马尼亚籍学者、宗教史专家,1956年来到美国,他著名的《宗教思想史》影响巨大。在伊利亚德去世后第五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刊登了一篇揭露伊利亚德历史的文章,作者正是马内阿,文中提到他曾经在30年代支持过铁卫军,这是极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其成员叫军团兵,铁卫军虽然在1941年就被取缔,但它被认为是后来齐奥塞斯库上台掌权的前期功臣。《巢》中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的原型则是伊利亚德的弟子约·贝特鲁·古利阿努教授,1991年5月21日古利阿努在芝加哥大学内被枪杀,死于学院的教员洗手间内,子弹从相邻的小隔间射进了坐在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脑袋,据说死因是古利阿努当时正准备审阅其导师伊利亚德早年的政治背景,而芝加哥有不少热衷于铁卫军的流亡罗马尼亚人。
想要更好地理解《巢》,必须和马内阿的另外一部作品《流氓的归来》互相映照,后者被认为是非虚构类的自传作品,但事实上它和《巢》拥有一样的内核,两本书的背景都在纽约和罗马尼亚之间切换,《流氓的归来》主要写罗马尼亚,《巢》主要写纽约,可以把它视为《流氓的归来》的续集,伊利亚德和古利阿努的故事在《流》中也有详细叙述,《巢》里则不过改换了人名而已。
在《巢》的故事里,后半部的重要线索是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收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而在《流氓的归来》里,古利阿努的谋杀案发生时,马内阿正好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上述和伊利亚德相关的文章,FBI找到了他,告诫他在与罗马尼亚人及其他人接触时要小心。
过多纠结于《巢》那杂乱无章的情节也许意义不大,马内阿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一一解答的疑团:加什帕尔为什么无故失踪?那封死亡威胁信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女学生的行为艺术实验?小说里的“我”到底是另外一个罗马尼亚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戈拉的身外化身,露最后为什么和“我”在一起?这是一本由各种闪光碎片支撑起来的小说,故事和人物都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书里一个来自奥德萨的出租车司机说了一段话:“我们全都在变成登记号。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奥斯威辛那样,而是在一个信用卡上。Visa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会保险卡、医疗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居住证0298号。加什帕尔的号。”它大致可以概括马内阿或者说书里这些流亡知识分子的痛苦:流亡之前,他们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们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远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所以《流氓的归来》里引用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齐奥朗还说:“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在不同的书里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在集中营中父亲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坐上了共产党的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原因是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活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
诺曼·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想要忘记的尊严和不能忘记的痛苦,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作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马内阿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书里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