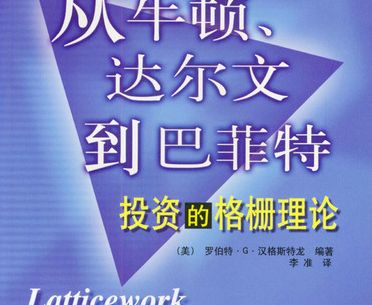

作者: 【美】 罗伯特·G. 汉格斯特龙
译者: 李准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by邹波
亚当斯密的学说认为事物都有一个“真实价格”,也就是最符合事物本质价值的价格,价格围绕它波动,这种本原论还是很古典的。
后来,波动本身所创造的价格影响开始超越所谓“真实价格”,“真实价格”即使仍然被认为存在,它的影响也开始式微,事物开始离开原初的物性根基,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脱嵌”吧……于是出现了马歇尔的竞争理论。但即使竞争也还是可以预测的,似乎。继而,无法用竞争解释的波动出现了,现代世界开始屡次崩盘。
如今我感觉到的则是:“文化神秘论”色彩浓厚的细分市场产品保护的策略——让供求关系无法轻易撼动一个产品的体系,一切都试图奢侈品化,所谓产品卡位,广告策略无不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细小的亚文化市场然后实现微小垄断,回避竞争——对真正公平的自由市场进行抵制——当我们无法将比自由更莫测的波动列为可征服的敌人——当我们无力反对更大的敌人,我们反对我们看得见的敌人——这也许就叫做保守主义。
当代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所信奉的流行文化或者职业文化、公司文化已充分决定的。软弱之下的文化决定的机械人,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组合是比潜在的人性更容易分析出的。
正如社会问题容易通过文化之下的认同表面解决,而商品则容易出于文化认同而被轻易购买。这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更实用主义更理智的人性本能。
是什么在主宰我们的行为?
我并不能迅速洞察人的性格,也阅人有限,但对各种人腔调里立刻流露的决定他的文化比较敏感,我的批判的格栅里放满了各种文化甚至亚文化的指示灯,当一个人出现,它们立刻会告诉我哪些灯亮了,哪些灯没有亮。
今天开始读嘉偌发我的书单里的书,他是改行做了投资分析师的前同行,他认为我的“洞察力”也可以用来当一个分析师——如果有一天记者这苦逼活干不下去——他推荐我入门的第一本书是《从牛顿、达尔文到巴菲特:投资的格栅理论》:开头提到桑代克实验结论,发现在一个领域的学习,不会帮助对另一个领域的学习,于是,我们的能力并没有增加,而只是知识的共同体增加了。
我们学习,将自己职业化,只是在筑墙。但为什么要筑墙呢,这种让某个职业神秘起来的努力,本身也成为了实现它保有其世俗价值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决定论造成的非理性价值体系(比如茅台),带来劳动的价值被高估,它显然也带来行业标准的威权和泡沫,同时,它也带来分众市场的保护。
对上文所说的“领域”,我则体会为越来越迅速奴役各种人的各种“时代文化”。
一种新文化,又是那样轻易地从不需要的历史的表面被一个普通人得到,通过简单模仿——越仓促宣称建立的新知识越是如此——
我只用模仿它的腔调,就似乎能学到格栅中的某种知识的外衣,一种文化圈的流行口吻,听起来像某种身份,而不是真正有什么知识准入制度,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不需要真正的口出真知灼见或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而只是一种几近严酷的寒暄能力、只是一种认同的过程。
当大部分需要综合思考的解决问题的知识变成了社交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学,而方法论又是一个教条又投机的人容易学到的模型、规矩套子,问题反而似乎就迎刃而解——解决方案或者也只是某种说服对方改变自己对事物的价值观。
实体的改变,越来越被推动舆论和意见的改变所代替,一个社会问题是由它所指需要改变的实体和关于该实体的看法构成的。
我们分析一种社会问题在今天如何算解决:它似乎只需要通过股票募集资金——这种将贸易、金钱和舆论同一化的东西,是的,人们不是常宣称,在这个时代,语言就算行动了。
股票市场真是个好东西,它将本该社会福利生生去解决的问题,抛给投资者的感动和同情,而这种感动和同情,在投资者看来,是他全部理性的结果。而至于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不是无限的钱涌入一个意识的陷阱,而陷阱的风险又转嫁给下一个陷阱……问题只是继续无限转嫁下去,直到世界尽头。
这成了重要的职业经验和人生经验——你能这样停留在外表就貌似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它能获得的回报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靠舆论和金钱幻觉而无限续约的关系而生。至少对投资界是这样。
理智造成难以预测的向平衡的回归,不理智造成难以预测的波动,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文化分析,来预测人们用所主宰他们的文化心理而做出的预测的不理智。
这也就是社会批判中指出文明的背谬与经济学思维的呼应。社会批评家是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分析师的。但最终让笃信成功学的分析师与社会批评家决裂的是,对金钱应该有怎样的策略,因为回归平衡也能挣钱,波动也能挣钱,利用理智也能挣钱,利用不理智也能挣钱。但社会批评和投资学最大的不共戴天的区别是,后者肯定得利用什么挣钱——可以指出经济和社会的不成功,但必须给读者和自己一个成功的模型,前者更关键的责任是:在真理面前不能撒谎,即使拆社会的台,打读者的嘴巴也不能撒谎,他很可能只是指出彻底的不成功和人类彻底的背谬。尤其是文学。
至于这个世界的复杂难解——究竟是什么文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它该被理解为一个聪明人干下荒谬勾当,还是一个蠢人和愚蠢的世界做了它们能做和该做的那样简单呢?或诚如博尔赫斯在小说《巴比伦彩票》中试图阐明的“无常”:一个被它的体制文化所决定的蠢材、一个被人们看透的蠢材却获得了构建世界的无限权力,从此摇身一变眼睁睁成为加诸人们命运的莫测的“无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