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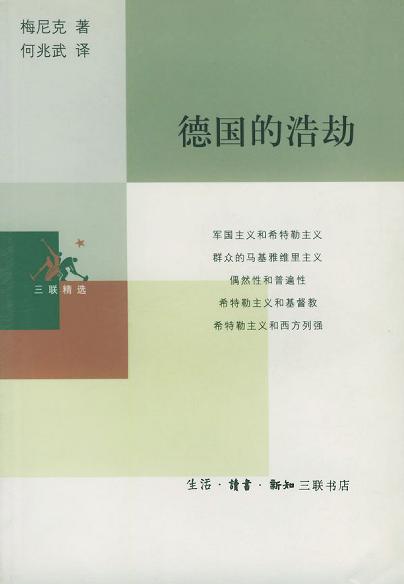
作者: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何兆武
撰文:刘波
一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本月去世后,《金融时报》记者菲利普·斯蒂芬斯回忆起1989年与她的一段对话,那是在一个非采访性质的酒会上,他问她,是否会屈从于财政部的压力而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听到此言,撒切尔抓住他的领子说:“我是不会让那些比利时人决定英镑汇 率的。”(欧盟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撒切尔那段时间还常向德法领导人强调,英国主权的基础是一千年的历史。当然斯蒂芬斯不忘调侃地补充道,这里的“英 国”应该单指英格兰。考虑到苏格兰的存在以及它时下正“闹独立”的背景,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政治家、媒体与学者共同构建的想象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经济共荣与科技进步将不断弥合曾经的民族差异,但正如上述对话所表明的,即便是在融合程度达到人类史上最高水平的欧盟里,基于复杂历史原因的民族隔阂与矛盾仍能不断刺痛人们的神经。
确如撒切尔所言,英国民族国家的形 成早于多数欧陆国家。追根溯源,民族国家最初是学者与政治家的拟制,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并非毫无事实基础,但却是以阐释的方式超越历史事实,最终取得一种类似于信仰地位的存在,填补宗教退位之后的现代国家公民的信仰真空。它是主动的政治整合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政治整合。
从1990年代 巴尔干半岛的战火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再到苏格兰独立争议,和平与非和平性质的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的幽灵没有完全散去,而如果回顾20世纪 的欧洲史,拜希特勒这样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之赐,德国的民族主义曾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曾经是那么的暴力和富于侵略性。无数历史学家试图解 释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在他们之中,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2-1954)拥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从德意志 统一到希特勒覆亡的全过程,而《德国的浩劫》一书,则是他在84岁高龄所写的总结性的压卷之作。
二
由于较近的历史给人的印象 更为深刻,所以局外人往往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历史上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向来都非常强烈,但事实上,德意志民族一度分崩离析,民族观念极其淡漠,其民族主 义的缘起并非对外征服的需要,而是像近代中国一样,也是源于自身的弱势地位,以及战场失败带来的屈辱。
在德国的中世纪时代,除了腓特烈一 世、条顿骑士团等势力外,这个民族基本处于受四邻欺压的境地,在英国与法国公然与罗马教廷对抗时,德国人曾对天主教士的横征暴敛逆来顺受,被嘲笑为“教皇 的奶牛”。反抗罗马教廷是15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革命的原因之一。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甚至沦为欧陆诸强交战的牺牲品,有统计认为它丧失 了1/3的人口(另一说为高达3/5)。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是德国民族主义大范围爆发的导火索。1807年,柏林 大学哲学教授费希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夏伊勒评论道,演讲“深深激励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其响亮回声即使到 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
耶拿战役也是迈内克所极为关注的,1814年拿破仑势力衰落后德意志各邦国奋起进行的反抗战争,被他称为德 国“解放战争”。迈内克绝不反对民族国家,而是对其抱着赞许的态度。他的首部重要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便探讨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对立 统一。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铁血宰相”俾斯麦所代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文化,但他强烈地赞同这位强人在1871年实现的德国统一。
他也主张德国 应该进行持续的民族国家构建。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代表着德国人团结所达到的顶点。然而还不到一年,团结又破裂了,德国人又走上不 同的道路。战场的失利引发推翻帝制的革命,而从右翼阵营中又传出视革命者为叛徒的“背后一刀”神话,这样的社会分裂为希特勒的上台培育了土壤。
迈 内克是希特勒主义的强烈批判者,但他对德国民族主义始终保持着热情,这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普鲁士-德意志身份,也是植根于他对欧洲大历史背景的体察。迈内 克认为19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两大浪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有欧洲国家都必须找到两股浪潮交汇与激荡下的自存之道。英国由机器而开始的经济-技术范围 内的革命,唤起了大工业、新的人民群众和高度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动员了民众,但不仅唤起了自由,还唤起了对权力和占有的渴望。从沉默中崛起的庞大民众 对既存社会秩序和文化构成无比巨大的压力,他们首先要求民主,继而不可避免地为充分保障自身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于是革命被设想为一种达到千年幸福王 国的手段。
但社会主义潮流最终并未发展为马克思等人所宣扬的世界革命,因为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横溢了它。民族主义浪潮与欧洲旧秩序不是 敌对的,而是能经常与之结盟,其主要支持者不是无产大众,而是日益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两股潮流交锋的结果在一战前夕变得显明:共产党人所预言的大爆发式 的最后革命并未到来,除了试图以“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为理由发动俄国内部革命的列宁等左派之外,大多数势力都以自身所属的民族而非阶层决定其效忠的对象。
迈 内克对德国的分析是,在那里,民族主义浪潮比社会主义浪潮来得早,大约早半个世纪,中产阶级也比无产阶级更早地强大起来,并达到高度的精神繁荣。从歌德的 时代到俾斯麦的时代,再到希特勒的时代,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权力与精神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既应对群众的压力、庸俗化和衰颓化的压力,又保 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但德国古典自由主义所试图实现的这样的综合,后来遭到严重威胁乃至于破灭。纳粹党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来调和两种浪潮:“通过一种极 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国会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其完成之日,便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想世界陷入黑暗 之时,希特勒的毒气室抹掉了德国文明的最后一丝残余。
三
《德国的浩劫》写于二战战火刚刚熄灭的1946年。迈内克绝不是纳粹 主义的拥趸,但德国的失败与被占领,也似乎为他所倾注心血的、自耶拿以来的德国一统并领导欧洲的梦想画上了最终的句号。迈内克在当时还不能看到1992年 东、西德的统一,以及随后德国在经济上逐渐成为欧盟的领袖,绽放文化和“软实力”方面的光辉。他所能预见的只是一段外国占领下的“屈辱”时光。
但作为历史学家和亲历者,迈内克需要为希特勒主义的缘起做出总结,这是已经80多岁的他的使命与责任。他坚称希特勒的崛起是一个偶然,而非德国政治与思想发 展历程的必然。因为,没有德国各阶层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没有《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形势,没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危机与失业,希特勒这个心理病 态的人将在某个角落里默默终老,但后来的事实却是,“脱节的时代在历史舞台上召唤出了脱节的性格,二者相互激发到了可怕的高度”。迈内克对希特勒上台偶然 性的判断,是本书最引人争议的一个论点。
迈内克对希特勒崛起偶然性的总结,是基于他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他与勃鲁宁等 魏玛共和国高层有过亲身接触和对话)。例如,他分析道,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力量要让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的个人决定导致了可怕的后果,这是当时许 多德国人所未曾预见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夏伊勒也观察到,在1934年8月之前,德国的将军们要推翻纳粹党政权原本易如反掌,但他们却对希特勒发下了效 忠誓言并坚守自己的“荣誉“。换言之,在纳粹主义成长为可怕的怪兽之前,德国人原本有很多消灭它于萌芽的机会。这些都是事实分析。
而另一方 面,承认德国人当时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希特勒上台,否认他上台的必然性,也有迈内克作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考虑,他必须顾及学术结论的社会影响。但也正因为这个 原因,迈内克被指责为对德国文化中的法西斯主义遗毒认识不够。然而,事实上迈内克对极端民族主义崛起的深层次文化根源的分析是极其彻底的:他重述了瑞士历 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对现代社会的“可怕的单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能引致极权主义的警告,他探讨了技术 力量对心灵的侵蚀,弥漫到大众之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可能引发的民族狂热,这些都最终使得奥地利学者格雷尔帕泽尔19世纪中叶发出的“人性-民族 性-兽性”的警告变成可怖的现实。
但作为一个继承了德国史学传统、倾向于把历史流变与人类的更高目标联系起来、强调历史伦理属性的学者,迈 内克不可能认定德国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罪孽、从而是需要根除的,他只能视纳粹的罪恶为一种反常,一种变异和歧路。而且,对于那些主张“纳粹浩劫是德国近代 历史文化必然产物”的人,他的“辩解”并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基于对现实事件的合理诠释。
在“第三帝国”的疯狂所制造的德国的一片废墟中,作 为知识分子,迈内克也必须拨开厚厚的劫灰,搜寻到一些可资后世作为建设基础的砖瓦,愤怒和批判不能成为全部。在寻找这种基础的时候,他绕过了年轻时代曾经 赞扬的俾斯麦,回归了更早的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期望其东山再起。本书译者在序言中写道,这体现了迈内克的“温柔敦厚之 旨”,会让一般读者多少觉得有些“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这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感,历史不应是只描述恶因而令人绝望的学科,正如迈内克对历史学使命 的描述:“通过将经验转化为理念,人类将自身从过去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创造重塑崭新生活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学可望取代哲学而成为一种“普世的学科”。今 日德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复兴,也足以告慰迈内克等学者当年的一片苦心。
如本文开头所述,世界大同的理想尽管美好,但民族主义仍将是长久的存在,虽然它的影响会不断衰减。民族主义并不是《德国的浩劫》的唯一主题,但它从一个侧面对所有现代民族主义可能走向的歧途发出了警报。迈内克写道,有一 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扩张;一种民族性是真诚浪漫主义的,另一种民族性则只是浪漫主 义的斗争武器,而武器成为目的本身就会导向希特勒主义。也许为了避免德国的歧途,人们应该构建的是一种内生的、文化上的、主体性的、持重稳健的民族主义。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