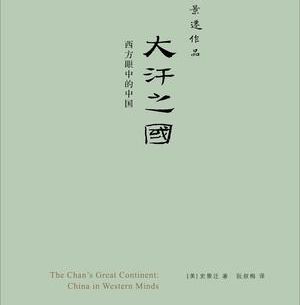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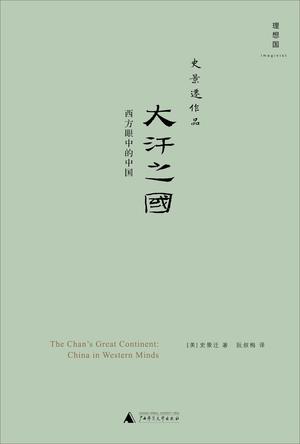
《大汗之国》
【美】史景迁 著
阮书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耐冬/文
据说钱钟书先生在回绝一位读了他的书之后想要登门拜访的读者时说:如果你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味美,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鸡呢?对 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受其惠确实不必识其人,个人也有选择不被认识的自由。而且,在“是否应该被认识”之外,还有“是否能够被认识”的问题,司马迁就曾谈到 过自己对张良的想象破灭的例子:“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识人之难。
相对于个体的人,国家则一无选择是否 应该被外界认识的自由,二有是否能够被充分认识的难度,有关国家形象与特质的误读时常发生。中国就一直存在着这种被认识的困境,不但“中国”这一概念的所 指对象难以做几千年一贯的定义,就连中国的具体形象,在各国各界之人的眼中与笔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中国公民遍布世界的当 下,中国似乎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被认识、被“准确”描述的需求,至少在我们的官方宣传里是如此。
谈到中国在域外的形象,我们很容易马上想到 影像中的那些样子:一个个拖着小辫子做苦役的“猪仔”,或是阴险狡诈、作恶多端的“傅满洲”博士,以及手执双节棍的李小龙。如果算上卡通形象,那我们还有 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这些被夸张处理或凭空想象出的形象一度代表了中国,而若仔细翻看欧美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形象远不止如此。
美 国学者史景迁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对西方所认识的中国形象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的考察范围上起1253年传教士威廉·鲁伯克出使和林 时所做的记录,下至20世纪下半期卡尔维诺创造的文本《看不见的城市》,共选择了四十八个对中国进行描述与研究的文本,每个文本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而 他则将这些个性化的认识展现出来,并略作解说。
有趣的是,史景迁并未在书中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或肯定性的中国形象,他旨在呈现种种文本的 产生机制及其特色,而不是简单地重绘一幅中国的图景。为此,他使用了“观测”一词,作为这些对中国的描述与研究的统称。在他看来,“观测”代表了观测者站 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其所认定的中国进行主体感受,因此本身就并非对中国的真实描述。但他并不认为这种非真实的描述就应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而打入另册,相反, 正因为观测者主体认识的存在,才让他们的描述文本极具个性,成为能够被他人接受的、对中国做出的一种解释。他提出,“观察者藉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 己”,正是对这种观测行为的最好诠释。这种观点,与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有契合之处,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体系之中,前见必然存在,而基于前见所做的解释 并不应被视为误解而被抛弃,而应被置入时间之河接受洗礼。史景迁不动声色地将四十八个观测做时间性的排列,或许也是要将各类前见呈现于时间轴下。
在 导论中,史景迁特别提出,“观测”一词本身也有着多重含义,既包括航海中的瞭望观察,也包括射击前的定位,还可理解为赌博中的出千行为,甚至可以作为叹气 的代名词。这一说明,也用词语释义的形式告诉我们对中国进行描述的行为本身含有多重性质,不能简单地视为理性的认识与客观的分析,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 的目的下由不同具有前见的人有意为之的事情。通过这种暗喻式的解说,他几乎已经将他对这些观测文本的看法和盘托出——只有复原这些观测产生的背景,做出观 测的目的以及观测者自身的前见,对观测的评估以及再解释才成为可能。
对“观测”的词义解析还带有一重含义,那就是对风行一时的“东方主义” 学说的回应。自爱德华·萨义德提出这一概念,东方主义经常被作为分析之利器,自中东以东的地区,凡是在来自欧美区域的描述中有与其真实状况(或自认为正确 的状况)不符之处,特别是关涉其自身利益者,就祭起东方主义这一法宝,认为这全出自“西方”的建构。东方主义者在认定东方的形象是由西方所建构的同时,自 己也建构起了一个看似整体而强大,实际上并不一定真实存在的作为建构者的西方。很多人在回应东方主义学说的时候都采用了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并不 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西方”建构者,所谓西方对东方的建构,也只是在某种情境、某种目的下的观测而已。值得玩味的是,史景迁本人对“西方”是否存在持比较谨 慎的态度,他认为,“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制作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 些共同传统。”可能在他的眼中,简单地否认西方的存在就和东方主义那种否定东方的立场一样不可取,作为所谓东方建构者的西方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就如东方主 义所认为的被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并非本不存在一样。
他所选出的四十八个观测文本,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如果按照文本作者 与中国产生联系的方式,可以分为亲见者、耳闻者、传闻收集者与想象者几种;如果按照文本产生的具体形式,可以分为见闻记录、个人想象与理性分析几类;若按 照文本出现的目的来看,则可分为反省自身的借鉴、政策制定的依据、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安排与戏剧性设定、对神秘性的追求等等。
之所以要按照各 种标准为这些文本分类,目的在于呈现出各种分类方法下各类文本的不同之处,若有足够多的分类方式,那么各种分类法下不同类别的特色将充分呈现,这就可以让 我们对文本的形成及其对中国进行理解时的诸种要素多一些认识。史景迁自己没有做具体的分类,只是就每个时段内文本之间大体存在的共性做一个概括,以突出其 强调的时间轴的线索作用。
书中为我们展现了西方人在认识中国时惯常使用的两种做法:与其母国文化进行比较,或从中国的现实中归纳某一时期中 国的特色。前一种做法是葡萄牙人派瑞在16世纪所写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开始使用的,当时他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中国法律的弹性特色;后一种方式则从马 可·波罗时代就已开始使用,讲述的多是西方未有的“中国特色”。两种做法的区别仅在于表现形式,因为第二种方式虽然未有明确的比较法,但还是将西方的现实 作为默认的参照系。直接比较法的运用是在双方皆有但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存在,而直接讲述中国特色则在西方未有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即可。这种比较的意识,以及他 们用来做比较的参照物,就是所有描述中国的西方论者共同的前见。
面对异质文明时,特别是这种文明不易直接用自己所熟悉的逻辑来解释时,用比 较来凸显差异,由差异来确定这种异质文明的特色,是一种自然的做法。这种描述方式,并非只应用于西方人看待中国时。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容闳等人回乡时,对 家乡人讲述自己在外修习之学业,就概括地以考秀才、考举人来解说。曾经有论者认为留学生们的这种表述方式是他们对自己留洋经历的不认同,其实不然,在一个 文化圈之内,只有用其所熟悉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才能让对话者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了实现顺畅交流,只能以曲解为代价。
通过比较,每一种文化都能认识到他者的存在,而他者之所以被感知,就在于其特异之处。因此,《大汗之国》所列举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本,都是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一次追寻。
当 比较成为一种通例,我们只能从比较的出发点去判定比较的用意所在。猎奇、反思自身的文明、为着现实的政策或利益、文学性的考虑、论证某一理论的证据所在, 都可以作为比较的目的,将这些文本中的目的性揭示出来,也是《大汗之国》要解决的一个任务。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可能的目的性在某个文本中并非互斥,相 反,它们可能同时出现,这正体现了各类文本的复杂性。仅从启蒙时代而言,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赫尔德等人对中国的论说,就往往兼有反思自身文明和 论证自己提出的理论等几种目的,他们所建构出的中国形象也因此显得较为立体且引人入胜。
对他者的观测永远不是单方面的,只有将所有观测过程 都呈现出来,才能将观测的意义完全说明。西方人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特色自会有所感知;亲历者往往震惊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之处,便从现象入手进行描摹,未 曾有过亲身经历的论者则在已有的现象描述基础上进行归纳阐发,或是单纯寻找母国文明的反面,将若干反面因素进行拼接,造出一个理念中的中国。这些相对独立 的观测有一个成立的基础,就是西方人作为外来者去感知中国。一旦中国人进入西方世界,新的问题便产生了:如何观测那些作为外来者的中国人?如何通过这些个 体或共居的某些群体去观测中国的文化?再进一步:当观测者作为本地居民,被观测者成为外来者,观测的出发点、观测体验与结论是否会和作为外来者的观测行为 大致相同?《大汗之国》专门以一章的篇幅讨论这一问题,将马克·吐温等人对赴美华工生活的若干作品作为考察对象,让我们看到,当中国人进入西方,对他们的 观测夹杂了傲慢与偏见的情绪,丑化的手法和因陌生而产生的恐惧感。这样的态度与当时美国对华工的普遍态度极为接近,这样的群体意识,以及出自现实的利益考 量,促成了排华法案的出台,后来又愈演愈烈,塑造出了超级恶魔“傅满洲”的形象。也许,保持距离感是尽量减少观测中的偏见必备的要素,当中国人出现在西方 普通居民的面前,他们可能是产生了文明的自卫心理吧。
对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魅力与危险并存的神秘国度,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 意识普遍存在。中国受到西方的关注度极高,这和它的历史、文明特色与区域地位关系密切。然而,中国也并非是惟一受到注意并被反复观测的国度,西方对中国的 观测结果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并非不会出现,甚至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也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中国学者葛兆光近年来所做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工作,以及梳理“中 国”这一国家认同观念的著作《宅兹中国》,可视为《大汗之国》的同类作品,它们分别从西方世界、东亚世界和中国内部来观测、审视中国,若将三者做横向的比 较,我们看到的中国会更加立体。
史景迁在概括《大汗之国》的立意时说:“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对 他而言,中国是观测的对象,也是文化刺激与回应的案例;对我们来说,中国却不只是观测者建构的文化形象和学术研究的个案,还是我们所在文明的渊源,宅兹中 国,信哉斯言。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