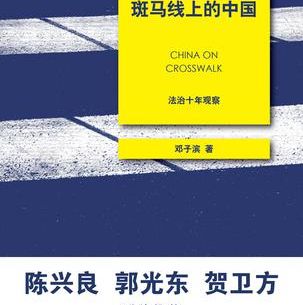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张伟/文 邓子滨先生撰写的《斑马线上的中国》,为其十年法律评论文章的合集。从中读者不但能看出作者一以贯之的法治思维,也可以明显感知到文笔的渐趋老辣。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可以作为书写法律评论的教科书:用语温和、说理透彻,言简意赅的形式也极其符合报纸的版面要求。一如当下所有的法律评论文章中显而易见的“缺陷”——就事论事尽管吻合了时效性,却会削弱文章的深刻性和整体性,本书亦不例外。但这与其说是评论文章的弊病,不如说是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狐狸与刺猬”暗喻在当下语境中的复活。
作者关注的事件极其庞杂,本书评论的对象包括了测谎仪、汽车安全带、二奶、酒驾、城管执法、许霆案、刑法修改及律师制度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作者的法治观是具体的,而绝不是对法律条文诘屈聱牙的复述或阐释。同时,政治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之间的龃龉,在作者也这里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具体法治将权利作为构建政治秩序的唯一考量,其余诞生于启蒙时代的言辞说教,甚至法律“拟制”因为不能代表个人的意志从而不值得过度关注。犹如历史学家贝克尔所说:“一切按法律办事,这种热情并不意味着无望而沮丧的个人会转向另外的、超过保护自我所需要的限度的权力;它只是一种本能,人民将众多才智中的一种,有效地用于实现他所向往的目标。一个仇视个人的政府,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的政府是‘伪政府’,它的法律是‘伪法律’。……在成文法之上,是高级法。国家的法律如果不代表个人的意志,就不是法律。”贝克尔式的法治论无比仰靠个人意志,其政治秩序的基础在于个人对法治的信仰,同时还蕴含着对暴政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反抗权。显然,本书作者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因为具体法治着眼于当下:创世论不能触及,末世论也无力探讨。
事实上,“法治十年观察”作为本书的副标题显得无比贴切。作为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以让后人对权利的中国之路做出综述,也让他们看清法治这种宏大的语词背后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遗憾的是,几乎每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这些琐事之中。作者对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并不抱怨,他甚至试图以专业化的言说方式参与其中。这说明他并不是自由主义狂飙运动的鼓噪者,而毋宁是沾染了法律人深入骨髓的保守主义特质。不过,读者仍可以总结出本书逻辑上的一致点:守法正义、同情弱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这种行文逻辑中,作者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法治布道者形象。但和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一样,本书试图阐明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背后隐含着关于规则的“拉锯战”:斑马线已经画好,而行人和驾车者却总是为自己的便宜随意践踏。因而,在作者眼里,人们遭受权力侵凌的原因并非犹太-基督教中约伯式的“原罪”报复,毕竟约伯本人对耶和华的律法是无条件遵从的。“就斑马线上的国民表现而言,不得不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是失败的。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教导成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守法者。……因此,斑马线问题,应当从娃娃抓起。”与梅尔维尔《切雷诺》的意图相似,作者试图将“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民美德同洛克式的自由个人主义”糅合在一起。不过,正如赫尔岑在《彼岸书》中说:“各世代皆自以其本身为目的。自然非但不曾以一个世代作为达成某未来目标的手段,而且未来根本非所存问;她有如克里奥佩特拉,宁以醇酒溶化珍珠,取片时之乐……”。唯有信奉历史铁律的人寄希望于未来的某一天实现某种梦想,而那些具有兰克式“现实感”的人都明白魔鬼就在眼前。“活在当下”即意味着每代人听从时代的召唤,并勇敢地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作者承继了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的思维,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增长幸福,因而要尽可能排除减损这一幸福的因素。可以说,所有的惩罚都是损害,它之所以被允许,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危害;而如果刑罚造成的损害大于要防止的危害,就意味着刑罚的使用代价过高。”与此同时,在作者看来国家权力机关在法治的图景中承担着较之个人更为重大的责任。“法院的忠诚应该首先献给法律。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对法院有合理的期待,不能赋予法院太多与法律无关的使命,社会效果虽不得不考虑,但首先要考虑维护法治;二是法院不能随意突破法律,让人们觉得善举比法律更重要,从而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需要提及的是,在犹太-基督教政治传统的“约法传统”中,人们只有遵从约法(如摩西十诫)才能摆脱埃及的奴役抵达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
尽管表现出了强烈的自由主义式法治观,并将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化行使纳入政治视野。但不无遗憾的是,作者有意将作为政治概念“人民”和作为法律概念的公民混同。——本书的激进气质由此也被隐瞒的无迹可寻,从而成功变身为中规中矩的常识。“正是一个一个的人汇聚起来,才构成我们政治话语中的‘人民’,而人民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以及执政的起点和归宿。”人民唯有在制宪的时刻方能出场,在常规政治中仍然时时可见人民的身影,这纵使不是民粹政治爆发的前兆,也会是篡取人民主权的偶像崇拜——人民沦落为政治修辞意义上的主权者,无法享有常规政治中的法律权利。事实上,尽管作者对现状多有批评,但他绝不是挑战者,而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政制必备的建构者。
作者信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在分析城管的数篇文章中,他将城市与农村、好人与坏人都纳入到讨论的范围。“城里人的利益肯定是人民利益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利益的全部,所以不能以此僭称‘人民利益’。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一个人以具体的行为踏入违法的领域之前,并且在经司法机关裁判之前,谁有资格宣布人民中的某一员是‘坏人’呢?法律只有连‘坏人’的权利都不侵犯,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好人。”事实上,共和政制最大的忧患不在于权力的肆意胡为,而在于公民道德的腐坏。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制——这是人民主权理论的逻辑终点。
托马斯·潘恩式“常识”的黄金时代早已不再,而今摆在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实现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是为某种理念做申辩。我们生活的时代极其排斥这种政治担当,每个人都面临着十分具体的琐事,这些琐事既可以看成是生活的必需,也可以视而不见;既可以将之归结为天赋人权的“高级法”,也可以弃之如敝履。总之,无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换来的要么是置若罔闻,要么是一片嘘声。某些专家已经沦落为经常肆无忌惮冒犯人们常识感的背书者,他们遗弃的岂止是技艺和德性。太多的政治理论试图在中国实验,以致于人们应接不暇,不知道该相信谁。鉴于声誉已经败坏,专家式的再启蒙还没有开始就已在人们的常识感面前无耻地谢幕。但本书并未抱有启蒙的雄心,恰恰相反,作者试图将专业知识和正义的理念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运送给读者。但如果从本书关注事件的复杂性上就推断出作者秉持法律万能论,凡事都想法“治”——这种极端的立法论并不符合作者的旨趣。实际上,他一再强调立法要划定公与私的边界,在私领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