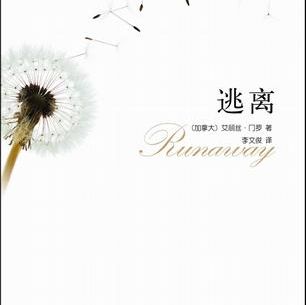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夏一璞/文 2013年10月10日以前,在亚马逊上搜索《逃离》,或许会以“逃离”为关键字出现一大串书目,而10月10日以后,与《逃离》相联系的是满屏的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名字,满屏的缺货,满屏的预定。洛阳纸贵的神话从莫言演绎到了门罗,只是这一次,并不是读者离奇的多,而是书店真的准备不足。
中国舆论热炒村上春树,国际上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更为看好,爱丽丝·门罗谈不上籍籍无名,但也绝不是聚光灯的焦点。对当今中国而言,无论是地缘性还是政治热度,加拿大都是一个平淡而遥远的存在,那个在加拿大小镇上打发了将近一生时光的,以书写普通女人为业的看似普通的女人,就更加陌生了。可是得奖之后,各种溢美之词开始井喷,诸如她的短篇小说颇具欧·亨利的神韵,不失契诃夫的悲伤。出版商也迅速嗅到商机,虽然爱丽丝·门罗作品的群众基础不算好,但与村上春树和阿多尼斯不同,她超越意识形态的写作更容易在中国获得畅通的发行。
舆论中对门罗讨论最多的是“为什么是她”,其实尘埃落定,我们不如看她为什么那么好。
海德格尔认为,美没有本质,更不可言说,因为美是“在者”而非“存在”本身,“美”是“真”的派生,是“存在的真自行置入作品”。存在主义对于“美”的见解,一语道破了艺术之美的真谛——有真自美。门罗的文学之美,就在于她的真。
艺术家对“真”的体验多种多样,可能是丰富而冒险的生活过,也可能是丰富而冒险的观察过。比如说,爱丽丝·门罗,在爱河的岸边看着他人的爱恨沉浮,而自己则如处女般生活着。她在访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她的“老处女”情结,“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当处女年华老去,自我厌弃所引起的敏感与多疑,被某时某刻的某一个场景触动,即可迸发出强烈的火花,点燃潜藏在心灵深处隐秘的激情。
在《逃离》中,无论是卡拉,朱丽叶还是佩内洛普,都是加拿大小镇生活中最常见的少女与少妇,或柔顺,或倔强,或奔波于田间地头,或流连于青青校园。门罗熟知她们的一切,洞悉她们的内心,甚至于她就是她们中间的一员。上天垂怜,赐予她敏感的心灵,于男人女人们平淡无奇的举手投足与眼波流转中捕捉到那转瞬即逝的厌倦和不断积累之后而萌生的“逃离”的闪念。当“逃离”被门罗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固定在她的文学中,故事就可以扩展出多种可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试图逃离或者实践逃离的女人,这些女人的命运或许与你相似,或许与我相似,在逃与不逃的边缘,有挣扎,有妥协。
大陆中译本为《逃离》,台湾译本为《出走》。“出走”更容易让人联想起 19世纪女性最伟大的出走——娜拉。在《玩偶之家》的戏剧冲突中,娜拉的出走显然不是隐秘而冲动的,她更像是一份直白浅显的女权宣言,政治意味远重于女性对自身情感、欲望的审视和珍重。娜拉的出走没有任何门罗式的惊慌,是成熟而坚定的。然而,这种坚定在娜拉出走之后,戛然而止。于是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或许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太过消极,不可接受。然而,一个生活在小镇上,对女权并无特殊立场的女性作家,为我们重现了这最可能出现的一幕:出走与回归。她的逻辑是,一个女人忠于内心的一次冒险,一个女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即使起点就是终点,可谁能说,她一直就在原点呢?无论是娜拉还是卡拉,她们的出走与回归,都不是可耻与可怜,当一个女人出于本心做出决定,即使后来反悔,她做决定的当时当刻,一定是无比坚定的。那么,对于欲望本身而言,它就是被满足的。而生命的激情也在逃离或出走的那一刻,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阅读《逃离》本身,脑海里常常闪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是否只能回来?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蓝》中不断询问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未来是否真的战胜不了我们的过去?门罗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宿命论者,她允许女人挣扎,反抗,却不看好命定的结果。“相信命运,跟着命运走,不相信命运,被命运拖着走。”门罗没有采取这类强势的男性话语,却用看似琐碎、片段化、跳跃性的叙述隐晦的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逃离”,在门罗的文学里,似乎更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表达,是一种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满足的仪式。
对文学与作家的评论,我最赞赏前苏联文学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描述,“文学是最壮丽的事业”,因为它需要一个人用一生来体验,来实践。“我生活、工作、恋爱、痛苦、憧憬、幻想,只知道一点——到我成年的时候,或者甚至我年老的时候,迟早我是要开始写作的,但是我之开始写作,绝不是我以此为任务,而是因为我的整个身心要求我去做这件事。”好的文学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金蔷薇”,是作家“用几十年的时间筛取着数以百万计的细沙微尘,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聚集拢来,熔成合金”。门罗的写作生涯完整地呈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对文学和作家的理想,她用几十年的小镇生活,把女人们内心隐秘的欲望、冲动、绝望和回归一一收捡、打扫、整理那些“珍贵的尘土”。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