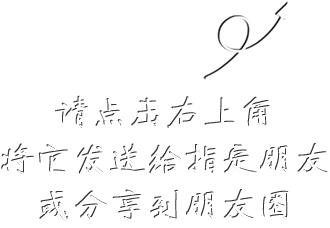思郁/文
一
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简称《艾希曼》)最早是以五篇文章连载的形式发表在1962年的《纽约客》上,内容是基于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所完成的一份报告。之后,阿伦特对发表的这些文章进行修订,1963年5月出版了英文版书籍,次年出版了德文版。中文简体版出版于50多年后的2016年。
《艾希曼》的中文版虽然姗姗来迟,但是这本书中的关键概念“平庸的恶”,我们绝不陌生。只要有关于纳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等话题的书籍,总会提及“平庸的恶”。这是阿伦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两个概念之一,另外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当然不是阿伦特的发明,但是当阿伦特用其概括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时,极权主义变成了一种对“极端的恶”的最准确描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一目了然,阿伦特在写给美国友人玛丽·麦卡锡的信中就承认,“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就是相对于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提出的。
1964年,关于《艾希曼》的争论甚嚣尘上时,阿伦特有机会做了一个广播节目谈话,开始就说,想先对因为《艾希曼》引发的争论做个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她说,这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是从一个案件事实中明确得出来的,“我指出了一个因与我们关于恶的理论相龌龊而令我震惊的事实,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种虽真实但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最令她感到奇怪的地方还在于,耶路撒冷审判处理的本来就是一个得到判决结果的案子,结果她现在被告知下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下判断”。
这种对她的书籍的误读让她困惑不安。要知道,当一个在特定语境中有着具体含义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当时的具体语境,经过传播学的过滤和越来越多人的误读,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庸俗词汇,变成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需要理解的一种公众意见——而这种意见与原著中所要表达的含义很可能大相径庭。
顺便多说一句,孙传钊编译过一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收录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中,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这是阿伦特《艾希曼》的中文版,其实那只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涉及到阿伦特原著的内容只截取了结论的部分。这个文本其实就是误读阿伦特最好的一个证明,抽离出原文的内容,省略阿伦特的论述过程,只借用结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建构一个新的争论语境,在这个新的语境中,对“平庸的恶”的概念进行想当然的重新书写定义。
二
《艾希曼》一书可以看作是纳粹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别传。整本书除了第一章讲述了庭审现场以及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对这次审判的重视之外,剩余的篇幅都是用来讲述艾希曼加入党卫军之后的经历。他如何从一名失业的工人加入党卫军,步步高升到中校,成为一名犹太人移民问题专家,并在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艾希曼是在1932年加入党卫军的,之前他是一名失业工人。1938年是艾希曼在党卫军中发迹的开始,他被派遣到维也纳负责“强制移民”,把所有犹太人强制驱逐出境。这是艾希曼在加入党卫军之后的第一份重要工作,他不但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还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了一种流水线的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移民”的效率。这次事件被上层党卫军树立为榜样和典型,他逐渐成为了一名犹太人移民问题专家。从此之后,逐步攀升,得到重用。从1937年到1941年,他得到了四次晋升,最终成为了一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授予中校军衔。此后,他受命参与到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来。从1941年到1945年间,艾希曼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工作,这位移民问题专家,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指挥官,直到最后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忠实地执行任务。
战争结束时,艾希曼被美军逮捕并关进监狱,但没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1945年11月,针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拉开序幕,艾希曼的名字频频出现,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艾希曼得知自己被曝光后,越狱出逃,几经辗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隐姓埋名,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逮捕,偷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十五条罪状被起诉,其中包括: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等。
对艾希曼的审判自1961年4月11日开始,持续了将近4个月,之后又经过上诉和判决。艾希曼在1962年5月30日被判处死刑,次日被执行了绞刑。
三
阿伦特得知艾希曼即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消息后,就向《纽约客》杂志主动请缨,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此次审判。为了这次审判,她推掉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计划,执意要去耶路撒冷,她心中有很多的困惑一直未解,之前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没有看到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纳粹战犯,心中总会觉得这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她向很多朋友都解释过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想知道一个执行过600万犹太人灭绝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之行对她而言,就像是履行一种重大的责任和义务。
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结果就是《艾希曼》一书的写作和发表。这本书在阿伦特的系列著作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流传最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她一直强调的是这是一本审判报告,从一个旁观者和记者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是一个普通记者绝不会用这种嘲讽的口味报道一次审判,也不会用“平庸的恶”来概括一个纳粹战犯,尤其是在以色列,这个聚集了大量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国度,把一个执行过600人死刑的战犯形容为一个平庸无奇、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官僚,这近似于一种挑衅和侮辱。一个记者只会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描述审判过程,不会做出判断。而阿伦特当然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判断。也正是这种判断激怒了一些人,甚至一个国家,与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为敌。《艾希曼》的争论绝非简单的“平庸的恶”这个问题,这大概是我们没有阅读原著之时最大的误读。实际上,这本书中涉及到“平庸的恶”这个话题的篇幅很少,我们对它想当然的认识更多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先入为主占据了我们的意识。阿伦特后来也承认,这种概括很容易让人误读为她为纳粹战犯辩护脱罪。但她的原意并非如此,如果我们阅读本书就能知道,阿伦特将艾希曼形容为“平庸”,更多的指向了一种不愿思考,不想负责的状态。至于她从庭审现场观察到的那个戴着黑边眼镜,驼背,头发稀疏谢顶,满口陈词滥调的艾希曼,确实毫无风采可言——但是这种印象可能过于主观,任何一个大人物,经过了多年的狼狈逃亡,被捕入狱,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希特勒如果站在审判席上,估计也是如此。再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当成为阶下囚时,我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青面獠牙的魔头。所以,在几年的争议风波之后,阿伦特说,如果有可能,她更倾向于不使用这个故作惊人之语的副标题。
撇开以貌取人这个层面的误读,我们也要认识到“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之所以经过了数十年之后依然能够引发人们的热议,说明阿伦特确实捕捉到了一些人身上或者说潜意识中的恶魔性。这的确是阿伦特著作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之一。我说的原创性指的是,我们无法通过表面的观察就轻易地作出论断,我们只能通过阅读阿伦特的著作和相关的论文,对这个概念作出丰富而精彩的解读,而不是通过那些批评者的断章取义来曲解阿伦特的原意。
在《艾希曼》中,阿伦特这段核心的论述值得一再提及:“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得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劲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所以“平庸的恶”绝非程度较轻的恶行,它其实是比“极端的恶”更严重的恶行,因为这种恶行是以虚假、和善和诱惑的面目展现出来的,更让人防不胜防。
四
《艾希曼》一书的写作对阿伦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催生了阿伦特后期的大部分著作的主题。这本书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它之前,阿伦特思考的是与极权体制不可分割的“极端的恶”;在它之后,艾希曼这个人物将她的关注点变成了思考“平庸的恶”——好人为何会作恶?阿伦特后期很多论文和演讲,包括她后期重要的两部作品《精神生活·思维》和《精神生活·意志》,某种意义上,都是由艾希曼这个人物的平庸性激发出来的。尽管外界对她的争议和谩骂不断,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个小人物的平庸性的特质。正是阿伦特的这种思考,将“平庸的恶”这个概念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已经不单单用来形容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纳粹战犯,还用来形容以后所有时代里,那些潜在的杀人凶手,他们不是恶魔,不是坏蛋,并非穷凶极恶,但是在某种条件的引诱下,他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屠刀,成为一个恶魔。某种意义上,阿伦特预见了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中提及到的二十世纪后半页大部分种族清洗,那些本来就和睦相处的邻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互相砍杀的仇敌,无数的灭门惨剧由此而生。
阿伦特在此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追问,如果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不纯粹是恶魔,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做出那些行为的?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1964)一文中,阿伦特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
在她看来,在纳粹时期,那些明哲保身、拒绝参与公共生活的人,虽然没有抵抗纳粹,但是这些人,却是仅有的敢于自己做出判断的人。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道德和价值体系都是陈旧的,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我们自动会选择某种已有的价值体系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并且遵循已有的先例经验进行处理。但是,对于那些不参与者而言,他们意识到纳粹的这种罪行并无先例可以遵循,他们继承的经验和价值体系中并无合适的判断标准。所以他们开始思考和自我发问,在纳粹犯下的罪行之后,他们该如何抉择。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决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什么都不做,“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些,而只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时,他们就会选择去死。不客气地说,他们拒绝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存”。而那些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人们所选择的做法,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思考,就把这种前无古人的罪行当成了一种习俗和惯例,按照原有的价值体系接纳进来。换句话说,纳粹时代的道德剧变并没有触动他们敏思的心灵,他们的思想没有悸动,他么的灵魂没有任何拷问的迹象。
在这里,阿伦特还对那种“我只是服从命令”的论调进行了反驳。服从当然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没有了它任何政治体都无法生存。但是服从是否就意味着不用担负责任呢,是否就意味着它只是那个命令的执行工具,并非真正的杀人者或者同谋呢?在这里,阿伦特说,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服从命令的人混淆了“服从”和“同意”的关系,将其等同。对儿童来说,需要服从的事情,在成人那里则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才可以。成人的服从中隐含的意义在于,他同意接受别人的支配,并且服从领导者的命令,因为领导者所发布的命令代表他们共同的意愿。那些服从他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他和他的事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从,领导者将是无助的,他根本无法完成任何事情。
那些拒绝参与纳粹公共生活的人,其实代表了他们拒绝服从,换句话说,他们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决定不“同意”纳粹的统治。假如将这种状态理想化,就会发现,如果有足够多这样的人拒绝了支持纳粹,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抵抗,纳粹政府都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其实是一种非暴力抵抗的形式。而那些参与到纳粹的犯罪过程,并且用“我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这样的陈词滥调为自己开脱的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该是“你为何服从”,而是该追问“你为何同意和支持”。在此,语义的转换之后性质完全不同,一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人变成了支持和同意罪行的共谋者。
五
《艾希曼》一书中,关于“平庸的恶”的说法绝非阿伦特的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也绝非为纳粹罪行开脱。当得到艾希曼被绞死的消息后,阿伦特在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他们绞死了艾希曼。并不是说这很重要,而是如果他们不把事情以种种唯一符合逻辑的方式结束,他们会让自己显得无比荒唐。我知道有这种感觉的人不会多。有一个改革派拉比出来为他求情,批评以色列的处决‘缺乏想象力’!还有其他人呼吁以色列应该达到‘神的高度’,这些都让我很反感。”
艾希曼的恶行当然要受到惩罚,他在执行犹太人进入死亡营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的死早在审判之前已经有定论了。以色列之所以大费周章,不惜冒着违背主权公约和国际法的危险,将他从阿根廷绑架回国受审,是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一种政治策略。他想通过这种形式,将以色列打造成犹太人世界的中心,告诉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找到家的归属感。通过讲述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历史,来重新团结所有的犹太人。
但是,对一次审判而言,它似乎承担不起这样大的历史重任,而且很容易偏离审判所追求的正义和公正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嘲讽这次审判是一次政治作秀。在她看来,对艾希曼的审判只能从这个人的经历中找寻他的犯罪证据,与艾希曼本人无关的犹太人事件,就算有再大的杀戮和不公,也与这次审判无关。《艾希曼》一书中最多的争议就在于,阿伦特对待自己同胞的冷漠口吻,她完全理性地讨论一次庭审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程序,就好像受害者不是她的同胞,与她无关。正是这种貌似冷血的口味让她受到犹太人的排斥,好像她根本不热爱自己的同胞,不热爱自己的种族。她干脆承认了这一点,她说她不但不热爱自己的种族和同胞,甚至不热爱任何种族,她热爱的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
这大概是《艾希曼》一书中最大的分歧,她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审视这次审判,而以色列最想做的就是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对犹太人历史的审判,从而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国家重新审视犹太人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了,“平庸的恶”从来不会消解掉恶的存在,它是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恶行。而这种恶行与我们不愿思考,甘愿成为一个服从者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那些不能运用自己理性思考,进而作出判断能力,只是一味盲从的人群。如果阿伦特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没有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没有对这次审判进行批评,只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作出客观和公正的陈述报道,她岂不是变成了她笔下的那个“平庸的恶”的形象的最佳注脚吗?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