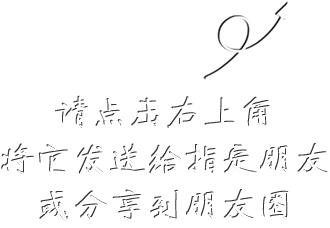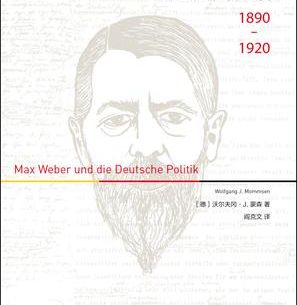

维舟/文
伟大的思想往往都是含混甚至潜藏着内在矛盾的。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这位“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身上似乎再度得到了印证。在世人的印象中,这位曾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奠基于新教伦理的社会学家自己就是一个冷峻的清教徒,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把他所提出的“学术的价值中立”等命题看作是他一生的信念和生活实践,因而当人们得知现实中的韦伯竟然是一个热情投入政治活动的民族主义者时,不免要大吃一惊。
的确,韦伯一生都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现实关怀,恰恰相反,现在看来很明确的一点是:和马克思一样,正是出于对现实中政治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和敏感,才促成了他的问题意识。他对统治合法性、官僚科层制等议题的研究,虽然一以贯之地强调这些并不能为实践层面的问题提供客观答案(用中国话来说,他拒绝成为“国师”),但都或多或少是受他对现实的思考所触动。认为韦伯主张“学术价值中立”就是躲进象牙塔,那是对他的误解,借用马克思那句名言,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韦伯不是韦伯主义者”——他倒更接近一个有节制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学术不应受政治干预、但也应拒绝那种干预政治的诱惑;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当隔绝于现实政治之外,相反,那能激发他的思考,只是这两个领域决不能混为一谈。
这么想没什么错。事实上,这一个多世纪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造成社会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完全缺乏现实关怀,另一则是掌握了一点理论就沾沾自喜,恨不得将眼前的世界都敲打一番,认为凭着自己所具备的这点知识权威即便不足以改造出一个新世界来,至少也能指导他人如何抉择价值立场。韦伯避开了这两个巨大的陷阱,但看起来似乎踏进了第三个:由于相信政治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的不同实践领域,因而当他作为一个政治介入者出现时,他似乎缺乏反思地接受了当时德国所盛行的政治思想中蕴藏的一系列前提假设。
于是,我们凭着后见之明看到了这位伟人身上的“局限性”:他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因为他预设了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是政治的最高使命(这是19世纪极为典型的德国思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因为大国地位是德国政治唯一值得追求的终极目标,其它所有一切都服从于此——议会民主制只是实现这一点的手段。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机制下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国家的实力与威望,并为推选出的领袖赋予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那些“追求富强”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政治的要点并不是落在“以最小代价实现个体的幸福”之上,而是落在“不计代价地获得国族的富强”之上。
这当然是一种在原本落后的民族国家中才会显露出来的心态。无论是“落后就要挨打”,还是“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所表达的都是一种深刻的怨恨:我们也要和早先的列强平起平坐,甚至超迈之。正如《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所说的,在19世纪德意志有教养的市民内心最深处的悲痛,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被忽视感”,在这种自卑又自尊的折磨之下,进而认为自身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应再承受这样的不公命运,而那就必须自己奋力去争取。“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个理想,始终是韦伯的核心关切”。
没看到这一点是无法理解韦伯的。德国历史学家鲍姆加滕在1861年就曾痛心地严厉批评德国人虽然富有教养、多才多艺,但“我们在政治上是个极为愚蠢的民族,严格说来是个劣等民族”,因为“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突然在实际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都免不了这样几种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倾向于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韦伯同样对德国政治生活中畸形的一面持有强烈批评态度,但在本质上,他其实同样对德国被排斥在列强对世界的分割之外耿耿于怀,同样认为大国所拥有的才是真正的政治生活,小国则无足轻重。
韦伯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的权力利益高于任何政体问题(民主宪政或帝制),民主观念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其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在功能上能确保获得国民支持来推行真正有利于国族利益的政策。他之所以抨击那些迷恋王朝声望和推崇土地兼并的大日耳曼主义者,原因也只是因为他觉得那会在实质上阻碍德意志民族权力的最大化,而不是他反对德国的扩张——恰恰相反,他强硬支持民族利己主义,认为一个伟大民族必定会“首先追求权力”,这是历史的必然。
他本人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扩张欲的观念内核,就是统治阶层“抱有以国家为取向的权力声望感”——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本人也正是如此,每每总是从国家而非社会或个人的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所不同的是,他在意的并不是统治阶层自身的荣耀,而是认为国家政治的最终使命是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复兴。他坚信,唯有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结合完全的契约自由,达到经济制度的高度合理性,加上民主政治和精英官僚体系的配合,才能在技术层面使德国的竞争力最大化。他不大谈起个体利益,是因为他相信“每个人的福祉都与德国的实力息息相关”,换言之,这种竞争观念非常接近于总体战,即如何最优化地发挥国家的最大潜力。
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将议会民主制仅仅看作是一种实现大国梦的工具了。既然他对大国理想、民族利益至上和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图景毫不质疑,那么必然的推论就是:在现阶段,阻碍德国自觉伸张其最高利益的,恰恰是其落后的政治体制本身。德国的资产阶级到来得太迟,又没有意愿和能力自觉地完成其政治历史使命。
在此我们应具的“理解之同情”是:韦伯的思考,是当时德国政治危机的产物。正是凭借着对这一危机的深刻认识,他看到死守着自身狭隘利益的保守派官僚已落伍于历史潮流,看到传统自由主义宪政之下那种作为独立个体的政治舞台的议会已失去作用,也看到软弱的议会制度在面对政党和小集团的多元化局面时运转不良,已不再能完成民族政治的最高使命。他在此所在意的不是这些政体的性质如何,而是本着工具理性的精神重新设计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使其能以惊人的高效率推进停滞不前的政治进程。基于此,他认为,除了直接诉诸民意来推选出一位能贯彻自己确定政治目标的恺撒式议会党团领袖之外,别无他途。他将中立于各政党利益之外,因作为人民总体政治意志的代表而具有超然魅力,而选民的功能就在于“识别领袖”。在这里,他考虑的重点不是制衡此人的权力,而是当时的德国因缺少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政治家而一再令人失望地决策失败。
这绝不只是韦伯个人的想法而已。本书作者的曾祖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就在其代表作《罗马史》中将恺撒视为超人和理想的罗马人,尽管不少历史学家将他视为出于个人野心而将国家推入危难的政治骗子。吉尔伯特·海厄特在《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一书中就认为,蒙森写作此书的灵感源于1848年的惨败,“我们遗憾地看到……由于受到所在时代和国度政治憧憬的误导,蒙森完全选错了对象”。然而他和韦伯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学术中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至少证明这种结构性困境绝不容低估,以至于连这两个堪称最杰出的德国心灵也难以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想法在不久之后的德国历史上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一个突破了几乎所有约束的政治领袖将德国拖入了世界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而卡尔·施密特,这位韦伯的学生、德国“最危险的心灵”,正是基于韦伯设想的逻辑推衍来为纳粹的政治理论摇唇鼓舌。尽管很多人愤怒地驳斥两人思想的继承性,认为师生关系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韦伯的学生中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但这不如说是人们难以接受韦伯思想中的矛盾微妙之处,也是因后人常不由自主地将其视为在价值上民主取向的思想家,而忘了他却是撇开价值判断、纯从工具理性的层面来思考这些政治制度设计的。
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正因此,韦伯是格外清醒的。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韦伯率先看到,现代的选战式民主政治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古典民主已不可能,而只能是少数精英借助庞大的理性科层体制来管理国家,而现代政治作为一项承担特殊责任的职业,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此为志业,那就是职业政治家。他在意的不是民主政治内在的价值(“民主本身就是善”),而是现实操作中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如何通过利益集团博弈、妥协、乃至政党分配来有效运作。近百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倒是在顺着韦伯的思路在走,许多重要的民主理论家如达尔、萨托利、李普曼、李普塞特等,都程度不同地承认职业化政治精英集团博弈是现代民主政治无奈的现实;而阿罗和布凯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更是指出,通过选票来使个人偏好为共同利益行动这一现代民主的基本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韦伯对当时政治危机的应对和设想,其实远不是那么容易推翻。
将韦伯简单地视为一位在政治上误入歧途的思想家、或在读了本书之后只得出“伟人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那绝对是误读,也低估了韦伯思想的深度。他所着眼的是自由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困境,实际上,这是他以自己的政治敏锐,察觉到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那就是民主是否具有能为一个国家/民族带来生存、荣誉和强大的外在价值。罗伯特·达尔就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现代民主理论与古典民主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是价值导向的,而只有工具性的好。
在二战之后,新一代的德国政治思想家代表是汉娜·阿伦特这样推崇民主的内在价值的学者,认为共同体而非私人生活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类存在,而这只有在共和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至于“效率”则本身就不是考虑的重点。的确,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韦伯当初过度追求国族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和幸福的保障,但这仍未能回答韦伯的核心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最有效地应对国际竞争和时代挑战?在经历了20世纪的残酷政治实验和计算机时代之后,我们现在似乎已能回答:看似分散、愚蠢而缓慢的民主制,结合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可能反倒是最高效而具备外在价值的,不过,那不是因为它总能做对事,而是因为它能少出错并快速自动纠错。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