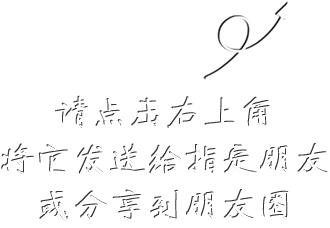陈芝/文
李劼先生的《论红楼梦》是我在高中时期除《马恩全集》以外读过的最好的文学评论,大学期间也不止一次向朋友推荐过此书,七年以后借新版回顾,所生出的头一感慨便是,文化人能写出的最好的书与最差的书就是这种类型,爱者手不释卷,恨者弃之粪土。如果不能接受作者先在的价值立场,读此书仿佛自寻煎熬;反之,易有醍醐灌顶,相见恨晚之感。
不过说是文学评论,如果你想在此寻求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它是不够格的,作者对中其意的红楼人物的溢美与对厌恶者的刻薄明显不知节制,使得很多人物被漫画式的夸张放大,变得像是其所评点的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部小说,而是一部低劣的同人作品,至于书中各种论断比比皆是的偏颇与武断更让抵触者添加了一条放弃的理由,如果之前还没有厌恶到家的话。
然而考虑到这是一部斯宾格勒式的论述,以上一切又显得理所当然,不如此反倒值得称奇了。换句话说,李劼先生是个才子式人物,写不出那种四平八稳让所有人都能欣赏的文章,自古以来这样人的共同特征便是实际上用激情而不是其他种种言语,因此真知与偏见交杂混融,不分彼此。谎言是弱者的专利,直言不讳是强者的特权,是以他们会比大多数人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绝大多数聪明人以其智力并非不能做到洞穿惨淡现实背后的阴暗,然而他们不愿承认真相,宁可自我欺骗,久而久之便如同皇帝新装的故事,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件美妙绝伦的衣服摆在所有人面前。
是以李劼先生的大部分论断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他生命中洋溢的激情损害了平衡能力,使他稍欠公正的比例感,或者说不能节制自己的尺度,让不习惯这种言语的素人觉得言语过分苛刻,缺乏理性中立客观,与你批评的对象有神马两样,进而站到对立面。然而如果你愿意忍受这方面的缺陷,那么这本李劼先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论红楼梦》也不可能不从中有所收获。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以外,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话莫过于李劼先生将红楼梦视为与西洋存在共时性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姑且不论自清代以来这所谓的文艺复兴指代的是何物,或许他说的是完成度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就他将文艺复兴视为对红楼梦的最大褒奖,也很能反映出他视野上的天花板,再怎么推崇洋大人,对洋大人的理解还是有所局限,到如今李劼先生也没有多少改变,这只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世俗知识分子的通病。
所以当他在本书开篇推崇贵族精神,也就不难发现这种不计功利为其深深称许的贵族精神固然超脱为蜗角功名,蝇头微利争抢地头破血流的绵羊走狗,但这种贵族精神只是世俗知识分子/士大夫意义上的,并且审美性更重,缺乏成为社会凝结核,更谈不上正直勇敢忠诚虔诚等社会性很强的人格特质。他们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可以洁身自好,但不可能开辟新天地,造就一个被否定的现世完全不同的理想社会。因为他们太出众了,以至于根本无法与庸众相处在一起,两者已经是不同物种,存在生殖隔离。
抛开这一点,他对红楼人物的归纳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红楼梦或者说东亚大陆本来就很匮乏土豪,也罕有成为或称许社会凝结核的思想资源,对朝廷来说这本身就有不服王化叛离中央的威胁。
李劼先生的创见是,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曹雪芹的写作可以或者说理当从人类精神面貌和命运处境的角度去赏析,政治学或考据功夫容易走进支离破碎的死局,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但又不仅仅是作者的自传,曹雪芹借红楼梦固然有追忆儿时似水年华的冲动,同时也在人生末年反复审视人类灵魂自身,对那些美好事物,就像贾府中唯一的净土大观园最终也落得陪葬的结局而感到愤恨与遗憾,世界毫无疑问最后将走向毁灭,用李劼先生的话说便是由色(现象)到空(虚无),但不同的东西被毁灭作者的态度也明显是不一样的,而阅读红楼梦,就应当与作者一起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精神风貌的衰落与瓦解,人的命运是否终究只是一场虚无,刹那的光辉转瞬即逝,转而被无边的空洞长久取代。这些问题可能有答案,也可能没有答案,但问题本身其实比答案更重要。
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们可以看到,在李劼先生眼中,红楼梦是一个走狗与绵羊的世界,走狗的粗鄙与绵羊的平庸替代了豹的进取与高贵,也就是奴隶道德取代了主人道德,不仅那超脱现实不计利害,对世界审美式的贵族精神已经难以看到了,就连像浮士德一样充满生机与动力的创造者也被时间湮灭,从充满进取精神的祖先开始,一代不如一代,逐步走向寂灭的寒冬,表现在红楼梦中,便是从荣宁二国公开始,经历贾代善、贾代化,到贾政、贾赦、贾敬,再到贾琏、贾珍、贾环,再到贾蔷、贾蓉等人,再以及他们的奴仆,人类在不断地堕落,道德文章不过是科场考试的投名状,礼义廉耻只是行走社会的门面伪装,仅知皮肤淫欲的纨绔子弟忘记了祖先的德性与功业,并逐渐迈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下场。
在整个红楼梦里,除了贾宝玉、柳湘莲等寥寥游离在世俗秩序以外的几人,其他的男人基本上都不是好东西,越是接近主流就越容易混帐,他们既无法为世界注入创造力,也给不了女性好的归宿,只能被欲望操纵像死魂灵一般游走,最终浑浑噩噩的死去。而最令人绝望的莫过于,即便本质上是好人的贾宝玉,在对待女性上也有其天花板,金钏因其而死,纵然事后独自一人为其哀悼,但过后该调戏丫鬟继续调戏丫鬟,再难见到想念金钏的痕迹。晴雯被赶出去时即便对袭人有所怀疑,但三言两语以后就不再深究此事。深怕其寒了心,红楼中最多情,最体恤女性的宝玉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那些色欲顽主呢?
而作为男人附庸的女性,在整体上比男人堕落速度倒是更慢,尽管也在向走狗与绵羊演变——后者用宝玉的话来形容,便是从珍珠变成死鱼眼睛。整部红楼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莫过于以林黛玉为首的大观园中的小姐丫鬟们,作者倾尽心血刻画这群人物,不仅是因为其有对小时候一起生活的人物原型的思念与追忆,更重要的是这群锁在深闺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子,还没有被外界污染的年纪,因此尚保留了一份周围人都已经失去的纯真,她们没有自由,一举一动都要看家长与礼法的眼色,但也因此啼笑皆非地远离主流世界,省去了多少烦心事。
尽管我们只能悲观地预料到,倘若她们在俗世上走过一遭后,二十年后也无非王夫人、赵姨娘的下场,或是市侩功利,或是缺乏生机,沉沉如死木。但至少在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料到具体情节的小说结局以前,也就是贾府的败落破灭以前,这些少女还有机会享受这份奢侈。
用李劼先生的话说,曹雪芹对少女们的缺点多有无言的体谅与包容,反而因为这些小缺点她们因此更像是一群真人,远胜于被现实彻底夺去活力的王夫人贾雨村之辈。
倒是李劼先生自己,对宝钗苛刻地过分了,在本书论及宝钗最激烈时仿佛她就是此世之恶,公正地讲,就算宝钗在少女当中较为庸俗,但体谅一个家境已经没落,地位势力在四大家族当中最低,而不是传统理解或者李劼先生误以为最高的年轻女子,父亲去世,兄长又靠不住,为自己的未来有所图谋实在是人之常理,其手段也无非大学寝室斗争,连办公室政治都不到,与王夫人的手段,贾赦的淫乱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黛玉是曹雪芹心目中最纯粹的精神寄托,因此高标地像是远离人间烟火,那么宝钗就是为生活而一步步妥协的写照,是站在另一端的标尺。在宝琴她们到来以前,宝钗的地位在小姐们当中其实最低,不像黛玉是贾母最宠爱女儿的孩子,宝钗与贾母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其身份只是一个客人,因此对贾府中的人事纠葛,宝钗无不有所留意,随便一个小丫鬟都知晓其声音姓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哪日过线,活的最累。即便因此显得功利,但也不曾像大观园之外的污秽赤裸裸地伤害他人。假设她是男儿身,肯定比她哥哥更有创造力,做出一番事业,而今却不得不自我压抑。
然而两人的结果算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正当的追求却被现实无情地粉碎,在小说中曹雪芹不住地暗示所有人无非是心死或身死的下场,而心死往往更早于身死,而好人,或者说拥有创造力和精神上不肯阿世者更容易走上这么一遭。对此李劼先生总结的一语中的:红楼梦是绝望对绝望的自述,它以惊人的气魄直面死亡,如果说人生就是畏烦闷,那么红楼梦对死亡的畏惧不是对生命受到威胁——因为人终有一死,而是对灵魂的残缺感到悲愤。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灵魂的阙如,使得时间变成虚无,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作为伦理实体的善找不到延续的可能,无法敞开显明自身,因此只能在永劫轮回里与恶纠缠不清,同归于尽。
于是,拥有创造力身为贵族的豹与不计利害审美似的豹的精神逐渐灭绝,只有作为顺民的绵羊与作为帮凶的走狗活了下来,而如果有机会绵羊与走狗就会撕下伪装,化身为豺狼。但是他们活的同样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被侮辱与被损害,而且人格也被反复践踏扭曲,毕竟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机会化身为豺狼的。而假如里中有曾觉醒者,也不过是对四际无人的旷野大声呼喊却得不到回音,大多数人依旧如虫豸一般生存,其中苦中作乐者宁肯自我欺骗,也不愿承认惨淡的现实,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久而久之,他们成功欺骗到了自身。毕竟,将痛苦解释成幸福,比将幸福真正追求到手,无疑简单太多。
李劼先生的《论红楼梦》其实有个副标题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这个名字说来不大妥帖,我们固然可以从红楼梦中见微知著,看到其置身社会的颓唐败落,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一个文明的末世景象,它的青春早已结束,它的现实只是死路一条。所谓凡鸟偏从末世来,哭向金陵事更哀。在此之后要么继续死而不僵,要么迎接新生。所有人都希望劫灰落地以后可以开始新的轮回,可将希望想象成现实,也无疑比把希望演变成现实简单太多。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