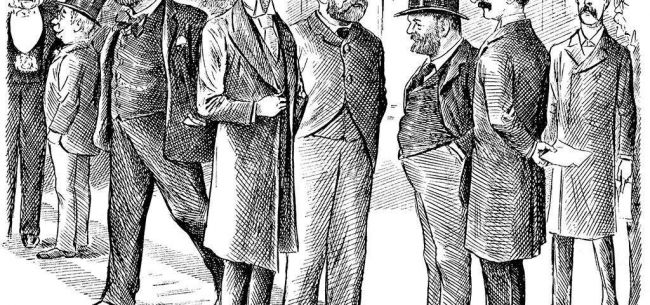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所学术风格剑走偏锋的学院。教授里头最著名的是彭慕兰,他在《大分流》里论证,欧洲在18世纪之前,生产力远远不如中国。在观点惊异、新颖程度上,弗农不遑多让,他指出英国的现代化最大推动力是陌生人聚集。
通常的教科书讲述现代化进程,按照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顺序,一步步过来,现代文明水到渠成,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罗素、马克思、约翰·穆勒,各派别的思想家都一致这么看待的,而詹姆斯·弗农以革新者的姿态宣布,以往观点都错了,英国是19世纪一下子爆发式冲入现代社会,仿佛一头冲进瓷器店的公牛。
旧时代的乡土英格兰
弗农认为19世纪之前的英国,跟法国、德国、意大利一样,均属于传统社会。在铁路发明之前,人们安土重迁,很少离开故乡。研究家庭社会史的学者劳伦斯·斯通发现,英格兰只有从男爵以上的贵族,才能进入全国性的婚姻市场,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方圆10英里内挑选配偶。
弗农搜集数据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在光荣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65%的英国人因为工作或婚姻前往他乡,这些移动是短途的,周期性的,离开的人大多还是要回到老家。就算是浪迹天涯、独来独往的流浪汉,行程也很有限,肯特郡的流浪汉移动距离不超过35英里。
这样的社会,必然是重视乡土人情的,类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描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
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英国有民主宪政,而中国实行东方式专制主义。弗农早就预料到这点,指出英国在19世纪后才有了现代意义的选举。尽管议会选举在18世纪中期就很普遍,但只有20%的选区出现竞选,因为一个选区里,就那么几个大家族,权柄在各家来回更替,选民的投票热情也不大。
所谓选举形式通常是这样的:想当议员的头面人物摆宴席,请乡里乡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整个过程很少有硝烟弥漫的政斗气息,反而充满了节庆的快乐气象。乡绅款待庶民,庶民尊敬乡绅,候选议员的政治纲领一旦跟本区利益抵触,便声望受损。
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一个政治家声称自己是爱国者,首先意味着他热爱本州,其次才是热爱联邦政府。英格兰也同样如此,乡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拿破仑争霸战是三四个世纪以来,不列颠遇到最大的外来威胁,即便到了这个时刻,许多英国人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清教徒的大本营东英吉利地区,地理与外界隔绝,没有征募抗法士兵。这里沼泽裸露,水系丰沛,天高皇帝远,政府力量很难进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才从这里动员到足够的士兵。
在苏塞克斯郡的小镇东格林斯蒂德,治安官调查询问了556个适龄男青年是否愿意战斗,有34个人已经入伍,有169人表示一旦法军真的入侵就会入伍,还有人表示只有法军到了本镇地界才会入伍,其他郡县是否沦陷,跟我们无关。
英国版“闯荡北上广”
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这世上的陌生人毫无交集,永远不会相识。一个住在腹地平原的村英国人,向他卖杂货的摊主,向他传教的牧师都是熟人,一辈子都碰不到几个外人,如果去伦敦打工,他会看到大街上黑压压的,到处是陌生人。他要和陌生的工厂主打交道,和陌生的租客合住,和陌生的路人挤巴士,与陌生人共处一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坐在咖啡店里的文人,观望着街上车水马龙,产生一种在庞杂人群里怅然若失的感受。华兹华斯用“流动的盛宴”一词,描述现代生活的脱序状态,诗人反复采用水流、激浪这些意象,来捕捉城市不断流动的感受。
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诉说道:世上最孤独之事莫过于第一次与伦敦街道的邂逅,他站在往来人流的中心,这些面孔穿梭不停,不与他交谈一词;男男女女匆忙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于陌生人而言却是谜一般的存在……
港台偶像剧里经常有这样的套路桥段,男女主角在地铁站、公园转角处擦身而过,非常凑巧得错过。这一幕绝无可能发生在熟人社会,小城镇里人们同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浪漫又忧愁的“擦身而过”,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特有现象,只有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陌生人之间在物理上会相处一室,在心理上却无限隔绝。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对此颇有感触,尤其是对北漂、沪漂而言,当他们从小镇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市中心,类似陌生疏离的感觉油然而生。戴望舒写《雨巷》,施蛰存写《梅雨之夕》,依凭的都是同一种都市生活情景。
城市的五光十色让文人墨客晕眩,却让学者更加镇定,詹姆斯·弗农敏锐地看到,在浪漫情调的表象下蕴含着危险。来到伦敦,相信一个陌生人是危险的,他很可能是个骗子、扒手。杂志提醒女性出行一定要结伴,不要在商店橱窗、公交车站徘徊,不要回应任何一个陌生男子的招呼。
把几十万陌生人放在一起,安居乐业,这是件难事,只有现代化的组织手段才能应对。在农业社会,相邻的村子经常因为争夺水源、田地互相械斗,《罗密欧与茱丽叶》里两大家族世代为仇的情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阿拉伯有句谚语:我和我的堂兄弟一起对付外人,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对付我的堂兄弟。
假设一个社会成功做到陌生人凝聚起来,那么它将获得巨大的收益。亚当·斯密曾推理:传统式自给自足的家庭,可以自己种田吃饭;但维持一个面包作坊则不同了,需要一个村庄的规模,维持一个面粉厂需要一个城镇,有足够多的消费人口,才能维持一个更高效的经济单位。詹姆斯·弗农抓住这个论点,在书中反复强调,英格兰是第一个突破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国家,富有最早、最成功的城市化经验,因此得以构建陌生人社会。
詹姆斯·弗农反复强调,“人多力量大”,其他现代化因素,新教伦理、科学革命远不如人口来得重要。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持相同看法,他说加速工业革命的不是煤炭,而是人口规模,催生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反过来,更多的劳动力聚集起来,支撑了规模更大的企业。
19世纪后期,兰开斯特郡的纺纱厂,员工平均人数从108人增长至165人,像帝国化学工业、联合利华这些企业巨头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无法想象,一个中世纪社会能存在如此庞大的经济体。
受雇佣的工人大多来自乡村移民,19世纪中叶,伦敦二十岁以上的人,只有一半是本地出生,其他工业化地带(苏格兰中部、南威尔士)四个居民里有一个是外地打工仔。伯明翰的外地人占总人口的41%,比伦敦还要高。1811年,只有伦敦的人口超过10万,而一个世纪后,英国有41座城市达到这个规模。把城市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不出差池,是构建陌生人社会的关键,而恰恰在此,詹姆斯·弗农犯下了关键性错误。
他和黄仁宇犯了同样错误
在华语学界里,跟詹姆斯·弗农观点最接近的是黄仁宇。辉格史学家赞美“英格兰人是自由的民族”,左派声讨“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詹姆斯·弗农觉得民主不民主,一点也不要紧,“陌生人”的聚集组织最重要。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落后,不在于君主专制,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管理效率低下,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万历十五年》的主旨高论,转化成村夫村妇都能听懂的大白话,就是“社会这么乱,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如果父母官掌握了数目字管理,我大明朝不可能完的”。
黄仁宇应该看看当时不列颠的情况,英国同样呈现小政府模式。在欧陆革命的184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力缺乏,13%的市镇几乎不存在警察局。在苏格兰最北部的斯凯岛,只有一个督察,他要走上3000英里,才能巡视完毕。
伦敦这样的大城市稍微好些,具有完善的警察机构,但远远不够控制局势,每900个居民只有一个警察,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平民与警察的比例为600:1,到了1881年,全国警察人数仅为3.2万。碰到大规模骚动事件(例如1926年的工会总罢工),政府还要另外抽调部队,才能压制场面。
英国统治的特色,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控制最大的统治范围。除了警察和邮政局两个机构外,一个普通英国人一辈子几乎碰不到衙门了,詹姆斯·弗农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直到20世纪初仍是小政府,还能治理得井井有条。
答案在于,《权利法案》、人身自由保护令、陪审团制度。英国的司法是公正的,获得民众的信服,英国的政府是良善的,民众不必担心横征暴敛。晚清大使郭嵩焘去了英国后,发现维多利亚女王虽然是个虚君,却仍受臣民的爱戴。他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中国人畏惧君王,只是畏惧其权势,一旦主上暗弱,底下人就起了不臣之心。
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商业化、具备契约精神的陌生人社会,能在专制政体中建立。在近代中国,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是因为这座城市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跟大清朝的腐朽气息绝缘。按照黄仁宇的理论,上海五方杂处,是冒险家的乐园,以龙蛇混杂闻名,完全属于数目字管理的反面教材,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沃土。
任何技术条件下的良政善治,包括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建诸于价值观虚无的基础上。詹姆斯·弗农认为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愚昧专制的英国,能成功步入现代社会。
在探讨英国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里,詹姆斯·弗农并不是最大胆的一位,艾伦·麦克法兰提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英国在13世纪就已经有了现代性的因素。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谈到,英格兰早在1250年已经有了发达的市场,发生了劳动力的流动,土地被当作商品,彻底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确立。表面上看,13世纪的英格兰是乡土社会,实际上蕴含了现代化的种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都是种子自然而然发芽生长的产物。
麦克法兰收集了从14至18世纪每一项幸存史料,进行手工及计算机的处理,其论证之详实,逻辑之缜密,令人叹服。他的著作问世后,英美学界虽然发出了五十多篇论文,但没有一篇能完全驳倒麦克法兰。
而《远方的陌生人》则给读者截然相反的感受,书里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从新闻出版,火车电报的发明,再到人口普查,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没放过。然而你读得越多,会感到越多的困惑,这么多冗余的材料无法支撑陌生人社会的理论。
在部分章节,作者甚至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英国家庭的私人性,工业革命刚开始时,44%的家庭都住了一个外人,他/她可能是仆人、家庭教师、远房亲戚,或者是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拿钱交房租的住客。穷人的孩子有7年学徒期,放在师傅家里寄养,到了20世纪孩子才在自家住,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模式才成型,换而言之,19世纪前的英国家庭陌生人比例高,反而显得非常“现代化”了。
总而言之,作者的雄心无法跟他的才华相匹配,他试图用陌生人理论作为一个“万金油”,来解释社会发展,学术功力却捉襟见肘。我们也不能对他求全责备,毕竟现代化是个非常复杂的历程,不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所能概括的。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