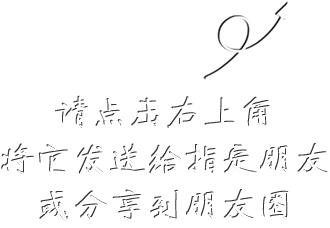那是湖上翩翩起舞的一只白天鹅,半个世纪来不常想起但也从未忘记。
一
我走出左右两边伫立着沉默石狮的大门,中午的街道很清静,几个老人坐在街边树荫下摆开巨大的棋盘,他们每天都在这里下象棋,成为街景的一部分。我在温暖阳光下漫无目的,想不出要去哪里。在记忆里,这一场景反复出现,渐渐构成了一种象征。一直辍学在家的我,从小就习惯每天起来不知道要干什么,但又在幻想里做许多事。时间和太阳一道缓慢地移动,夜色掩盖白昼,楼影树影仿佛吞没了阳光下发生的一切。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
由于在八十年代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自忠路三号、原铁狮子胡同一号,被称为“铁一号大院”的段祺瑞执政府得以大致保留原状,这在近四十年天翻地覆的北京属于异数。2016年的某一天,我曾经回到那里,熟悉的风景足以激活久已淡忘的记忆。
执政府主楼是北京少见的而且保存完好的大型哥特式建筑,我小时候住的红砖楼则是五十年代的宿舍楼,虽然质地厚重,但在美学上乏善可陈。这种据说来自前苏联式样的楼房在那时随处可见,如今绝大多数都已经拆除,这三栋楼却十分幸运,沾了执政府的光得以保存。我走上红楼顶的巨大平台,除了稀稀落落的几根晾衣绳一片空旷。我忽然看见一个穿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旧灰色瘦腿裤的女孩,在平台中央随着《天鹅湖》的音乐翩翩起舞。
在六七十年代走出执政府大门,如今宽阔的平安大道还是一条窄窄的林荫道。马路对面是13路公共汽车站,这里现在仍然是公交车站。往东不远是13路无轨电车站,然后就是与东四北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了。从北向南的六路无轨电车后来改成106路,两站到东四,那里有两个电影院,一个是东四电影院、一个是隆福寺剧场。在没有电视的时代,电影院是孩子眼中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我的童年没有几部电影可看,每次走进电影院,当灯光转暗,音乐响起,我仍然会激动不已。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瓦西里的台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当时不仅电影,面包与牛奶也近乎没有,匮乏里的印象就格外深刻。八岁时,我在东四电影院看《列宁在1918》,因为个子小,把哥哥和我自己的棉猴叠起来垫在座位上坐着看。有一段时间,电影院里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两部外国电影,后者被普遍认为更好看,多半是因为里面有一小段芭蕾舞《天鹅湖》,在革命年代,露大腿的芭蕾舞无疑是禁忌,仅仅因为附着在一部革命电影上才有可能播出。据说有很多电影院在放映时删去了这一段,但我看到的是未删节本。至今记忆清晰的是看到天鹅起舞时后面有人很不以为然地说“怎么放这个?”我大叫一声:“看的就是这个!”一片哄笑中,轻盈的白天鹅就消失了。
二
早年的影像记忆,往往对一个人的历史观有着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穷其一生也不曾认识到,年少时不自觉接受的印象也许并不怎么真实。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因为列宁。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政治版图重组;帝国坍塌,一片废墟,各方逐鹿,新人辈出。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军事强人、民粹领袖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也有几场革命,但大多数不成气候,只有前一年的俄罗斯革命存活了下来。历史上后来变得无比重要的事件,在发生当时往往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而且1918年的苏维埃共和国确实风雨飘摇,列宁遇刺只是其中事件之一。二月革命时携手推翻沙皇的几个党派很快就反目成仇,那一年俄罗斯政权脆弱,政变频仍,都不怎么血腥,更多是一哄而起的偶发事件,最后才是居于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列宁后来被尊为伟大导师是由来有自的:他敏锐地察觉到民心厌战,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德国签订城下之盟,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他断然实施革命的铁腕,外建红军、内组契卡,无论是对昔日的盟友还是对沙俄残留的军阀都毫不留情。电影中的刺客卡普兰和高喊“让列宁同志先走”的诺维科夫并非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而是同样激进,不久前还并肩战斗的社会革命党人。
那几年欧洲的中心话题是凡尔赛和约、魏玛共和国、国联(国际联盟)等等,俄罗斯还是一个边远的存在。多少因为如此,苏维埃政府经过三年内战,把各自割据的白俄军阀分别击破。在这个过程里立下大功的首推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然而在《列宁在1918》的电影里,当时并不重要的格鲁吉亚人占据了主要位置。
被清洗后来又被暗杀的托洛茨基电影里自然不会提,留胡子穿皮夹克看上去很酷的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逝去,他一手创立的契卡却继续壮大,在前苏联一直是最有权势的部门。革命的严酷也就一直继续,其影响遍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国从三十年代的肃反到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友人转来一篇关于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一家文革中遭遇的文章。孙泱是中共早期烈士、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朱德挚友孙炳文之子,著名演员、周恩来养女孙维世之兄,曾经担任朱德秘书,1964年调入人民大学,1967年被迫害致死。他究竟死于他杀还是自杀,至今没有定论。虽然当时宣布的结论是自杀,然而孙泱人高马大,如何在很低的暖气管上自缢,是相当难以解释的。孙维世第二年被捕,在狱中被活活打死。
孙泱到人大时我父亲已离开人大,所以彼此没有交集并不熟悉。不过父亲在人大多年,调离后家也没有搬走,与旧日同事过从颇多。孙泱是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死的人民大学负责人。
孙泱去世几年后,遗孀石琦和女儿孙冰带着两个弟弟流寓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院。他们搬来的时候我已经搬离,所以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听到有关的传说。我听说孙冰是闻名遐迩的美女,却不确知究竟曾否见过她。后来我邂逅她的一个女友,告诉我她还是个孩子头,很有女侠气,或许是逆境中逼出来的吧。我确知的是,在某个夜晚,当我回故居找旧日小伙伴时,遇见孙泱之子,文静秀气,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看上去有点忧郁,在一片闹腾的氛围里格外引人注目。几年前友人告诉我他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岁月在太平盛世中流逝,时代的变迁不仅仅呈现在每个人衣着的变化上。再说我也并不介意是否面目全非,一个时代的严酷与苦难,无论愿意或不愿意,依然会深深留下痕迹,既使不再提起,也会部分流传。这是历史的力量,或者说是关于历史的一种信念。
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院的发小们聚集在一起时,不少人会有打捞往事的愿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关于文革的记忆对许多人影响深远。令人惶惑的是,许多共同经历的记忆开始模糊甚至互相矛盾,历史叙述的不确定性与边界或在于此。
三
七十年代的北京生活其实很无聊,只有八个样板戏、十几部电影,绝大多数书籍都成了禁忌。年少时的娱乐,不过是打扑克、下棋、玩烟盒、打弹球。我很幸运,家里的书抄家时没有被抄走,兄长朋友们又经常在地下传阅各种书,日子平淡无奇,节奏缓慢,没有留下痕迹,只有读过的一些书至今还没有忘记。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本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时,我应该还不到13岁,但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死亡的残酷与爱情的美好,形成强烈的对比。后来我又读过至少两遍,每次读到凯瑟琳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时都会热泪盈眶: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海明威就出生在芝加哥近郊的橡园镇(Oak Park,音译奥克帕克),我刚到芝加哥时,去瞻仰过他的故居:一幢简单古朴的房子,旧家具、发黄的手稿和老照片有一种安详悠远的气息。上个世纪初,这里是一个规行矩步,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小镇。海明威在这里成长,但是他并不属于这里,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海明威的一生,在作家里绝对属于丰富多彩的:战争、革命、探险,样样不拉;雪茄、女人、航海,从未闲着。他一生结了四次婚,感情经历和话题都很丰富;他是个敏感的人,也很自我中心,行事捉摸不定。海明威研究因此一直是显学,无论严肃评论还是八卦绯闻。
然而一个作家的伟大终究是由于作品,其余不过浮云。《永别了,武器》是最感动我的反战小说,里面不仅仅是真实的残酷,还有虚构的爱情。在这一点上,它比《西线无战事》更为动人好看。事实上,我最喜欢的雷马克小说是《里斯本之夜》,同样是战争中的爱与死,动荡里的个人命运就如同茫茫大海上一叶扁舟,随着波涛起伏,不管怎样挣扎,最终无能为力。
海明威在1929年写的《永别了,武器》是他的成名作,和之前的《太阳照常升起》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的一代”代表作。一战与二战不同,爆发于偶然而不可收拾,最终没有赢家也没有正义。一战之前的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生活的巨大变革,繁荣与发展似乎是一个既定方向,欧洲人对未来满怀信心,对自己的价值观深信不疑。“迷失的一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第一次坍塌,在原有的政治正确废墟上,国家主义与民粹等混成的怪胎,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后有德国纳粹。在国际地缘本来的边缘地带上,兴起了巨大的红色苏联。
海明威、雷马克以及我以前写过的茨威格等许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作家都不是书斋中人,而是为和平、自由与进步奔走呼喊者,然而他们那一代作家面对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兴起无可奈何。他们预见黑暗,却只能和时间一起缓缓步入黑夜。这或许是他们当中,不少人未能如后来的大作家那样生活理性、寿终正寝的原因吧。虽然二战以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告终,然而深渊的阴影往往伴随人的一生。海明威在1961年用一杆双管猎枪炸碎了自己的头,死得很勇敢也很疯狂。
四
十多年前我曾经开车去很远的地方看一场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不知是因为期待太高,还是由于前苏联解体后国家芭蕾舞体制崩坏,舞团四分五裂,普遍水准下降,反正是没有什么感觉。回家路上,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了,失去了对人生的敏感?
《列宁在1918》里的芭蕾舞镜头在我的童年里是如此印象深刻,年少时,白天鹅曾常在梦中萦绕,或许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审美观的成形。我已经想不起是在哪里听的,但仍然能够感受到第一次听《天鹅湖》黑胶时的美妙。如今我的地下室里有不下十个《天鹅湖》黑胶版本,由穆拉文斯基、安塞美这样的大指挥家指挥的,却没有那时的感觉了。
发小中没有谁记得曾经有一个女孩在红楼的楼顶平台上跳《天鹅湖》,我不知道是自己记忆有误,还是出自童年时的一种向往、一次想象。也许我把白天鹅幻化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女孩,有时人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模糊现实与期望的倾向,自己相信的真实可能并没有发生过。不过我确信真实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夜晚,第一次看《天鹅湖》全剧,散场后和一个女孩在北京展览馆树丛掩映背后的回廊坐了很久。那是我曾经认识的跳芭蕾舞女孩,至今清晰记得她曼妙的舞姿。那时我就常唱舒伯特的《菩提树》:“也曾在那树干上,刻下热情诗句,欢乐痛苦的时候,我常走近这树”。然而青春热情,难免无疾而终;曾以为刻骨铭心的瞬间,多半在时光里风化。现在唱《菩提树》,最后一段比从前唱得轻而自然:“如今我远离故乡,往事念念不忘,我分明听见它说,在这里长安乐”。想象终竟是镜花水月,大约二十年后,幻化成《美国往事》里的一段回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坐在滨海的房间里,这是一个多云的黄昏,隐约有海浪拍岸的声音。西望太平洋和故国的方向,但见海天一色,空无一人。
虽然从佛学上讲,没有分别、一片空旷更接近世界的本相,不过我素不敢以有缘法自居,更倾向于凡人的使命还是在于找寻真实。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和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有太多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因为缺少关注,或者由于被湮没与遗忘。在2018年想起《列宁在1918》,关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世界,我们究竟还知道多少?在经济高速成长、生活快餐节奏的当下,半个世纪前的亲身经历,我们又还想得起多少?
二战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也开始了冷战。一边是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是重建的自由民主世界。狂热献身是植于人性深处的冲动,坚信不疑是维系社会安宁的需要。敏感的文学家一生多半处于夹缝之中,他们更多感受到人性的可疑、世界的不确定性而又无能为力。《永别了,武器》和《西线无战事》甫经发表就洛阳纸贵,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翻译成中文。前者有一个很鸳鸯蝴蝶的名字:战地春梦,这个译名大约更适合当时大众品味,很得流行演义小说的神韵,也折射出译者的理解。然而爱情在《永别了,武器》并非一种流行元素,而是与战争、死亡对抗的另一极。视之为“春梦”,多少忽略了作者的寄托与小说的力量。是的,文学与历史是无用之学,从来不足以改变现实,在崇尚实际的商业时代人们更多离之远去。然而文学中的美感、历史中的真实,是心灵史与事件史的记录,比物质世界留存得更为长久,构成一个时代传承的根本。
大多数人的历史认知,来自教科书、文学、电影及其他,很少来自历史著作本身。对于我来说,文学不仅是一种历史认知,更是一种坐标。日常岁月大半是平淡的,历史真相往往是冷酷的,而文学不管怎样写实或悲观,总会是有温度的,何况一个人完全可以心中悲哀,却仍然满怀希望。自然,希望很可能是虚妄的,理想主义冲动被利用成为疯狂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每代人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自出生而逐渐形成的思维惯性,注定了必须有所寄托的命运,注定了要去寻找心中不会消逝的象征。很难说这到底是坚守信念还是逃避真相,有时也可能兼而有之。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世界似乎有了方向。没有谁意识到,二战以来的政治正确其实在缓缓坍塌。在本以为会是一派祥和的2018年,人们发现历史并未终结,动荡与冲突的可能性并未减低;意识形态虽然不再分明,价值观的混乱却似乎与日俱增。一方面,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让世界前所未有地富庶,大大增加了人在现实人生中的选择可能性;另一方面,总有一些人感觉心灵不知所措,不得不以个人的方式构筑自己的避风港。在我生活中的某些时刻,那是湖上翩翩起舞的一只白天鹅,半个世纪来不常想起但也从未忘记。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