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0-10-28 01: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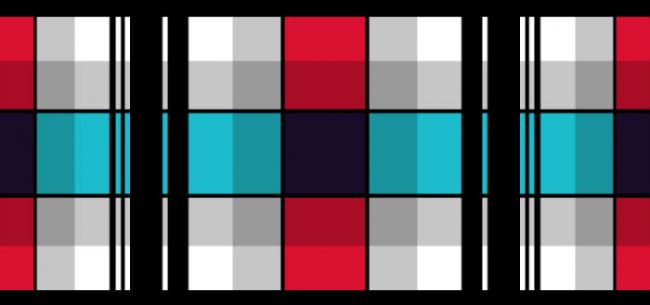
杨舒蕙/文
《格子》(THEGRIDBOOK)不只是一本平面设计专著,而像是一个由“格子”构建而成的巨型迷宫。其中,塔庙建筑、中世纪礼拜圣歌、集装箱船运、电子表格、肥皂泡等,这些表面看上去毫无关系的东西,都被作者汉娜·希金斯(HannahHiggins)以“格子”为线索贯穿起来,形成庞大的知识地图。莉莉·福特(LilyFord)在该书的英文书评中写道:“格子和现代性之间存在关联吗?这是她要回答的问题。尽管读者很快就会明白,她的目标远比这野心勃勃。她以天主教的视角看待网格的构成,所涉猎的主题在同一个图书馆内都很难找到,更别说是一本书了。”
“现代性”是希金斯真正关心的主题,而“格子”是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议题入口与脚手架装置。与其说她要讨论的是“格子”与现代文明相互塑造、相互构建的问题,不如说她想从整个(西方)历史的通渠中谱系式地打捞文明发展机制中最隐秘的动力内核。现代性是百年来几代学者意欲拼杀的疆场,也是最抽象、最难于厘清的大课题,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已经把现代性问题说透了、讲清了,此后的一切言论都是多余——现代性问题总是可以演变出更丰富的层次、更巧妙的维度供研究者试验、供艺术家创造。
汉娜·希金斯生于一个令人艳羡的、纯粹的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激浪国际艺术运动创始人之一迪克·希金斯(DickHiggins),母亲是激浪派中非常活跃的艺术家艾莉森·诺尔斯(AlisonKnowles),双胞胎妹妹是纽约的媒体艺术家。希金斯于1994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艺术史系教授。她著有《激浪的经验》(FluxusExperience),还与道格拉斯·坎恩(DouglasKahn)合著《大型计算机实验主义:早期计算与数字艺术的基础》(MainframeExperi-mentalism:EarlyComputingandtheFoundationsoftheDigitalArts)。汉娜·希金斯的书写野心不但来自于天性深处的冒险基因,还传承于芝加哥大学早已有之的跨学科文化传统。她的研究趣味超越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这句话可能描述得不很准确,实际上,我更认同她是一位“恣意盎然的研究者”。希金斯总是试图在历史的宏大图景中抓住某个演变的基质。这种于断裂处寻找延续性的方式无疑承袭了福柯的思想遗产。
从芝加哥大火说起,到芝加哥建筑结束,书中的10个主题名称各异,但本质上都是“格子”——“格子”是这10种类别的元结构、元模块。从摩天大楼到办公室隔间,从蒙德里安(PietCor-neliesMondrian)的画到计算机代码,“格子”赋予一切以形式,又被一切形式所规约。“格子”拥有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在“现代性”作为专门化的名词正式出现的时候,“格子”早就蛰伏在历史深处了——它是西方文化中最显著也最隐秘的视觉结构。希金斯如同织娘,津津有味地编织出“格子”演化史。她试图证明:“格子”会以各种形式出现——甚至可能远远超出这10种——它可能会弯曲或碎裂,也可能以超出现有认知的崭新形式倒逼我们更加仔细地辨认它。“格子”的持久性表明:一旦它被发明,就永远不会消失。它是文明结构中的随附之物,萌生于深处,向未来追溯。
1979年,艺术史学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Krauss)提出了“格子”(Grids),在思想界引起反响。她把现代主义绘画中的“格子”描绘为“扁平的、几何化、有秩序……反自然、反模仿、反真实。这就是艺术与自然背道而驰时的样子”。“格子”反映了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和新的、平稳的运输机制。在现代想象中,“格子”令文化与自然和身体对立:它“背弃自然”。同样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对效率的忠诚。在批判了“格子”从自然分离后,克劳斯继续认为:“在现代,‘格子’是排挤真实维度的手段,并用美学法则取代它。”
但汉娜·希金斯认为克劳斯的论争并非十足正确:“格子”从来都在。早在芝加哥大火之前,早在芝加哥成为现代大都市及工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前,城市网格系统就已经运行了。“格子”存在于狭长而瘦削的地块上,也存在于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带到美国的地图上。“格子”存在于每一首带有音符的赞美诗中、每一家商店的分类账簿里、每一个印刷的招牌上,存在于读过或没读过的每一份报纸上;“格子”还存在于每一堵砖墙的表面,而每栋建筑的正面都点缀着由“格子”架构的窗户及其图案。
“格子”不断变化,时间赋予它“演化”的类生物特征,“格子”就好像一个困于生命周期中的烦恼个体。法国艺术历史学家亨利·富西永 (HenriFocillon)在他1934年出版的《艺术形式的生命》(TheLifeofformsinart)中,编年体式地记录了建筑形式的生命历程:从粗短的、尖尖的拱门到高耸的哥特式建筑——向那种跳跃的、不可思议的瘦弱形式的动态转变。对富西永来说,形态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法则推进,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格子”的多样性和不可阻挡的演化与他的观点十分相似。
20世纪早期的两次主要艺术运动都依赖于“格子”。当保罗·塞尚(PaulCézanne)建议画家们“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来处理自然”时,也就是把物象格式化了。他认为,如果树看成圆柱体,把苹果和人的头看成球体,把山看成是又大又笨重的圆锥形物——倘若用这种几何学的方法,就可以准确地看到所见之物。在塞尚的构图中,“格子”更是影影绰绰地存在:椅子、桌子角和橱柜边共构了一个几何场,这是另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实体。
塞尚对人类的“双眼视觉”感兴趣,因为双眼能把两视象融合为单一知觉对象,但如果分别闭上不同的眼睛,还是可以感觉到物象在空间中的微妙差别。在塞尚的画作中,细微的焦点移动是完全可见的。但请注意,移动的视点也在征服和打破“格子”。
塞尚的“几何实体”与“多重焦点”为乔治·布拉克((GeorgesBraque)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提供了画作创新的可能。1907年到1914年间,他们发起了立体主义运动。塞尚留下的思想遗产很清晰:各种各样的形状被简化成一系列单纯的几何形式,然后能够从多个角度同时进行描绘。像在毕加索的瓶子、苦艾酒玻璃、扇子、烟斗、小提琴和钢琴上的单簧管这样的立体派图像中,名义上的完整主题就像一地碎玻璃。布拉克和毕加索通过与另一位数学家莫里斯(MauricePrincet)的朋友关系,对著名的四维几何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Poincaré)的一些理论较为熟悉。立体主义对20世纪艺术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影响实际上不仅仅只是视觉上的,更是时空认知层面上的。对一些人来说,立体派支离破碎的表面代表着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对绘画空间的客观分析更加趋向全面抽象的运动。
俄罗斯至上主义画家卡齐米尔·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 KazimirMale-vich’sBlackSquare)体现出这种现代主义的“格子”冲动。它完全是黑色的,毫无掩饰地平坦,标志着一个盒子的完全闭塞。在马列维奇之后,许多画家都效仿此形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画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phAlbers)在一系列彩色正方形的画作中表达了“对方块的敬意”(HomagetotheSquare)。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画家阿格尼斯·马丁(AgnesMartin)创作的作品只不过是白色画布上的铅笔网格。名单很长,数不胜数。
网格在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优势并不是纯粹自然的。德国教育改革家弗里德里希·弗罗贝尔(FriedrichFroebel)的幼儿教育计划使得幼儿园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以支持幼儿获得更优化的视觉、触觉和声音训练。那些标榜自己“未经污染”的现代艺术家,他们童年时代的恋物癖和幼儿园玩具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格子”与现代形式之间的形塑关系。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Wright)用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口吻描述了这些玩具:
我坐着在幼儿园里,面前有个小盒子,盒子边长4英寸,里头有正方形(立方体)、圆形(球体)和三角形(四面体或三脚架)。这套玩具让孩子意识到大自然有内在结构,尽管这远远超出了他们当时的理解力。但是幼儿先天的感知力能够领悟到这一点。比如我就很快就变得对物体中有意味的构造模式敏感,因此我不喜欢画一些杂乱的、随意的东西,我想去“设计”。这一切都是在幼儿园学会的。
赖特对形式的觉醒,虽然象征着几何学本质在他心灵中的升华,但他还接着强调说自己发现了一种“在一切事物中不断演变的构造模式”,表明了一种多维度、跨学科的设计感,毋宁说这是几何化的“格子”元结构在起作用。
20世纪初,柯布西耶为了使建造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他在1914年设计、建造了钢筋混凝土预制骨骼住宅,由此提炼出新的结构原型,即多米诺体系,其重大意义在于出现了一种无轴向的均质空间。房子由楼板、柱子和楼梯等基本要素构成,网格作为重要的“隐性要素”,表征多米诺体系在水平方向的排列和拓展方式,同时成为建筑结构的组织形式。随着技术和设计方法的简单输出、快速复制和模仿,当代建筑呈现一种被“格子”控制的严峻状态,建筑美学的差异性仿佛被彻底消除。世界趋向形象化、空间化,媒介的交融、“格子”的隐匿、趋同,最终都试压于那唯一的经验主体——人。
现代城市被认为是在一个固定的网格场基础上设计的,它允许通过地图坐标轻松获取导航,这就是所谓的“烤架”(gridiron)。这个好玩的名字来自中世纪的人们用来烤肉、烤鱼(甚至能拿来折磨人)的金属栅格。烤架是精确定位自己所在地的工具,例如在纽约,若要问“大都会博物馆在哪儿”,烤架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在整整齐齐的第五大道八十二街上找到它。有一种通常的理解是:现代大都市的网格规划是砖块被建造成直墙后的必然结果:先是砖块造出房屋,然后一排排的房屋出现了,再然后是街道、是更大的街区等等。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烤架是原因,不是结果。烤架始于明确的前期规划,它将个人的身体、行动同城市空间的关系系统化。希金斯认为是文化架构在使烤架系统——“格子”成为可能,这是高度规范、管理严密的文化的表征。
每类“格子”的出现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砖块、石碑和城市网格使坚固的住房、语言的标准化和城市的高效发展成为可能;地图、乐符、账本和印刷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大众文化。将“格子”视为大规模社会化的框架,这一观点与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对神话的描述一致。他认为神话是一种社会黏合剂,以最简单的方式构造现实,同时保持对特定语境和细节的适应性。根据这种说法,神话不是谎言,而是代表社会用来有效构造信息的工具,正如“格子”服务于一种历史进步的愿景,调解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工业秩序,西方文明的“格子”神话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非人化的社会控制机制——但我们不会愿意听到这种说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将人类的思维设想为一个“格子”,他认为“格子”是人类内在动力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达。换言之,不要将“格子”的规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关联误认为是永久的。无论建立社会标准的每个“格子”的起源是什么,“格子”的反复转换,它们打破、粉碎、弯曲和适应意想不到的目的。福柯在他对“权力”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写道:“要想从上至下地运动,就必须同时存在从下到上的毛细血管。”“格子”的历程是清楚的,就像为组织、交流和控制创造机会一样,它们也为分析提供机会。在“格子”被打破的地方,文化揭示了变化。例如,城市网格上废弃的砖房可能会成为棚户区或艺术家工作室。由于无人居住,或遭到武力破坏,这些废弃的空间会进一步沦为废墟。砖块作为壁炉和家的有力象征,也几乎成了革命和战争的同义词,以倒塌或投掷的形式出现,就像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经常出现的画面一样。
汉娜·希金斯的《格子》是一部有趣的大书,但大部分评论者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同样奇异的口吻来描述阅读体验:“她偏爱强行将不相干的东西并置在一起,然后非常流畅地讲述每一种‘格子’的宏大历史,奇闻轶事与她傲人的自信交织在一起。”我认为希金斯不是对自己的架构与文风天真而不自知,相反,她似乎有意放任这种写作:为了一种简洁与畅快的节奏,避开那些对细节和逻辑的过分纠缠,也避开那些更复杂、更微妙的学者专家式的处理方式。她反而将孩童般的心境嵌入文本中,时常大声呼唤她的读者:“快来这儿看看!这儿有格子!那儿也有格子。”汉娜·希金斯兴许是希望像创造艺术一样来创造《格子》,抛砖引玉,将这新鲜的发现立刻拿出来,保持这混沌的、还未被过度开发的学术处女地。
对于一个始终在时空中生长和变异的“格子”元结构来说,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同样是历史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身在局中时,即使拿出百倍的力气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拽,都仍然囿于“此山中人”的局限,因此,描述现象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甚至出于巨大的谦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