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1-10-24 10:28

![]()

马向阳/文 阅读成了一种社会焦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
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介学者克雷?舍基如此赞美互联网的出现,声称这一新技术正在颠覆印刷品暗含的权威性,并批评“严肃阅读原本就是一个骗局”,此时,中国的校长、教师和家长们却在忧心忡忡地告诫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要求他们远离手机,多看书。2021年一项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进行的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中国国民人均每天用手机的时长为100分钟,而剩下的可怜读书时间则不到玩手机时长的1/5,只有20分钟。
阅读活动真的像古代先贤们所说的那么重要吗?还是像美国媒介学者舍基所说的那样,人类根本没有必要为阅读的消亡而显得矫情和伤感。长久以来,阅读的历史几乎等同于文明的历史,东西方赋予了阅读文化同样重要而严肃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西方社会重视通过阅读去培养每一位公民的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鼓励读者保持批判性思考和怀疑精神;那么在中国社会里,耕读传家的读书人传统几乎扮演了最重要的知识接力和齐家治国功能。
21世纪初,数字技术呈现出一种泛滥无敌之势,阅读活动从启蒙时代的权威神坛跌落,很快坠入了痴迷——祛魅——衰亡的快速下滑通道,甚至有西方学者进一步预言,阅读的没落,使得人类有可能再次回到古登堡之前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代,人类的知识活动和今天的数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同样推崇和使用参与和交流性的口语,而非印刷品时代白纸黑字所代表的不容置疑的封闭权威。
如果说阅读的未来属于中世纪,阅读人还有未来吗?一旦阅读的意义被消解,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意义、还能赋予我们的道德生活以某种意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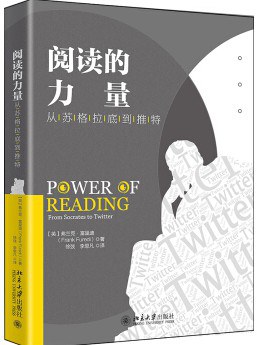
阅读的力量
作者: [英] 弗兰克·富里迪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徐弢 / 李思凡
出版时间: 2020-11
一、柏拉图式拷问:毒药还是良知?
从人类有阅读活动始,读写能力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播的重要使命,更有塑造人们良知的奇妙功能。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古雅典时代,读书像古代中国一样被视为一种高尚而稀缺的职业,苏格拉底认为,书面文本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东西:一旦书中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呈现在一个具有智慧的人面前,阅读的危机就出现了。
在苏格拉底看来,当时的雅典只有为数不多的值得信赖的公民才有资格去从事诸如追求真理这样艰难的事业,在这条崎岖小径上,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获得真理,并不可靠。一方面,文字书籍流转到了大众那里,如果无法被“正确理解”,阅读行为就只能引发偏见在更大范围扩散,进而助长那些浅薄之徒“言过其实的和愚蠢的骄傲”;另一方面,真理事业太过艰苦,知识“不是某种可以像其他科学一样被写成文字的东西”,只有“在经过那些共同探究它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长期对话之后”,真正的知识才能觅得通向灵魂的道路。
换言之,苏格拉底对于阅读文化的满腹狐疑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于口传文化的过于迷恋。在他看来,人类的阅读并非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封闭的文字系统缺少口语文化的纯粹性、开放性和灵动活力。正是从这一交流的悖论出发,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向所有的读者发出了第一次健康提醒,他使用希腊文中的“药物”(pharmakon)一词来譬喻阅读和写作,暗示基于书面文本的阅读行为,存在着一种隐秘不彰的天然悖论——它既可能成为一剂良方,也可能变成一味毒药。
柏拉图的拷问,千年以来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并伴随后来一波又一波的媒介变革浪潮,人们关于阅读的重要性及其种种弊端触发了种种纷扰争议,再也没有停歇过。聚焦书面文字的不同阅读行为之间,开始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张力:某种阅读是进行有效交流的启发和交流的工具,另一种阅读则踏上了对现有道德秩序提出诘难的危途。
在中国,儒学圣人同样不喜欢谈及“怪力乱神”这样类似的、对现存道德秩序构成威胁和“非礼”的“敏感”话题,在孔子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儒家信条之下,《论语》这样的经典文本及其解读,被赋予了一种拥有无上知识权力地位的封闭性、权威性和神圣性。中国圣人所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直率的表达,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庸众”和蒙昧者这样的态度相比,夫子们分明有着一种舍我其谁、不言自明的精英式骄傲:要想维护周天子时代那样的社会道德和秩序,唯夫子之诚意之神圣之高贵才能做到,卑微小民何足论也。
在维持一种“述而不作”的高贵传统方面,苏拉格拉和孔子有着同样的贵族精神底色。苏格拉底认为,“适合大众的文字除了能够照亮事物的本质”,并且让所有普通人“都能看见”之外,这种高尚的工作其实隐含着一种永恒的职业焦虑——苏格拉底本人从来不相信,在充满歧义和解释空间的文本及阅读行为中,一旦提出的问题能给普通人“带来任何益处”,“它充其量只是对少数人具有益处,即对于那些只需稍加引导便能依靠自身力量来发现真理的人带来益处。”
在小心翼翼地选取极少数“合格读者”,并且试图通过进行选择阅读文本、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思想方面,孔子比苏格拉底走得更远、更彻底。相比较而言,孔子的儒家思想比苏格拉底的哲学更专制、更封闭,也更具贵族气息,两位先贤在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下,掩饰了同样的对书面阅读行为的不信任。
阅读困境里,还折射出的人类黑暗时期知识贵族和无知平民的阶层冲突,在《论语?微子篇》的“子路问路”一篇中表现得格外耐人寻味。孔子偕弟子子路赶路迷路了,孔子就让子路去借问正在耕地的两农夫长沮、桀溺:“渡口”在哪里?农夫甲长沮一打听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迂腐夫子孔丘,就反唇相讥道:他“应该”知道渡口在那里,说完就埋头继续干活;另一位农夫桀溺则干脆挑拨离间,讥讽子路跟错了人生导师。夫子居然也会迷津失道,两位农夫此刻拒绝指路,这一故事恰恰隐喻了孔夫子们“怃然”若失的言说困境:“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天下无道,夫子们企图依靠言说来拯救世道人心,在这些只能以耕作为生、打心底里鄙视夫子和《论语》之类文本阅读的“低端人士”看来,书呆子们“应知”而不知,作徒然之说教,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迷途?
在21世纪数字文化全面覆盖的今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孔子们对于阅读的危险性的警告依旧时有回响。网络上各种虚假消息和无下限广告的“阈下广告技术”影响下,许多用户流连其中而难以自拔,唯一的不同情形是,和两千多年前这些圣人们所处的“黑暗时代”相比,人们这样被媒介所播弄操控的现象在数字时代变得更加普遍,阅读引发的焦虑也更加严重罢了。

阅读意义的消解,暗示了人类文明正在走上一条更加不确定的迷途
二、阅读作为一种职业:意义的焦虑
阅读有何意义?阅读为什么存在一种所谓的“严肃阅读”和“快乐阅读”?两者的差别何在?如果说在文本的封闭空间里,一直隐藏着福柯所说的那种让人盎惑又充满操控的“权力关系”和具有强大遮蔽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又如何让读者“正确地阅读”、小心地避免被种种洗脑和控制、从而“合理地行动”呢?
自柏拉图和孔子之后,人们的阅读行为始终为上述问题所困扰,阅读在成为一个社会“难题”的同时,围绕阅读意义展开的纷扰争论和种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在统治者、知识分子和文盲阶层中间都聚拢曾一种令人不安的、甚至带有极度危险性的恐怖阴影。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阅读意味着是打开真理之门的首要路径。苏格拉底时代,先知们视阅读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智慧方式;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教徒们赞美阅读是品行高洁和探索真理的媒介;启蒙时期,“合格的读者”成为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和理性、唤醒个人主义、建设活跃的有德性的公共生活的主导力量;18世纪以降,“热爱阅读”成为每个普通人的理想生活,阅读自身被发现具有某种“自身的内在价值”和每个公民实现自我完善的首要手段,读写能力也成为市民们一种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西方社会在尊崇阅读的同时,发现阅读行为在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方面扮演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功能角色,由此也埋下了焦虑的种子。不仅仅是柏拉图和孔子这样的伟大贤者在阅读价值这一问题上困惑良多,表现出种种严重的内在冲突、矛盾和隐忧,这种焦虑感一路沿袭下来,折磨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直到两年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读写能力的独特性、对于印刷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权威性,依旧充满了各种不安和质疑。
以18世纪初期的英国为例,16世纪的古登堡技术所代言的印刷文化,像人类进入新媒介时代的一条“璀璨星河”(麦克卢汉的华美比喻),在两百年后引发了又一波“媒介大爆炸”,其猛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媒介转型。以英国报业为例,1712年到1757年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报纸发行量增长了八倍,邻近的法国也是如此,1789到1799年的十年里,巴黎出版发行的新报纸居然超过了两千种!
印刷品繁盛带来的新一轮媒介革命,直接催生了一种只属于中产阶级的公共舆论,一个有着相对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一种被称为“理性时代”、“进步时代”的文化洪流或者说“时代精神”(黑格尔发明了这一用语)。这一时期,阅读症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阅读分层”的出现——通俗文学代表的故事书、廉价小说、和低俗报纸,连同为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狄德罗、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高级作品”,同时塞满了中产阶级的书柜橱窗。在英国这个“阅读之国”里,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商人、手艺人、妇女,到城市公务员和普通劳工,无疑不在热衷阅读,“现在,所有的英国人都成了读者,”一位历史学者如此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阅读文化的无限推崇和对于“阅读规范”的无边焦虑也是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这种焦虑到了统治者,很容易被无限放大,言论市场马上变成一个用生命献血祭奠的场所。在这一绵延数千年不绝的通过阅读和经典文本“检验”、以进行社会教化和驯服的科举传统中,儒家经典被赋予了唯一正确的。类似宗教般的神圣性,这时,如何正确地阅读,阅读的意义、以及解释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就成了一个关系到个人生命乃至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今古文之争、汉儒和宋儒之争、独尊儒学和废弃儒学之争,中国历史上围绕儒家经典的阅读及其阐释,最后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结束,其中的纷扰争辩,只能以人头落地来终结。在被称为“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性的封闭文本中,这种文本的封闭性和解释的唯一合法性以及最高权力的神圣性三者之间如唇齿相依,被紧紧捆绑在一起,从秦始皇的活埋焚尸,天才写作者和阅读者苏轼差点丢掉性命的乌台诗案,再到雍正《大义觉迷录》里湖南秀才曾静等知识才俊的不眠冤魂,面对每一次试图冲破权力和文本相互交织的思想罗网的社会力量之冲动,统治者从来都是用带血的刀刃来划分“正确阅读”和“合格读者”的边界。
了解到这一传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胡适、陈独秀们当年推行白话文、鼓吹“平民文学”的深远意义——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新边界勘定,就是从冲破“老一套”文本阅读的旧边界开始的。
三、阅读的终结:在骗局和迷途之间
21世纪初,面对数字文化的冲击,人们从来没有如此焦虑过书面阅读的未卜前途。按照《阅读的力量》一书作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富里迪的说法,数字文化摧毁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方式,还有从封闭到开放的媒介形式变化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权威性的跌落。富里迪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而不再是一个“思想的时代”。“在思想的地位和知识性论断的客观意义得不到重视的背景下,读写能力本身也被认为无足轻重”。以此同时,书面阅读的价值也被大大贬低了。
就此而论,数字学者舍基的“阅读骗局”只是其中的一种阅读焦虑症候。阅读文化的衰落和更新,与其说是因为网络技术赋权带来的言论市场过于自由或者说混乱,其实,更深的诱因还是麦克卢汉所渴慕的“口语文化”复兴。在麦克卢汉关于书面介质文化的经典表述中,他把文本空间中的最重要的封闭性内容描述为“窃贼手中的一块美味多汁的肉,其用途是干扰和分散‘心灵的看门狗’的注意力”。换言之,麦克卢汉乐见数字媒介对于书面媒介的驱逐,在他看来,作为阅读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并不重要,它只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干扰,媒介本身才是“信息”(mediumismessege),书面阅读中的内容只能表现出一种相对的重要性,而且是作者自说自话的主观表达,当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性解读同样要受到前所未有的褒扬。
在麦克卢汉和舍基这样的媒介明星学者眼里,长达五百年的印刷信息主导的时代被称为“古登堡间歇期”——换言之,古登堡代表的印刷文化霸权,其实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短短的瞬间而言,数字文化狂飙突进之后,伴随阅读价值一起坍塌的,还有印刷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内容霸权——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的知识、智慧和文化遗产这一整体性的体系——如今都在数字媒介面前瑟瑟发抖,失去其权威性。
阅读意义的消解,暗示了人类文明正在走上一条更加不确定的迷途,或者说是十字路口。从文本阅读的贬值,再试图回归中世纪口语文化的一种自然交流状态,这种故作天真的神往,深刻预示了媒介变化即将引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或许正在萌芽。当“作者之死”、阅读意义面临消亡时,如何打开封闭性的书面文本的神圣权威空间,进而跃入一个由无限开放性的信息文本和每一个网民自我构建的个人独家意义空间中去,数字化阅读正在询唤一种新的“合格读者”和“正确阅读新媒介”的出现,新一代网络土著们既能在信息海洋里自由冲浪,又不至于因为自由思想的盎惑(有学者暗示,互联网上的各种“阈下文本”就像奥德赛归航途中的各色女妖诱惑)而迷失方向,进而再一次发现通向人类新文明彼岸的“真理之路”。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