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向阳
解剖刀划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1632年1月的一天,26岁的荷兰青年画家伦勃朗雄姿英发,正在阿姆斯特丹准备一场瞩目的公开创作表演。这位年轻的画家以其创造性的肖像画风格,风靡了整个阿姆斯特丹。这一次,他受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邀请,为该行业知名科学家杜普医生正在进行中的一堂别开生面的解剖课堂当场作画,用以纪念和表彰杜普医生杰出的专业声誉。

杜普医生的解剖课
伦勃朗的这幅名作《杜普医生的解剖课》,至今被珍藏在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面中,画家描绘了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指定的八位医生,其中,主人公杜普医生被置于强烈的明暗光线对比中,其他围观解剖课的七位医生或凝神、或惊奇、或怀疑,只有杜普医生表情格外耐人寻味:他既没有面对观众,也没有专注病床上的解剖对象,甚至也忽略了他身边的同事们——此刻的他,正凝视着房间之外的远处。
当代著名神经科学家、《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认为,画面中主人公杜普医生的表情,传达了当时欧洲社会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解剖刀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工具,催生了今天神经生物学所关注脑细胞和思想之间物质连接这一重要研究路径,在当年更是触发了斯宾诺莎颠覆性的危险发现:杜普医生的手术刀和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生物学发现一起,正毫无敬意地直接闯入造物主的神圣世界——人类最隐秘的情绪和精神世界——包括欲望、情绪、心灵和智慧的发生和运作机制。正是这些天才预言和发现,使得斯宾诺莎终身被教会驱逐,只能隐居在那个时代的明亮尘埃里,直到他44岁死于尘肺病。
这一天,是人类社会一个万众瞩目的戏剧性时刻。当天观看伦勃朗现场作画表演的公众中,英国生理学家威廉·哈维(他后来发现了血液循环)和斯宾诺莎的导师笛卡尔也厕身其中。十七世纪中期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正是人类智力大爆发的天才世纪。
一个人们开始只信仰事实、观察和实验的新时代由此开启。精细的手术刀、透镜、显微镜和实验室,代替了笛卡尔们探索人类本源的方式,人们深信新的科学工具可以解剖人体结构,进而深入到皮肤之下的身体内部深处,了解到欲望和情绪、身体和心灵、自我和世界等人类的所有本质。
斯宾诺莎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
四百年后,斯宾诺莎当年关于情感机制的研究,让当代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感到震撼。就像1632年1月那一天、人们在围观画家伦勃朗描摹杜普医生的解剖课时的神奇感受一样,当今天视听文化媒介正在取代读写文化媒介时,同样会感慨达马西奥笔下当代神经科学发现和斯宾诺莎伦理学理论的奇妙契合。
当东方甄选第一网红董宇辉在直播间里于狂喜和眼泪之间进行无缝切换时;当薇娅、李佳琪在直播间高声深情大呼“我的家人们”,并通过各种各样的粉丝节、感恩活动把人们和商品的关系变成一种情感连接时;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指责所有报纸新闻为“假消息”,并利用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来治国理政时;当传播学者们惊叹:“网络人”都更愿意用情感来取代事实的“后真相”媒介社会已经到来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当年斯宾诺莎所洞察到的情绪发生机制正在给社会生活施加更重要的影响力。
从当代最热门的神经生物学出发,斯宾诺莎曾一路前行,从细胞生理描述,再到身体解剖,最后是脑科学研究,进而解释对美德伦理学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基础,斯宾诺莎赋予当代生物学家们以非凡灵感。
内稳态机制:从情绪到感受
斯宾诺莎的情绪引擎理论,离不开人类身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自动化的、一种叫做“内稳态”的生命管理装置——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这一装置经由不同的身体组织和结构在经历长期进化后,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灵敏、又高度协同的内在调控系统和受调控的生命状态。
简单来说,内稳态机制包含自下而上四个层面的身体组织:最底层是由新陈代谢、基本反射(如惊跳、对噪音、触碰和冷热及明暗光线的自然反应机制)以及免疫系统等组成;中层是愉快(奖励)和痛苦(惩罚)的行为,这些反应的集合及其相关化学信号,构成了生命体验中愉快或痛苦的生理基础;第三层是上层的大脑驱力和动机,斯宾诺莎有时称之为“冲动”和“欲望”,是指有机体受到某一种特定驱动力的行为冲动以及对于这种冲动采取的意识感受(如解决或者抑制);最后第四层是趋近顶端但未达终极的分支,即情绪本身,这是生命用来调控其状态的“王冠宝石”。狭义的情绪包括快乐、悲伤、恐惧、骄傲、羞愧、同情等,所有这些情绪,构成了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命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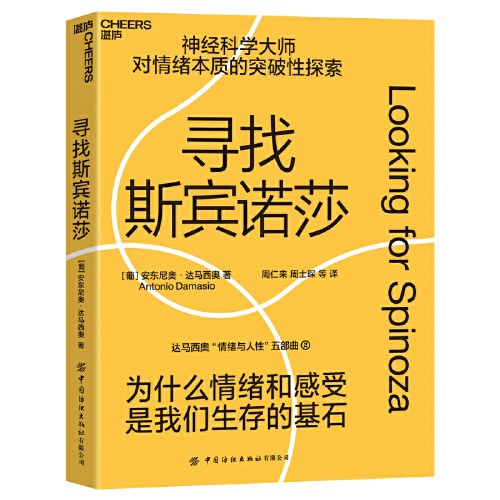
《寻找斯宾诺莎》
[美] 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 /著
周仁来 周士琛 /译
湛庐文化 |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2年3月
内稳态机制扮演的最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个体生命中任何时刻的“努力”状态——“每个事物莫不尽其所能,以努力保持其存在”。每个人为了实现所谓的“幸福”生活之目标,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身体细胞无时无刻不都在努力运作,负重前行。
换言之,内稳态机制中所有细胞的努力,为的是提供一个比中间状态(如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更好的生活状态,即杰弗逊等先贤们在《独立宣言》所昭示的社会理想——“我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所有人生来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护生命并寻求幸福,他们的幸福来自于成功的努力,这些事实就是美德的基础。”
血液中传输的化学分子,以及沿着神经通路传导的电化学信号,所有这些“努力”的指示构成了一种奇妙生命基本装置,用以自动解决我们生命中基本和重要的问题:如寻找能量(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来源;吸收和转化能量;维持与生命进程协调的内部化学平衡;通过修复损耗来维持肌体的结构;以及抵御疾病和伤害身体的外部因素等等。
数千万年来,个体大脑和社会整体一直在协同进化,得以演变出今天人类社会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行为:如群体的安全感、合作的力量、必要的制约、利他主义和最初的工会等等。一切生物莫不如此,一只小蜜蜂的脑组织仅包含了95000个神经元(人类有几十亿个神经元和几万亿个内部神经元连接,一些低等生物如秀丽隐杆线虫只有302个神经元和大约5000个内部神经元连接),同样进化出相当深厚的社会性。
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曾经分别试图从先天和后天等不同视角研究情感产生机制对人类的影响。在达马西奥看来,研究情绪的发生机制,必须将情绪和感受两者分割开来,否则,“就难以看到情绪是多么美丽、多么令人惊叹的智慧,以及它们能多么有力地为我们解决问题。”从情绪发生到感受情绪,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有机体、能够映射人体结构和身体状态的神经系统(从而将这些映射中的神经模式转换为心理模式或者表象)、意识、脑映射。这中间,脑映射特别重要。一开始的情绪是一个问题,脑机制进行的调节和感受又是另一个主动的过程。以爱为例,除了作为一种令人感到愉悦的状态之外,爱什么也不是。
一旦我们能感受并见证内心深处的生命状态,这显然又是一个更显奇妙的时刻!当人们试图去逆推感受的源头及其进程时,会发现,感受能够见证我们心灵的深处,这恰恰或许正是生命成为复杂有机体的真正原因。心理学家已经验证,一些在生命早期遭受过额叶损伤的个体,往往会失去对他人产生同情、依恋、尴尬和其他社会情绪的能力,进而无法展现出预示着最简单的社会道德系统的先天性反应:比如利他主义的萌芽,以及没有应有的仁慈、没有适当的责难,也没有适当的自我失败感。
就此而言,人类的内稳态机制构成了社会生活治理的基石。一方面,人类用了数百万年来进化自身的内稳态自动化装置,使其日趋完美;另一方面,我们也发明了各种契约和组织等非自动化社会装置来调节群体行为,以促进和维持从每一个个体的内稳态机制到整个社会的内稳态机制。以纳粹极权主义为例,当年纳粹们声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公正的世界”所采取的许多非自动化的策略(如屠杀犹太人等),其动机、目标和手段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性和脆弱性。当代社会中的很多组织、社会习俗和道德准则,本质上也模拟了内稳态调节机制,它们通过一根长长的“脐带”来模仿一种类生命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并将之与其他层级紧紧联系在一起:欲望和渴望、情绪和感受,以及对两者的有意识的管理。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发明,就是社会大规模促进其内稳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虽然成绩骄人,问题同样不少,即便如此,这些不完美的非自动化的社会调节机制,依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和灯塔,无论这灯塔之光在今天看来如此幽暗、如此微弱。
美德的生物学基础
在十七世纪斯宾诺莎所建构的生命伦理体系中,生物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按照现代生物学的观点,人脑和社会过去一直在协同进化,而斯宾诺莎提出的生命体系,显然受到了一种有保护生命的自然倾向的生理机制制约——生命的保存依赖于生命功能的保存,因此,也依赖于生命的调节。
事实上,生命调节的状态是以情感(如快乐和悲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欲望加以调节;人类个体通过自我、意识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构建,可以认知和理解欲望、情绪和生活状态的不稳定性。有意识的人会将食欲和情绪理解为感受,这些感受又加深了人们对于生活脆弱性的理解,并将其变成一种关心,最终,这种关心从自我开始流向了他人。
斯宾诺莎的问题是,一旦人们所有深思熟虑的行为,包括美德,实际上是由某些可能无法控制的生理构造等先验条件所决定的,那么,人类还能拥有“自由意志”吗?他其实从未否认过,每个人其实都在有意识地做出某种选择,而一切生命、政治及社会的最好状态就是自由。一种生命只有在他仅凭自己的本性而生活,仅凭他自己的决定而行动时,才是自由的。事实上,这也是他从21岁就立志成为一名战士、隐士和孤独者的初衷。为了掌控生命本身,斯宾诺莎承认,既然人类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是一种有益于机体表现的“理性”行为,那么我们任何时候依旧可以说一个绝对的“不”,就像康德一样坚定和迫切,哪怕说“不”的自由有时显得那么虚幻缥缈。
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基于生物学的美德有两重含义:首先是最简单的幸福,它来源于人类会按照自我保护倾向来行动,然而这并不够,人类更重要的幸福感受,除了需要建立社会契约字样的非自动化内稳态装置之外,更来源于一种摆脱消极情绪肆虐、抵消生命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威胁的力量。在斯宾诺莎看来,幸福不是对美德的回报,它就是美德本身。
1656年7月27日,24岁的“怪人”、叛逆者、隐士斯宾诺莎被驱逐出了犹太人群体,1670年,38岁他的独自一人来到海牙定居,带了一个书架和他的藏书、一张桌子、一张床以及他用来谋生的镜片制作设备。
早年出生富豪之家,晚年生活窘迫,斯宾诺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朋友们的慷慨捐赠,每年只接受300弗洛林的小额养老金,这笔钱足以支付他的食宿费用,购买纸张、墨水、玻璃和烟草,以及支付医生的账单。44岁时,斯宾诺莎死于硅肺片,这是一种职业病,在他成年之后,这位与世隔绝的哲学家一直靠磨镜片出售来谋生,后来他的肺部全部被闪亮的玻璃粉覆盖,直到无法呼吸。
斯宾诺莎一生热爱镜片。镜片可以窥见身体最深处的情绪和感受,也能洞察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和神性。感受产生自生命过程,又是生命的来源,更是生命指向的全部目的。斯宾诺莎不仅仅要为情绪正名,而且要告诫人们如何面对生命本身。在勇敢和希望之间,他选择了勇气这一人世间最罕见的美德,至于所望的“希望”,他是这样定义的:
“希望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快乐,它来自某物的未来或过去的表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它的结果表示怀疑。”
自由诚缥缈,美德才幸福。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