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宗伟/文
特奥多·W·阿多诺是让人敬畏的哲学家,理查德·瓦格纳是让人崇拜的音乐家,当阿多诺谈论瓦格纳,单纯出于引经据典,中国人也不能忽略了这本书。无论作者阿多诺的倾向与意图如何,我都有权认为:它属于那种使音乐与哲学带着尊严的著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的《论瓦格纳与马勒》一书,分别收录了阿多诺对瓦格纳与马勒两位音乐家的评判,前半部分《试论瓦格纳》由10篇写于不同年代的文章组成,各篇都选取了一个角度,相互呼应组成了社会心理、音乐元素、瓦格纳乐剧三个主题,作者企图用这三把手术刀把瓦格纳解剖给读者看,但是,与其说这些散乱的篇章服务于一个“照亮”阴暗的一致目的,属于作者外科“工作的整体”,不如说它们仅仅在标题上完成了分工的任务,内容上丝毫没有体现出对整体命令的执行,甚至各篇之间的语言风格都有所差别。对此作者解释说,他除了手术刀还拿着一台名为“微观逻辑”的显微镜,活的肌体被他切割进十块玻璃器皿,用以放大观察里面的文字细胞。我已经闻到了这本书里的刺鼻碘酒味,幸运的是,译者动用巧妙的翻译技巧以及优美的语言,冲淡了它。当然了,如果有人笃定认为,那些单独篇章必定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呈现出了整体,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位锻造“历史”的老师傅。
至于作者说,“瓦格纳的悲观主义是叛变了的造反者态度”,几乎点出了瓦格纳音乐、戏剧、社会心理在作者观察中表现出来的核心症状:颓废(décadence)。瓦格纳在作者眼里,是个软弱的叛徒,他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叔本华、叛变了艺术。
叛变了革命
瓦格纳1849年参加了德累斯顿起义,革命失败后被警察通缉,逃往瑞士。在流亡中,瓦格纳发现了叔本华哲学,成为了一名悲观主义者,这一次,他直到去世都坚持了立场,未曾动摇。但在作者笔下,这是因为,市民阶级对瓦格纳施加的力量,是全方面的,而他作为个体,忍受不住市民阶级的道德压迫,无力满足“市民阶级体面”的各种要求,所以,瓦格纳在力量面前屈服了,他背叛了革命,堕入了叔本华的同情道德,于是乎,从前的被压迫者,现在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压迫者的事业了,等于认同了压迫者的力量,并且用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来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软弱与屈服。如尼采说,“瓦格纳信仰了革命半辈子,只是像任何一个法国人那样曾信仰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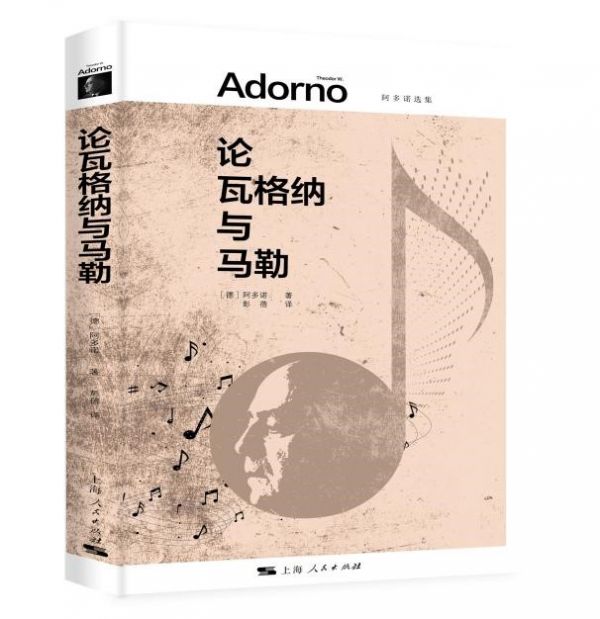
《论瓦格纳与马勒》
[德]阿多诺 /著
彭蓓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7月
叛变了叔本华
瓦格纳接受同情道德,也就接受了身体即意志的立场,无意识先于意识的看法,本能才是艺术根基的主张,但是,如同身体也会死去、迟暮与凋谢,瓦格纳也要面对这些立场、看法、主张的地基即将坍塌,根据即将腐坏,这也是一切意志主义者(或称悲观主义者)都有的困扰,因此,他们纷纷提出了解脱(或称救赎)方案。
但在作者笔下,瓦格纳的方案不把意志对自我的否定(叔本华方案)当作是自由的行动,而是命定的、被决定了的世界计划:瓦格纳把划归(全部宇宙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意志的“永恒正义”(叔本华语)留给了个体生命(个别的意志),如此,个人不会由于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最终得到平息,让“永恒正义”在未来实现,在他不再存在的世界里完成。瓦格纳眼里,痛苦仅仅是材料,是不可遏制的意志渴求的符号,他创造出的形象,如唐豪瑟、特里斯坦、安福塔斯莫不如此渴求着。这样,个体便得到了开脱,他不必为了在他生命结束之后迟来的终极正义,承受无止尽的痛苦,于是,人甘受他人痛苦的同情道德,安然地转变成强者对弱者的道德。
作者把老“自由派”公民叔本华树立为旧道德的代表,瓦格纳《特里斯坦》里的马克国王,则是向新道德过渡的折衷人物,守旧派在对马克国王的嘲讽中,完成了对新道德的屈服,在一个强者占有弱者财富的世界里,正因为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罪的,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只不过代价就是得不到任何“永恒必然”。所以作者说,瓦格纳“对个人的开脱有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意味着,糟糕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诅咒,一份破产判决,而是一次赐福,一个强盗团伙的加冕。瓦格纳洞察了这样的世界,运用艺术创作复制了它,并把这个过程上升为哲学原则,只不过这原则没有带给人丝毫尊严,瓦格纳却向它低头。
如尼采说,瓦格纳式管弦乐音的特点就是“无罪责”,它正说出了“现代灵魂”的意义,然而,瓦格纳或许也有不得不背叛旧道德代表的苦衷,如尼采说,这位代表指摘“黑格尔与谢林的时代不诚实”,可他并没有比同时代的名人“更诚实”。
叛变了艺术
瓦格纳在1850年代转向悲观主义之前,已经写完了大部分作品,这注定需要他修改或是重新解释与演绎自己的作品,这样做不仅会引发瓦格纳自身的混乱与尴尬,也给后来人布下了层层迷障。但在作者笔下,由于瓦格纳的解脱构想就是无(或称虚无,以之为内容),所以,这个构想本身也是空洞的,以便能装下无,结果,它只剩下没有内容的慰藉功能。后来,这个空洞的构想被搬上了舞台,沦为了一种舞台“幻境”,也就是竭力去呈现无之物,展现无的现象,因此,瓦格纳的作品对肢解性力量的认同达到了极致,无耻地赞颂有(或称存在)的毁灭与堕落,比如在《指环》里,虽然最后的世界末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人们几乎可以说,在救赎的名义下,死者再一次被骗”。
此外,瓦格纳还在舞台上叙述了自然中的历史,那么,无作为自然存在的辩证要素(没有无,有又何在?),又被自然指示出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比如,莱茵仙女们把夺回的戒指带回家,沉入水底(有的沉没),于是,无便在这水深中,被规定了出来(有的毁灭正指出了无)。瓦格纳在最后的岁月里,执着于那些身处这深度之中的混合生物,比如,花园中的魔女,歌德的迷娘,乃至于妻子科西玛。如尼采说,当人问,瓦格纳在音乐史里意味着什么?可答,他使“表演在音乐中冉冉升起”,且看他如何“向虚无的本能献媚,并在音乐里把它伪装起来”。
至此,我揣测,作者如果预见到,为了装下瓦格纳空洞的构想,《试论瓦格纳》这本书的各篇自己也得先是空的,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要冷静地去解剖瓦格纳,动用许多材料去填充,以使自己与瓦格纳的颓废散发出的魅力(Zauber),软弱产生出的共鸣,始终保持着距离。但这么做也极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可是,我恰恰觉得,我们现代人,自认拥有“现代灵魂”的人,既然已经不断地屈服于强大的、更强大的力量,又不愿意相信没有科学做担保的来世与永恒,那是时候了,听听瓦格纳。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