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零九年夏天,我所在的杂志做了一期保卫南京古都街区的专题。这原本只是一个2000字的小报道,没想到成了封面故事。对大部分香港同事来说,南京只是一个地标,一个他们还可以在诺大的中国地图上,大概能找到的地方。八月的香港,闷热极了,人们快速地行走、高效地工作,谁也不想多停留一秒,去关心这个千里之外的古都,那一砖一瓦的拆除或保留,实在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杂志出刊没多久,一位同在文化圈做事的香港朋友在MSN上和我说:“葛亮看了你们的报道好开心,他是个在香港的南京人,想和你们联系,我让他直接找你行吗?”
我当然乐意,那几天,我正好开始读他的《朱雀》。我尊敬的王德威教授评价说,“徘徊在南京的史话和神话之间,《朱雀》展现的气派,为葛亮同辈作家少见。”王教授还将此书收进了台湾麦田出版社《当代小说家系列》。作为这个系列里最年轻的作家,才过而立之年的葛亮,让我很是好奇。
见面时,我们很自然谈到《朱雀》,“朱雀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在上古中国神话里,朱雀被视为凤凰的化身,身覆火焰,终日不熄。根据五行学说,朱雀色红,属火,尚夏,在四大神兽中代表南方。早在东晋时期,朱雀已经浮出南京(建康)地表。”
他说他用五年的时间写《朱雀》,还了欠南京的一个情。这让他的写作变得有了责任感,这一点我很意外。我说我正在读,他很开心。但我向他坦言,我不喜欢小说的中间部分,他也没有不悦,只是很耐心地问我为什么。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那些惨烈,天天在我脑海里重演,躲也躲不掉。所以当我在《朱雀》中又看到这段历史时,有些本能的抗拒。而且因为这段历史太过熟悉,对小说的读者来说,就少了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显得牵强。可是我也明白,对于有野心要为“南京的‘过去’与‘现在’造像”的作者来说,这是跨不过去的。
南京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 我脑海里还依稀能想象的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去过南京两次,秦淮河的那份情和魅早已被廉价的工艺品商店成堆成堆地挤了出去,留下的那份俗气让我不忍停留。没想到这样的一家店,竟然写在了《朱雀》的开头,可能这也是当下不能回避的真实南京吧。正如葛亮所说:“写作之初想表达的是这座城市在现代化的清洗之下,还可以保持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古典姿态。但是在后期写作的时候发现,这种姿态已在慢慢地弯曲和凋零。”
“这个城市,从来不缺历史,有的是湿漉漉的砖石碑刻供你凭吊。十朝风雨,这该是个沉重的地方,有繁盛的细节需要承载。”
这城市的“常”与“变”,犹如年月的潮汐,或者更似暗涌。
交谈之后,我才发现,虽然离开十年了,可葛亮对南京的感情很深。不是一般意义的家乡,是有故乡的味道,他之前的一部作品《七声》,写的也是在南京的人和事。他写南京,是有“瘾”的。
这种借城市叙述的写法,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并不少见。记忆中有张北海《侠隐》里的北京(严格来说是北平)、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还有朱天心笔下的《古都》台北、香港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生》。王德威说:“她们以个人的爱恨痴嗔将大历史性别化、民间化。”
这样的审视和寻找联结的书写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福气。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的人和一个城市的命运息息是相关的,我们却总是忘记这一点,以为个体只是历史长河中溅起的一滴水花,轻易地放过了。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和莫言老师聊天时,他曾经说过:无论是多美的城市,在他眼里,也难以替代二十年岁月痕迹在他脑海中留下的故乡的乡村记忆。那土地的气息,花草的清香,甚至是烈日下牛羊的骚味,在他眼里也比灯红酒绿的现代城市来得更让人倾心。
这种情感在我们年轻一代很少见了。以前交通和科技不发达,人一辈子能活动的地域、了解的世界很局限,会对脚下的那片土地有依恋;可现在不是,只要数小时的飞行,几乎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发达的互联网,把全世界的人都连在了一起。人们认识世界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变了,新鲜的人与事接踵而来,缺的只是时间去沉淀出一种深层次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渐渐地,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对什么都不那么在乎了,或者说,没有什么真的能让你刻骨铭心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倒是很感谢《朱雀》,它让我发现了故乡的意义。那些在大城市漂着的年轻人,会在卸下一天的疲惫、安躺在床上的时候,想起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吗?想到故乡,会有那种淡淡的甜暖到心窝窝里去吗?
或许已经很少有人会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翻出故乡的过往看一看吧,仿佛年年岁岁在那些街道、胡同和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早已被冲刷得干干净净;那些故乡泥土里散发的清香,早已被汽车散发的尾气掩盖了;那些融在我们血液里的气质和味道,也与故乡不相关似的。
可你我之所以成为你我,哪有这么多的理所当然。我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葛亮要将《朱雀》的男主角设计成异乡人的身份了:
“在原本以为熟识的地方,收获出其不意,因为偏离了预期的轨道。一些郑重的话题,在我的同乡与前辈们唇间,竟是十分轻盈与不着痛痒。他们带着玩笑与世故的口吻,臧否着发生于这城市的大事件与人物。偶然也会动情,却是因一些极小的事。这些事是无关于时代与变革的,隐然其中的,是人之常情。这大约才是城市的底里,看似与历史纠缠,欲走还留,却其实并不那么当回事,有些信马由缰……我突然醒悟,所谓的熟悉,让我们失去了追问的借口,变得矜持与迟钝。而一个外来者,百无禁忌,却可以突围而入……”
因为《朱雀》,我和葛亮成了好朋友。他现在香港的一间大学教书、做研究,每次聊天他都会提到文学、说起写作。你会发现,那真是深入到他血液里的东西,可以让他平静。这感觉真好。
葛亮是典型的双鱼座,执着、较真、凡事追求完美。连书稿里出现个错别字,都忍不了。可他性格很好,对人谦虚、友善,长得又很帅气,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他会被他的学生们欺负。听说他的学生刚开始也都这么认为,但后来都很喜欢他,因为发现这个年轻的老师真的教给他们很多真才实学。
可是,繁重的教学负担,总是让他找不出足够的时间,专心写作。但他的生活与很多仅以写作为生的香港作家相比,倒是安定很多。人在香港,写作这件事,在生计面前,显得特别无助。这让我对于他付出的五年光阴,尤敢敬佩。我总是很好奇,因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他,如何在这两件不相干的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中寻找到平衡。他觉得这个平衡之于他,倒不算太难。也许这就是南京给予他与生俱来的脾性吧,总有些漫不经心。
这我想起葛亮最喜欢引用《儒林外史》里头的一句话来形容南京:两个平民,收拾了活计,“就到永宁泉茶社吃一壶水,然后回到雨花台来看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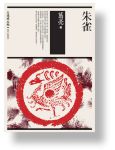 如果不是因为南京,我想我也不会有机会认识葛亮。
如果不是因为南京,我想我也不会有机会认识葛亮。
- 数字100发布《中国城市居民金融消费情态与趋势》报告 2010-08-27
- 南京准“地王”入市 “内定”传言再起 2010-08-27
- 谋划民企CBD 赵汉忠“老枪”归来 2010-08-26
- 北京:世界上最堵的城市 2010-08-25
- 首届(2010)中国城市科学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2010-08-22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