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18-08-08 11: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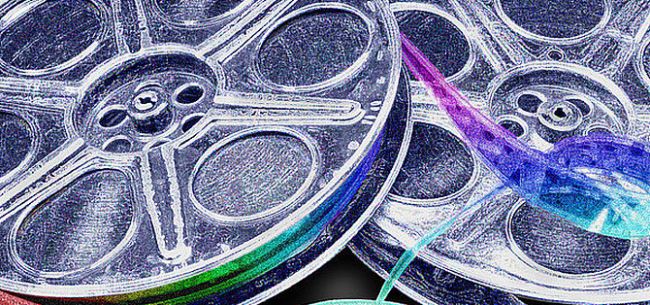
(图片来源:全景网)
对谈:王小鲁(电影学者)
余雅琴(电影策展人)
五
余: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科幻片和人工智能、平权的问题,是否回到你刚说到的命题上来?你去年跟我谈“电影终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猜测和有些学者“电影已死”是一个论调,但我看你以前的文章,对新技术的看法似乎并不像他们那么悲观。能不能解释一下?
王:其实是这样的,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科幻电影和剧集出现以后,我发现电影本体论和人生本体论的交叉越来越厉害,这么说当然有点夸张。我说“电影终结”的时候,我想到更多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我其实一直对于后者更感兴趣,我发现任何一个体系性哲学家,往往都会为自己言说的世界提供一个终极图景。马克思、黑格尔都有自己的“终结论”,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所以终结并非死掉,而可能是预知到了一种理想的稳定的未来,所以这个概念无所谓悲观乐观。令人沮丧的是,我个人很少读学术期刊,我们刚发现这个电影终结很多人都在提,不是新词,如果早知道这一点,我也许就会放弃这个词语。但是我想这种雷同可能有几种含义,一是知识和现代生活的世界性,使得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有类似的发现,至少聚焦点有时候会比较一致,历史运行并非偶然;另外从别人的转述里面,我觉得我的想法和其他人似乎并不一致,所以我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表达。
余:我发现目前的一些研究还是将西方的学术发现介绍过来,观点听起来一样,其实还是有差别。比如说电影已死,认为电影这门艺术将要消失,而我知道你的发现是在自己的经验里推演出来的,有自己的脉络。
王:我也看到国内学者在宣布“电影已死”,我觉得它表达的是对胶片的迷恋,因为“电影”的译法一个是Film,就是胶片,而Cinema,就是剧场的意思,当然Movie(运动)这个译法还没有带来那么多麻烦,这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后,电影丧失了胶片时代特有的质感和手工感,而且数据都在硬盘里,手摸不着,这让人感到空虚。当然,电影已死还可能说的是当传统电影媒介的边界消失,这带来了电影自性的危机,当一个东西无所不在,它就无所在了。但我不喜欢这种论述,我们也可以说电影逐渐分化为传统院线电影和多媒体电影,电影更多元了。而且电影在中国就是电和影的组合,在日本它叫映画,Film死了,映画未必死,Image未必死。我说的电影终结的意思和福山的历史终结有点相似,就是对电影终极图景的想象,有人认为谈终结是对人类想象力的轻视,但我宁愿将这看作一个戏仿,一个想象力的自我训练。
余:我记得桑塔格也说过电影之死:如果电影迷恋死亡了,电影也就死亡了。这是电影百年的时候说的,1995年美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她在这个时候说电影之死,大概是指艺术电影的没落,她说大部分商业片过于媚俗,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精英化的。
王:桑塔格有她的角度,但就当下的中国经验来说,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不考虑电检的因素,这些年商业电影的发展其实是给了艺术电影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空间,这一点早就论证过了,而且中国电影院吸引力的重建,商业大片尤其是3D电影其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英雄》到《阿凡达》。就好莱坞而言,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从偏重叙事转向偏重视觉奇观,用大场面来营造吸引力,这个转变就是从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卡梅隆等人的科幻片、奇幻片开始的,这个现象到90年代愈演愈烈,我相信这是桑塔格说那番话的背景。可以看到那时科幻片奇幻片并没有被学术界重视,他们还将这些看成脑残娱乐,远远没有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启发性。
余:《黑客帝国》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样的现象,学者们纷纷用这个电影来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当然,这是后来的事,电影和科技的发展都太快了。
王:记得《黑客帝国2》上映不久后,电影学院一位老师讲课时激动无比,说以后的电影(不是指动画片)可以不用真人演啦,全是数码制作,表演系的应该有危机了。我当时觉得这老师太狂热了吧,但后来证明他很有预见性。电影的这种进化,我们是有见证的,才几年就有了这么多技术飞跃,3D的重新崛起和新媒体电影的花样翻新,VR技术,尤其是前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120帧电影的讨论,重新激发我对于电影本体论的热情,我觉得这些技术连在一起看,未来电影的形态似乎就可以推断了。后来看了《西部世界》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词——电影意志,我其实是从“电影意志”这个角度,推出未来电影的可能性形态也就是所谓电影终结来的。
余:那篇文章我看了,很多人在转载,当时读了文章以后还觉得有点激动,这个词仿佛将电影赋予了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当然这是我主观感受的东西,你可以谈一下其中的逻辑。
王:一般认为电影是在1895年在法国被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异议,英国、日本、美国其实都有更早的实践,就是说,电影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差不多的时间里被发明出来的,这证明它来自于一种普遍的人类意志。外国学者说,电影其实在它出现前的几百年就在人的脑海中被制造出来了,银幕娱乐活动在1895年前已经有250年历史,当时人们利用画片和会动的玻璃投影到银幕上制造动感,所以说电影意志是人类普遍意志的表达,这个意志是什么呢?就是对抗时间和复制现实,不仅仅理论家巴赞说过这些内容,我阅读中国早期电影人的文章,也对电影永久保存的功能有强烈认识,这都是大而化之来说的,这个过程还会牵扯到具体技术条件的发展,巴赞强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完整电影”,这概念也不是他首创,但是他做了重要的发挥。所谓完整电影就是完整复制现实的电影,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2D到3D,这样演化下来,电影越来趋于完整,但还是达不到真正的完整,所以巴赞在40年代说,电影还没有真正诞生呢,其实他所说的完整电影,说的也是一种电影的理想状态,和电影终结有点相似。
余:其实电影终结并不是说电影活动就从此停止了。
王:对!历史的终结设想的是一种人类所可能想象到的最好社会样态,一种无法再继续设想下去的样貌。福山谈历史终结的信心,基于他对人性的了解,因为人有一种渴望被承认的冲动,这种冲动只有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才能被满足,而电影终结其实也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克服时间的流逝、渴望复制现实也来自人的本性。3D之后,观众还是和电影角色隔膜,后来出现了VR,就更进了一步,还有一种就是《西部世界》所预言出来的模式,都可以说是电影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完整复制现实的冲动,到这里近乎实现了。
余:我觉得《头号玩家》也展现了未来电影的可能性,在绿洲里面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虽然里面的虚拟空间还是工程师搭建的,但是你可以参与改变,可以在里面约会或者打斗,主人公生活在贫民窟,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他一戴上VR眼镜就可以进入绿洲,变成英雄,穿上一种特殊材质的衣服,游戏里的触感他就能体验到。
王:这个游戏情境——现实中的匮乏到虚拟世界寻找满足,与电影很是契合。90年代末比尔·盖茨就在设想一种“虚拟紧身衣”,跟《头号玩家》里的装备很相似,从影像上来说,主角戴上VR装备后所看到的自己是他的虚拟替身,这在1975年的《未来世界》里就有了,这一切的发展似乎都在历史理性当中。这种虚拟替身可以带领观众进入现实场景,然后可以和里面其他角色互动,这可以作为一种未来电影的方案。《西部世界》里设定了电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观众本人进入一个真实空间,和里面作为角色的人工智能发生各种关系,从外部环境来说,这是最逼真的,毕竟它和真实生活一样是四维的。当然这里不是用介质来界定电影,如果你用介质界定,也许这早就不是电影了,但这是按照电影原初意志来推演的形态。我是觉得,这种形态最好是某些我们迷恋的影片的升级改造版,比如《泰坦尼克号》,我们进入其中的场景,遇到一个作为实体存在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的实质是人工智能,观众与它互动的丰富性可能不够,这就牵涉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伦理问题,就是是否让它们拥有自由意志的问题。
六
余:这其实又回到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上去了。科幻电影里面有一种悲观主义,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大家认为人工智会进化得比人类更优良,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说,人就被淘汰掉了。那你觉得是否应该让它们有自由意志呢?
王:英国《卫报》为纪念《2001太空漫游》50周年做了个专题,一位导演说:“AI已经变成了神一样的存在,问题是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的观点是,它和输入它的人一样好和一样坏。”这话很有见地,但似乎也有逻辑问题。《机械公敌》其实讨论了这个事情,AI公司给人工智能输入了保护人类安全的机器人三定律,三定律环环相扣,但这个逻辑最终却演化出来一个可怕的结果——AI会为了人类的安全而反叛人类。所谓的逻辑,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上帝工作的原理,但人类所理解的逻辑仍然是有漏洞的,《机械公敌》演示了这个漏洞。而且我们强调人工智能是可以自我学习的,在这过程中,会不会因为一些逻辑漏洞而逐渐失去把控,如果机器人真的有了自由意志,怎么会甘心做“人类逻辑的奴隶”?
人工智能和电影的关系,一是它作为电影题材,现在则是作为可以和观众真实互动的电影角色。但电影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对于人的精神性的满足,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具有自由意志或更复杂的情感,可能就会和人形成一种对抗关系,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还是有限的。我这里采取的还是比较人文主义的立场。到这里其实我还想说,前面谈了那么多后人文主义和机器人怪兽外星人,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遵循人的逻辑来想象这一切的,每次我看外星人题材电影都会失落,我觉得事实上我们还是在使用地球的逻辑来塑造对方的怪异性的,哪怕是《降临》这种非常有新意的影片,他所谈的交流问题的解决,一样是根据人的心性来叙事的。事实上,作为人,我们是根本无法以非人的角度想问题的。电影终结时的观众必须还是人,这大概是我们想象的一个界限。
余:好莱坞的《复仇者联盟》系列票房居高不下,我觉得不管里面是蜘蛛侠、绿巨人、雷神其实都和人一样,缺陷很明显,优点也是人的优点,他们向往的东西也是人所向往的,近30年来好莱坞最火的明星几乎都演过科幻片里的非人角色,哈里森·福特、施瓦辛格、裘德洛,他们代表了更美好的人体,这让我们更加认同他们扮演的角色。
王:对。科幻片里面,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就是Real,《人工智能》里的小男孩很忧伤,特别期待成为一个Real Boy,真正的男孩,《银翼杀手2049》里面也一样,其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对于自己至尊地位的迷恋,这就是所谓后人文主义气氛中隐含的坚定的人文主义。《头号玩家》最后强调了“真实的生活”的优先性,但真实的生活究竟是指什么呢?它并没有对此展开思辨。
余:机器人有伦理问题,VR似乎不太需要讨论这样的伦理问题。除了上面说的几种形态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电影的可能性,就像英国《黑镜》里面表现的那样,人的大脑里植入芯片之后,可以通过大脑和一个投影设备连接,放映出大脑中回忆的影像。
王:其实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美国正在研究的机脑连接。还有一种全息投影,在《第五元素》还有《银翼杀手》里都有展现,最早的《星球大战》里就有这种东西。但这些是否还能作为电影或者新媒体电影的一部分?可能还是需要界限划分。无论如何,这样的一种未来科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肉身有限性的超越。电影也是如此,而且最终形态的电影,不仅仅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这样的超越使得人变成了神,人神时代即将来临,当然这不是新观点,西方学者早把这个写进书里了,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见解。其实前些年看电影,经常发现未来科幻和远古历史、神话元素结合。神话是人类意志的表达,电影也是,电影和神话的联盟出现了。过去神话仅作为电影的题材,现在电影将成为把神话现实化的手段。电影和神话的关系可以阐发的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电影中的重要角色都有古希腊神话的原型,比如阿芙罗狄忒是《本能》里面莎朗·斯通的原型,其实学者也乐于寻找电影的原型,巴赞找到古埃及木乃伊,精神学派找到了柏拉图的洞穴,中国人找到汉武帝的帷幕投影,西方也从古希腊神话找到AI的原型,古希腊工匠神就打造过美女机器人,而中国人则可以在关于西周的记载里找到AI的原型,那个人造人可以唱歌跳舞,周穆王说,人类的能力简直和造物主差不多了!其实电影和AI都来自人对神的模仿。
余:《X战警·天启》里面,讲了世界上第一个变种人的故事,很多电影都在神话里面寻找灵感,这个电影里面的暴风女和神话故事的雷神电母的感觉差不多。
王:我这里特别想解释一下“电影意志作为人类意志的表达”这个说法,从某种哲学来说,人类意志作为一种集体意志就跟历史规律一样,个体很难去左右,其实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现象,人类意志是一种按某种逻辑自动运行的东西,所以可以推断电影意志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电影具有自己的意志。“电影意志”这个词很酷,因为它好像把电影变成了人工智能,马丁·西科塞斯的《雨果》是向早期电影人致敬的,其中设计了一个情节,梅里埃制作了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画出了最早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的场景图,梅里埃还说,要想了解电影必首先得了解原始洞穴的象形文字。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都不是偶然的。当我说“电影具有自己的意志”,我会说这是一个比喻,不然别人就会觉得特别奇怪,但是我们经常说“电影遵循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这句话我们并不觉得奇怪,但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同一种哲学的产物,黑格尔认为一切实体都是主体,那么电影作为实体,也是活着的主体,不过这样的哲学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接受了。
余: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人工智能也具有自己的主体,它也能自行演化下去。但是这很让人担忧,最近雷德利·斯科特说,人工智能要牢牢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但问题是,总有人会挑战界限和伦理,将这种技术发展下去,一种技术一旦出现,就肯定会运转下去。
王:你说的这一点其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观点,我觉得可以从中推出一个悖论:人类是无法阻挡人类意志的,这个人类意志其实是脱离了个人也因此是脱离了几乎所有人而存在的。我读马克思,发现虽然他曾经崇尚个体自由,但这部分很抽象,没有具体内容,他推崇的主体性多是集体主体性,而非个体主体性,越了解这些学说越会发现,就个体而言,历史几乎是自动演化的。这很让人沮丧,因为个体主体性事实上被取消了。但这种思想相信历史进步论,人类生活最终是乐观的,推崇资本主义的福山其实也相信这种历史进步论,它的历史终结的理论被人嘲笑,因为后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大量民主倒退的案例,但又经过了几十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福山觉得自己的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有些时候,这和我研究电影的感觉差不多。从电影意志的角度来看,为什么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DV纪录片浪潮,一些业余作者拍出了不少好作品,推动了艺术和社会发展,我在观看的时候,常常觉得作者之外,日本的SONY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署名权,因为这种便利的技术使得电影天然获得了那样的新语法,在这个浪潮里面,电影技术的主导性是巨大的,它和中国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到它就是历史理性的化身。后来这个浪潮遭遇了人为的挫折,但如果你相信历史理性,你就会知道目前一切只是小漩涡,最终的走向绝非如此。这是我的一个信念,但这个信念并非仅仅来自于主观。
余:你说的这些我很理解,但你这么一说,我会觉得电影作者被大打折扣,因为我们一般认为艺术是个体的表达,是用来表达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在电影的终极形态里面,人在哪里呢?
王:我非常理解你的话,其实上面所说的都是特别本体论的东西,都是电影提供精神满足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复制真实的质感,电影人物和故事才具有各种感染力。至于你说的个人表达的电影、戏剧化电影甚至实验电影该怎么存在,我觉得当然可以共存,但旧问题仍然可以用新形式来承载,人仍然是作为观众和有限的创造者。但是未来电影必然存在于未来的生存感受中,电影表达人类悲欢,但当时空感受和人类自身改变后,人的情感模式也会改变。如果人可以长生或更加长寿,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焦虑就都被化解掉了,过去唐诗里很有魅力的是离别美学,见到柳树也伤感,“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在那时候生离即死别,由于交通和卫生条件,山川阻隔里面包含着巨大的悲痛,正因为太悲痛,所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才那么珍贵,但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感觉,这种诗意,以后的人类也许就读解不出来了。新技术的出现可能瓦解旧的对抗和权力关系,电影的旧有表达模式也可能会因此做出巨大改变。就好比权力压力增加,知识分子比我们想象得更易于撤退,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想到这些就特别难过,我和人开玩笑说,未来也许只能依靠人工智能了,也许来一场技术革命就能将陈旧的权力关系瓦解掉,实现与社会革命一样的效果。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