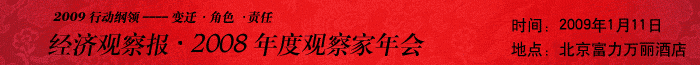中美三十年:如何重寻黄金年代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雾的重庆让人浮想联翩。这座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首都,现在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金融时报》前驻中国记者詹姆斯·金奇称它是中国的芝加哥,它的发展将像芝加哥在美国的崛起一样,带动一个国家整个西部的发展。它还为目前正在经受挑战的中国制造业输出了大量的年轻工人。他们搭乘火车或者长途汽车颠簸30多个小时抵达东莞或者深圳的工厂,留下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在故乡生活。在我走访的一所重庆开县的小学内,89%的孩子的父母都在沿海工厂打工,他们被戏谑地称为“留守儿童”——这所学校大概拥有学生3200人。
它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让曾经对它熟悉无比的人也感到陌生。1983年,当白修德(西奥多·怀特)再次回到这座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迷失:“在我一度为家的这个城市里,现在我只能认出两个地方:一个是狭窄幽暗的、周恩来过去办公用的共产党党部,这里曾是我经常来往的地方,我习惯在鹅卵石铺设的人行道上散步,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条林荫大道……另一个地方是旧城墙留下的惟一的一个门——通远门,尚保存完好,以作为考古学家对近代和古代历史的考证。”尽管是公认的中国的朋友,白修德和他的老师费正清在1940年代离开中国之后,也只是在1972年才得到再次访问中国的机会。他们当时是作为中国专家跟随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时的白修德几乎已经忘记了他在重庆学会的汉语,但是仍然被周恩来一眼认出。周恩来指着他用主人常用的客气话埋怨他为何在1949年之后从未到过中国,白修德回答说,“这可不是我的错”。费正清则用俏皮话说明了从那之后中美之间的尴尬处境:“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还多。”
在此之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却处在一个短暂但甜蜜的黄金时代。只要到重庆看一看我们就会明白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之间的感情。马歇尔别墅仍然耸立在重庆的黄山上,从那里走到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只需要十分钟。曾经出入这所官邸的人包括乔治·史迪威将军、亨利·卢斯、陈纳德、司徒雷登、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当然也包括马歇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将蒋介石抬升为世界的五巨头之一,尽管丘吉尔对此颇不耐烦。罗斯福赞扬重庆人民在轰炸下的勇气将激励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他说“保卫美国的关键在于保卫中国”。史迪威将军训练他的中国士兵,和中国将军孙立人在战壕中交谈,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其中包括著名的中国专家包瑞德和谢伟思——穿着中山装拍集体照。美国妇女们用医用棉花擦拭中国伤兵头上的污痕;中国农民则用滑竿将受伤的美军士兵抬到三十里地外的医院;中国厨师为著名的飞虎队烹制可口的饭菜。中国的报纸上还登出了美国的国旗,号召读者记住美国国旗,鼓励他们救助美国军人。双方都对对方存在着炙热的情感。亨利·卢斯在写给《时代》驻中国记者站的信末落款称自己是“TheOldChinaBoy”,作家斯旺博格说卢斯在1943年造访中国时,受到了自马可·波罗以来最热烈的欢迎;中国士兵亲昵地称史迪威将军为“乔大叔”,著名的滇缅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然,在这种炙热的情感之下掩盖着的是他们各自内部的分歧。卢斯强烈支持蒋介石的中国,史迪威对此却不屑一顾,包瑞德和谢伟思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中国抱有好感,白修德更是对蒋介石充满反感、对周恩来赞赏有加。甚至只拜访过中国一次的海明威也称赞周恩来是中国最杰出的人之一——据说这位知名作家的赞扬让延安认为自己在外交上大有可为。
二战的结束伴随着一系列的产物,其中就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阵营之争。意识形态的争论让政治家们抛弃了现实感。中国被划归到美国的敌对一方。双方互相竞赛着为对方描绘可恶图像。美国国内在争论着谁应该为“失去中国”承担责任,中国则大声地宣布“别了,司徒雷登”——直到不久之前,这位燕京大学创始人、美国驻华大使、卢斯家族的挚友才算回归中国,被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
深刻而漫长的隔阂,终于被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与基辛格等政治家们打破。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经常猜测,如果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没有被刺杀,他的理想主义和新思维是否会让他迈出通往中国的步伐。不过最终打开中国大门的,却是政治家们重新回归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崇尚实力外交和区域均衡,尼克松总是在寻找能让自己成为伟大总统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则面临着自己领导的国家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双方开始了谨慎的彼此试探和信息传递。即使尼克松已经抵达北京,双方仍然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热情,故作冷漠。历史学家们翻出尼克松抵达当日的中国报纸,发现头版上仍然充斥着关于劳动模范和英雄母亲的报道,只是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提到美国总统到访北京。
在1972年,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创造了历史,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在她2007年出版的著作《尼克松和毛泽东》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在后来出版的简装本封面上,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作为副标题:“只争朝夕”。但即使如此,中美签订正式建交公报仍然要等到六年之后的1978年。这六年中,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也未能迈出进一步的破冰步伐。或许会让基辛格颇为不悦的是,正式建交这个荣誉没有由他来完成,而是由他在学术上的竞争者布热津斯基促成。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中国的实际领导者是邓小平,一个务实主义者。当邓小平询问美国人,他是否能够派遣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时,卡特总统慷慨地对他的下属说,告诉邓,他可以派20000名。
从1972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复杂而有趣。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研究了从1972年到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他出版的著作名字为《美帝》,不过,这里的美帝指的是——“美丽帝国主义”。美国曾经长期被宣传为敌人和用心险恶者,但是中国人却突然发现,正是这个国家萌发出了让人赞叹的创造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尤其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繁荣的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新的学习对象。美国则为中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精英人物。
两个大国一旦建立起外交关系,就像中国的古典婚姻一样,要想断绝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但是和婚姻一样,其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1989年当然是最重大的一次冲击。其次是1999年,访美的朱基总理希望能够顺利与美国达成入世谈判协议,但是克林顿总统却在一部分智囊的建议下含糊其辞。只是当朱基失望地离开时,克林顿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重大的错误,而媒体和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指责白宫在重蹈覆辙——它的无知和矜持打击了中国的改革派,从而帮助了中国的保守派,这不仅对中国不利,对整个世界也是噩耗。后来卸任的美国外交官谢淑丽在她2007年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描述说,朱基曾经相当动容地对美国官员说,自己的办公室每天都在接到中国各地示威的报告。而北约的导弹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更是让整个国家怒不可遏。被民族情绪鼓舞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发泄自己对美国的不满——后来也有人讽刺说,这些游行者中有人在第二天就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排队等候签证面试。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又一次人为地让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紧张不已。不过美国政治家已经越来越明白,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坚持,比如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关系。
在中美之间为各种问题争吵和纠结之时,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同时发生。在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症状明显出现之前,这个变化曾经是专栏作家们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崛起和与之相伴产生的各种问题。中国研究重新成为显学。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在全世界如成吉思汗的大军一样所向披靡;它的公司在全世界开始展开收购行动;它开始谋求自己的能源布局;它也试图寻找自己新的国际定位,改变低调行事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已经让西方人吃惊。它也先后尝试用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来描述自己的这种定位。
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都在说明中国地位的必然抬升。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必然要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衰弱这个词语可能并不恰当,它会给人一种暗示,世界正在上演它已经无数次上演过的帝国兴亡录。上一个衰落的帝国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尽管英国人熟知历史,但是直到衰落之前,他们仍然相信历史只是一种适用于他人的小把戏。
惯于夸大的媒体和并不严谨的学者也喜欢重新搬出这套把戏,把它加到美国身上,他们甚至试图为中国和印度加冕。可惜事实并不如此。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如法利德·扎卡利亚所说的“他者的崛起”——并不是美国本身在衰落,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在崛起。
这个有趣的变化必然带来中美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尽管缓慢,却影响深远。中国已经不再是罗斯福试图力举到世界舞台上的战后五巨头之一,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无论怎么解释,事实都是如此。
美国在此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呢?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被放置到一个更为严峻的背景下,那就是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该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已有的超级大国试图去管理正在崛起的力量,世界历史表明这种尝试都不成功,而且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德国的崛起不能被管理,日本的崛起也不能被管理。更加理性的做法是把新的大国引入到世界的议事厅。李光耀学院的院长、亚洲崛起的代言人马凯硕正是如此建议:为什么不向这些国家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要职务?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大国放置到联合国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或者,就中美关系而言,更加直白的是,为什么不能对你的债主客气些?这个说法最先由一个美国人提出,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对美国的建议。最近,这个说法则被一个中国人重复,中投的总经理高西庆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JamesFallows采访时,也这样说。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行动说明。重新寻回中美关系黄金年代的想法荒诞而不切实际。双方都不能容忍这个想法。中国人将那段历史看得别有意味。甚至芭芭拉·塔奇曼也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经历只能说明,必须把中国还给中国人,哪怕是好心的帮助也可能种下恶果。美国人则开始对中国心存警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行动难以确定的巨人。小布什总统向印度伸出的橄榄枝,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可以同尼克松叩开中国大门相提并论的外交革命。印度被视为盟友,中国则被视为潜在的竞争者,而不再如罗斯福总统所言那样,保卫中国就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行动纲领,那就是:现实感。如果世界不是那么理想和高尚,那惟一还能庆幸的,就是它至少还足够理智和势利,利益还能成为一个靠得住的准则。两个国家都不能再让一些不切实际的争论蒙上理性的双眼,无论这种争论来自哪个方面。最大的现实是,它们彼此需要,世界也需要它们在很多问题上彼此合作,比如避免区域战争、应对环境问题和消灭全球贫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