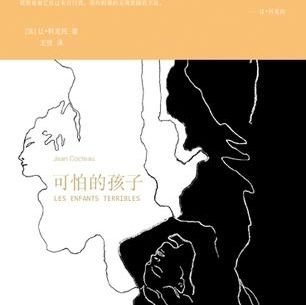
by btr

好友拉迪盖的离世对科克托打击颇深,科克托开始迷恋吸食鸦片;而《可怕的孩子》正是在他戒除鸦片毒瘾时创作的。《可怕的孩子》写于1929年,据说让·科克托在短短一两周内就写完了全书。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科克托说:“我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种力量或存在——我对之所知甚少。它下命令,我执行。《可怕的孩子》的想法,是从我的一位朋友那儿来的,他告诉了我一个圈子:一个与社会生活相隔绝的家庭。我便开始写:一天写十七页。写得很流畅。我很满意。非常满意。”
《可怕的孩子》始于巴黎蒙蒂耶住宅区里孩子们的一场雪战。主人公保罗——他是“整个中学里最引人瞩目的”人。保罗爱他——那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可怕的感觉,没有任何解药,那是一种纯洁的欲望,与性无关,亦没有明确的目标——掷出的、可能包裹着石块的雪球击中胸口。这情节仿似来自于某本青春、成长或教育小说,甚至具有情节剧常有的戏剧性,然而法国作家让·科克托却以风格化的诗性语言,敏感的想象和意象及准确、深入的心理描摹把读者带入一个异质的小说世界。
在科克托看来,这些五年级孩子身上“依然存在着那一股顺从于童年隐秘天性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同样牵涉到诡计、受害者、立即处决、恐怖、折磨和牺牲”。“同样”一词泄露了科克托的意图:他并非仅仅为写孩子而写孩子,而是要写出这些尚且简单的孩子们身上普遍的人性,要“回到孩子们的现实世界,由平平常常的细节所构成的可怕、神秘、壮烈的世界”。
在科克托笔下孩子们的现实世界里,“房间”和“游戏”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主要意象。保罗与姐姐伊丽莎白同居一室,时常裸裎相见,两人关系中虽然没有性的介入,却在情感层面接近某种柏拉图式的乱伦。依照家中看护马里耶特的说法,“她感觉这个房间的空气比外面的更轻。罪恶就像某些细菌一样,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高度。纯净、轻盈的空气,任何沉重、低贱、卑劣的东西都无法渗透进来。”于是,这“房间”便成为与外部现实世界隔绝并相对的、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的隐喻。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游戏”规则。“‘游戏’是一个非常不确切的说法,但保罗正是这样称呼孩子们喜欢沉醉其中的半清醒状态”。在保罗与伊丽莎白之间,“游戏”不仅意味着做白日梦一般的幻想,也包括彼此折磨、惩罚,甚或偷窃无用之物,以纠正“变得庸俗的倾向”。姐弟俩为“游戏”还创建了一套话语系统,如以“出发”一词描述游戏引发的状态。
就这样,《可怕的孩子》情节的演进及结尾的高潮,便表现为“房间”的更迭及“游戏”地位之变化及至“游戏”的终结。当母亲去世后,热拉尔有时留在蒙马特街过夜,此时“房间才成了气候”,他们将房间变成舞台,“戏”成为“房间”的同义词:“这出戏里的任何一个演员,包括那个观众,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个角色”。不久之后,伊丽莎白成为一名模特儿,她遇见孤儿阿加特,因其外貌酷似达尔热洛,保罗爱上了她。于是,“在伊丽莎白,甚至是保罗的生活中,游戏的地位越来越小。他们没法出发了。他们感觉心不在焉,在幻想时也总会有干扰。”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与富有的年轻男人米夏埃尔结婚后不久,丈夫就意外去世。这看似突兀的情节若在隐喻层面解读却颇为合理,科克托写道,“米夏埃尔跟他们的房间形成完美的对比。他对他们而言就代表着房间之外的世界。”在这里,“房间”之接纳或拒斥,成为能否建立人际关系的隐喻;也因此,当他们搬进米夏埃尔留下的豪宅时,保罗便立刻开始行动,用屏风围起一方杂乱的领地——这不啻是完成了“房间”的重建。
在高潮部分,科克托以四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基点,书写“游戏”之终结、“房间”之崩坏。伊丽莎白无法忍受保罗对阿加特之爱,便暗中使坏,唆使热拉尔与阿加特结婚。然而,热拉尔与达尔热洛之重逢将故事带回起点,另一个球状物——一团毒药改变了保罗的命运。他投药自尽,并写信给阿加特表达爱意,于是伊丽莎白的计谋败露。她抓住手枪,内心已然崩溃,“这个房间正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陡坡上滑向终点”,爱与死在伊丽莎白自杀的那一刻“撕开一道伤口,令这个隐秘的房间如舞台般展现在观众面前”。此时,“游戏”戛然终结,“房间”如同孩子们长大一般倏然消解,叙事也在两个主要意象的变奏间达到诗意的高潮。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