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湛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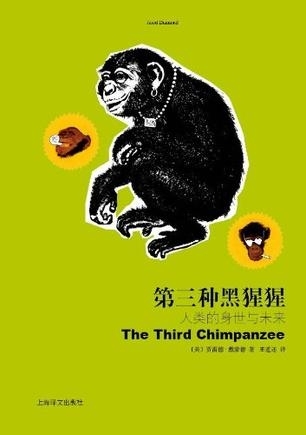
生活越来越像一部科幻片了,环境破坏、气候变化、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以及时不时发生在现实中或精神上的战争。我们如今有幸也有能力窥见这一切,前无古人,继往开来,以致于不需要把时间往后推,似乎一切困难与问题都是新生儿,每个人都毫无理由地去坚信人类与环境曾经有过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是科技与文明进化的双刃剑把现实劈砍成如此美丽又如此丑陋。如果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你们都错了。”那他八成是个科学家,要知道,科学总是违反常识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一如生物演化学的鼻祖达尔文多年前所做的那样。
人异乎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但是哪些关键因素使人所以为人?除却那些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标识:语言、艺术、农业,很不幸,吸毒也要被涵盖进去。在科学面前,一切道德名词都是乏味又无力的,写就科学,唯需根植于事实的推理。《第三种黑猩猩》是戴蒙德被授予麦克阿瑟基金后,决心将自己的思考传播给大众而写就的第一本科普作品。虽然他并非人类演化学的科班出身,但正如《第三种黑猩猩》的译者王道还所说,作者恰是因此,在精神意趣上成为了“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
戴蒙德是一位生物地理学家,他的经历颇值玩味:童年时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父亲在他的卧室墙壁上挂了两幅巨大的地图,一幅是欧洲地图,一幅是太平洋地区地图。随着战况的变化,父亲每天都会移送地图上的别针,这激发了他早年对地理和历史学的兴趣。在成长过程中,他爱上了对野鸟的观察,并因此决定从事与生物学相关的职业。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还继承了母亲的语言天赋,学会了12种以上的语言。所有这些都使他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解释科学,打破“两种文化”(人文与科学)的分庭抗礼。
一个带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家的视角是别具一格的,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探讨了许多使我们困惑却被我们忽视已久的问题: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的农业并非只为人类带来好处,事实上,女性地位的变化,阶级的形成,都是自农业被“重新发明”之后的事;人类会明知有害,却故意地去吸毒、酗酒、摄入烟草,持续这种行为原因或许是“上瘾”,但愿意去尝试则可以用动物界的残障原理去解释——只有那些对个体有害的构造和行为,才能有效地显示发出讯号的个体是诚实的,例如“我的身体足够强壮”。而人与动物在这点上的关键性差别,只是动物看似“自毁”,实则利大于弊,人类却是真正的代价远超收益。
虽然人类的很多特征都并不能使我们对未来更加乐观,但在戴蒙德看来,真正有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则是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在地球上无止境地扩张,伴随着征服、驱赶和杀害其他的族群。“我们成为彼此的征服者,也是世界的征服者。”戴蒙德以科学的推理追问:为什么某一族群拥有征服其他族群的文化优势?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秀,事实上,一些父母还停留在石器生产的人,子女现在却以开飞机为生。“有些社会的文化习俗成为世界主流模式,不是因为那些文化习俗可以令人幸福或者有利于人类的长期生存,而是因为那些社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各大洲的文明业绩不同,是因为塑造文化特征发展的力量,是地理,而不是人类遗传学。”
本书的第四部分被命名为“世界征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戴蒙德留下的经验使他对战争有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是科学式的,而非哲理性的,戴蒙德将人类视为第三种黑猩猩,也以对黑猩猩观察的实例指出:所有人类的行为特征中,最直接从动物前驱中衍生出来的就是灭族屠杀。曾经有人类学家提出,人类演化的过程受人类狩猎的需要驱动,戴蒙德觉得这也许是个事实,“只不过,我们狩猎的对象也是人,我们是猎人也是猎物,因此我们被迫群居。”
责怪被害人这一心理变奏使得灭族屠杀有了合理性,对于那些“站在错误一方的人”,怎么做都可以,包括灭族屠杀。人们例行公事般将受害者比作畜生,各族语言中都不乏其辞。最可悲的是,灭族这种悲剧性事件并不会给第三方造成什么影响,很多人或许不以为然,但实际上,细数人们对某些事件的关心,例如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实则了了。由于我们甚至不曾记得,因此这类前例也就更加无法成为阻止新悲剧酿成的契机。人类目前杀戮外族的能力随着武器的愈加精良已空前强大,而随着社会间冲突的加剧,相互厮杀的欲望也逐渐升高,人类有能力毁了别人,也有能力毁了自己,这在今天越发不是杞人忧天。
所有这些现实无不使人悲观,更早之前就有人发出过叹息,探险家维希曼预测人们会重复前人的错误,因此在其所著的《新几内亚探险史》中以一句“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作为结尾。如今有无数的科幻片展示着人类最后的穷途末路,但戴蒙德却说,如果相信毁灭的命运早已注定,他便不会写这本书了,人类的命运远未可知,或许我们要比两种黑猩猩幸运多了,谁说的准呢?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