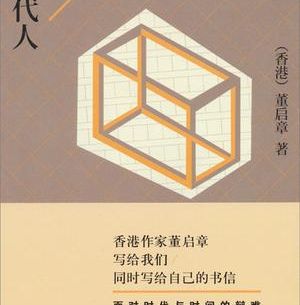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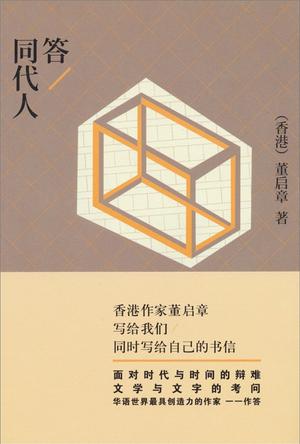
作者: 董启章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撰文:btr
从482页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上下合计共886页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到710页的《物种源史·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香港作家董启章从2005年起潜心构筑的巨著“自然史三部曲”眼看就要完成,但自2010年出版《学习年代(上)》迄今已近三年,完结篇却迟迟不见 踪影。
2013年3月,当董启章又一次拿起笔时,这完结篇悄然起了变化:“自然史三部曲”并未虎头蛇尾,而是——照小说里道人的说法,“蛇尾又生出虎头来”。这一次,董启章意在“虎蛇一体,首尾相应”。发表于4月底出版的《天南》文学双月刊的4万字,便是其新作《<自然史>前言:美德》之前奏。
我们的采访约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一间叫作“rice paper”的越南餐厅。餐厅旁有一个大型室内溜冰场。董启章的短 篇小说《溜冰场上的北野武》写的就是这里。对于董启章来说,小说世界就像这个溜冰场,是一个剧场般的存在;而作家的职责,正如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言,是 “把自己的心化作舞台”,搭建一座文学里的剧场。在这剧场里,怀疑将被悬置,人物将在一部部小说里重生,如同董启章笔下的贝贝变成栩栩、变成恩恩、变成哑 瓷,在《美德》里又变成了维真尼亚。
|访谈|
问=btr
答=董启章
问:《美德》与你此前的长篇在风格和技法上会有哪些不同?
答: 有分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美德》是非常浓缩的,因为要把很多事情、很多场面、很多人物浓缩在一个几万字的空间里面,所以里面有差不多100个名字—— 100个名字对于一个长篇来说不算很多,但在4万字里面密度就很高。所以我也担心可读性(笑),有一段就是名字、名字、名字,把名字排列出来似的,以前我 没有这样写过,正因为要写这样一个前奏,才用了这个方法,不是一个正宗的、写小说的方法。但我也不是从来没有试过——我写过一个短篇《溜冰场上的北野 武》,写的就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在溜冰场边观察里面发生的事和孤独的人们。在《美德》里,有一段是写一个咖啡店,主角是在咖啡店里工作的经理,他观察咖 啡店里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在长篇里面会出现的。这是一个群像,有一大群人的面相在里面。
问:这群像应该来自于你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香港社会的观察。你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感情,在你的写作中香港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 很难简单说。基本上,只能通过小说来表达。因为假如我简单地说一两个词语,说我对香港的感觉怎样,都会是简化的,所以你看我一直都是在写香港,你也可以 说,除了这些人物,香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角。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的每一部分都跟香港是分不开的,所以很自然,写作时我的意识、我的内在和外在 都有这个成分。内在就是:我是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人;外在就是:我长大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个叫“香港”的社会。所以,从内到外都会不自觉地去反射这样一种状态。
问:对于一个生长于此的人,会不会看惯了周遭一切?为什么你能持续保持一种创作的冲动,而且创作了如此大量的作品?
答: 对,为什么没有看惯呢?其实香港人,不单是我,对于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自我意识是很强的,这可能是从我这一代人开始的。为什么一个习惯的地方,会常常在意识 里出现呢,我想这是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很容易相对于其它地方而存在。这种“相对感”是非常强烈的,相对于中国大陆,相对于西方,正是这种“相对感”让 我们看到边界。假设在内地城市,在一个城市长大的人都有一种感情,像上海人对于上海,广州人对于广州;但与香港比,那种边界感就没有那么强烈。当边界划得 很明显时,就会越来越自觉这样的存在。
问:同样写香港,你为什么更多地选择小说这一体裁?
答:虽然大家都在寻找、或者说以某种身份和立场说话,但背后这个身份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本质的东西。历史是什么,也是这样一个建构的东西。而这与小说是很相像的。所以小说里的所谓“虚构”,在一般意义上与现实可以分得很开,说“虚构”的就是假的,但小说里也可以建构历史,我一直觉得历史和小说有相通的地方,用小说这种体裁也更能够看清建构的过程中发生的事。
问:但历史的书写有一种权威性?
答: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相反的。小说没有这种权 威性,小说都是从个人、从比较边缘的角度写出来的。相通之处是,两者都有一种建构。但历史的建构是非常强大的,作为一种权威;但小说的建构是弱小的,通过 个别的写作者,有相似、也有相对。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角度的历史。
问:那么从写作风格的角度看,你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哪里?
答:长句子的话,普鲁斯特的影响很大。从想象力方面来说,受卡尔维诺的影响多一点。香港作家方面,大的影响来自于西西、也斯。西西主要是把香港这个城市作为写作对象这一点,思维方法则受了一些也斯的影响。
问:粤语作为一种非常口语化的语言,与用作写作的语言,在你的小说里通常会很舒服地融合在一起。你如何看待日常的口语与写作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答: 是比较难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差别很大。我也是因为不断这样去写,才慢慢找到一种比较自然、也不太自觉的方式。在香港写作有一点很奇怪,我们写的与我们讲的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书面的、很不自然的事,是一个构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不会去追求写得非常自然,反而会觉得既然是一种构筑, 那就尽量去用不同的方法建构吧。
问:你的好多小说里、包括《美德》里面都有一个小说家,或者说,您的小说经常是meta-fiction,指涉自身。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答: 事实上,我并不是非常关心meta-fiction这个问题,我反而觉得很有需要去探讨的是所谓“真”与“假”的关系。即,在写作这个行为里面,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我写得很真,读者读得时候觉得很真,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写得很假”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本来是在虚构,但是我写一个角色,他是一个作家, 让人觉得与我有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做法是真还是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探讨“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或所有艺术创作行为的背后。这是个本质的问 题,所有艺术都在问这个问题。
问:你认为“真”与“假”的边界在哪里?
答:边界不在版权页上。读者读一个小说,他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慢慢进入这个世界,而且觉得里面的东西很真。并不是因为觉得作者写得很好,所以才很真;而是觉得它与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情真的有关系。这很难说,可能一说出来就不是我本来想说的东西。
问:类似于看电影的时候将自己代入角色?
答: 嗯,但那是暂时的。我在刚写的《体育时期》再版序言里谈及这点,最近香港有个剧团将之改编成舞台剧,再版时也加进了一些关于演出及剧团的文章。写小说,既 不是要把你“骗倒”,也不是要让你觉得“它是假的”,而是要在两者之间——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也不能抗拒,会投入其中,暂时觉得它是真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说的“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说得非常巧妙,所谓暂停我们的“不相信”,但前提就是 “我们是不相信的”,只是我们暂停这个怀疑,暂时去相信它。是先要有这个“不相信”,然后才有“信”。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关系。我要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东 西,我觉得“真”与“假”的边缘状态是非常奇妙的。有读者告诉我,他从十几岁中学时代就开始看我的小说,看得太沉迷了,他觉得变成了我的人物,那我就有点 担心,可能对他会有不良影响。但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真和假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很难说。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