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14-11-03 15: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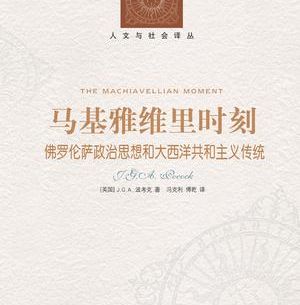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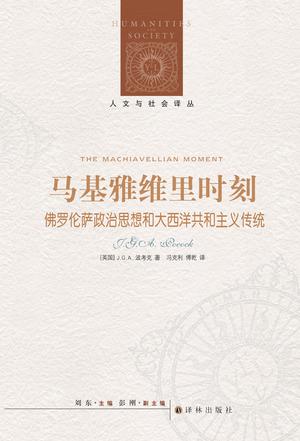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刘东/文 终于熬到《人文与社会译丛》的第一百种了,那些曾把我们给一时唬住的各种西方新奇理论到了“九九归一”的时候,也就算是到了向我们“祛除巫魅”的节点上了。
一
回想起来,在那个封闭的国门刚刚开启、西方还神秘得什么都能有的时候,这些一窝蜂地压将过来的新奇理论,还真是把我们一下子给震住了,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显得似是而非,但又基本上都能够振振有词。当然,为此我也曾经发出过抱怨,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跟风的时髦,就好像人家巴黎刚刚打个喷嚏,加州那边就开始感冒了,而中国研究领域则干脆发起烧来。——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只是在研究中国的人,也就变成了总想要摆弄中国的人:
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
当然平心回想起来,出现这种情况也属于难怪,——只要学术界还希望进行跨越式的对话,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会是他们共同的语言,或曰通分他们的公分母。否则的话,同时拥到一个国际会议上,你所讲的涉及这一个具体领域,我所讲的涉及那一个具体领域,他所讲的又涉及第三个具体领域,彼此之间到底又该如何交谈呢?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理论、以及由理论所表达的立场与倾向了,——那才是大家能够共享的东西,也才是能把大家连接起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框架”之于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来说,正如“数学”与“模型”之于经济学家一样,都属于这个共同体的语言纽带,或曰沟通人们的联络暗语。
然而,这种跨国传染的理论时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吞活剥、强作解人,到底给中国的心智带来了多少麻烦,却构成了笔者多年前很感忧心的主题:
人们很可能只是从宗教的信徒半信半疑地蜕化成了理论的信徒;他们是在明知这种(那种)理论并不完全可靠的情况下,就不经洗礼地谈笑风生地归宗了此一(彼一)门派,而从此之后便只顾贪图口舌和口腹之快了。由此一来,尽管现代社会看似更为多元和丰富,但这个被几条干巴巴理论掏空的生活世界,反有可能比古代文明更为浮薄、浅陋、卑俗和蒙昧,——既然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生存意义的敏感,只会念几句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轻飘飘的套话。
理论确有可能把人越弄越呆,只可惜呆子本人总是缺乏自我意识,还以为只要一朝理论在手,就准会比别人高明和聪明。他们并不认为外来的语式一定要跟原生的语言共同体进行调适,甚至发生微妙的位移,倒觉得只要现实的言说不合外语语法,就准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基本语病。在这种思想的暴力与暴虐下,心智的其他要素统统哑口无言,包括种族经验中最为惨烈的记忆。所以,如果福柯曾把培根的名言发挥成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那么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这种话语就主要表现为理论话语,而且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正是福柯本人的理论话语。
回想起来,其实当我撰写上述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特别讲明这种新奇理论的突然泛滥,又主要是源自一个当代西方的学科史问题,——也就是说,是由“文学”这门西式学科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致。
二
具体而言,由于结构主义与新批评的同时“过气”,且又分别被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所取代,人们在这种西式大学的文学系里,就不再能沿着“作家、作品”的老路,去展开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研究,否则就会被视作“落后”或“过时”。于是,原本安居于这个行当中的从业者们,也就纷纷选择了尽量速成的改行,他们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历史的,而从家门上投奔了历史系,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理论的,而从思路上投奔了哲学系。
只可惜,这些懒人又从哪边都学不太象:君不见,冒称自己属于历史系的,也并无真正史家的体会,只能勉强把所谓文学史(或思想史),也勉强冒充作历史的一种;而冒称自己专攻思想的,也并不能真去恶补什么柏拉图和康德,只好拣一些浅显的文化批评,哪怕只读过几页相关的书评,便去贩卖其立场,或硬套其框架。
这已是多年来所见到的“怪现状”了,本来也以为就会长此以往下去。然而慢慢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所谓“搞理论的人”,已经没办法再这么唬住人了,他们的桂冠也好像是变成荆冠了。甚至,还在自称“专攻理论”的人,其名声若不是带着臭味,也至少会裹来一丝莫名的嫌疑,很容易给人留下拘泥于书本、强词夺理、攻其一点的印象,——哪怕这种往往屡试不爽的印象,有时候也会冤枉哪位无辜者。
回想起来,我这辈子虽还不算很长,但也已是经历过很多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而在这中间,有些转折当然是伴随着急风暴雨,由此才发生了南辕北辙的陡转,并给人留下了深刻乃至惊悸的印象。而另外的一些并不更小的转折,比如对于美学的普遍厌恶,或者对于国学的普遍热衷,却是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不知不觉地就斗转星移了。而这一次理论的祛除巫魅,似乎也是同样如此,——仿佛只是在一觉醒来之后,理论就没有那种眩人耳目的魔力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原本满嘴某种理论,可你一旦沿着他的热衷,把那本书给原原本本地翻译过来,他反倒从此就缄口不谈此书了。——这时候,你才醒悟到他不仅没有看过原文,就连其中文的译本也懒得看,根本就只是凭着道听途说。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出版百种”的节点上,望着如此卷帙浩繁的理论名著,我才更加切身地反思到,原来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种转折的过程。也可以说,也正是因为那些理论当初曾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才发狠要把它们都组织翻译过来,好让它们的本来面貌全都大白于天下!
由此,就要把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一旦把它们全都翻译过来,人们反而对此又不以为意了,那么我该觉得多么失望呀,岂不是很多辛苦都白吃了么?所以,正因为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项“理论事业”,在这个作为节点的转折处,我又必须坚定而明确地提醒,不要因为理论的魔力又被看破,大家就觉得从此就可以看轻和小觑它了。那些迻译进来的理论著作的重要性,仍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嫌过分的,只不过大家眼下读得多了,其代表作也大多都变成中文了,它才不再显得那样神秘和炫惑了。然而又必须警觉:如果仅仅因此就反而轻视了它,那么,我们的仍自简陋而苍白的心智,也就丧失了向上攀越的坚实阶石。
的确不错,在通过理论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中,总难免要出现一些想来取巧的南郭先生,而他们一时间也是占足了非分的便宜。——这是因为,尽管理论总是要结合实际的,但在中间,却只是有些人才是真正地结合了,而另外的一些投机分子们,则只是煞有介事地装作自己也“结合”了。
三
无论如何,到了如此人头攒动、彼此说不了几句话的国际会议上,仅凭在理论倾向上的那一点点交叉或叠合,人们一下子也很难一眼就看穿,其间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呼应处,而且存在着实践上的正相反。
正如从“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代代亚洲学生中,既走出了邓小平,也走出了胡志明,还走出了波尔布特。按说,他们所学到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可以算是来自同一个根源,从而构成了某种“理论国际”的各国支部;然而,他们到底分别把各自的国家弄得如何,那就不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虽然在一方面,那些可恨又可悲的南郭先生,的确是让人痛心地糟蹋了理论的声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糟蹋,就把婴儿和洗澡水给一起倒掉。
正因为这样,理论朝向我们的“祛除巫魅”,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关心理论本身了,否则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在思想上也就太不长进了,因为只要它们是在讨论着至深的人生问题,我们就只能努力去“越过”这些理论,而不是贪图省事地“绕过”它们。
所以恰恰相反,尽管在这个节点上,理论著作已经没那么富有煽动性了,可转念想来,这反倒正是更仔细地通读它们的时机。这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阅读心理才会更加冷静,不会刚看到几句似是而非的巧辩,就被它炫惑得根本“找不到北”了。
所以,理论对于我们的“祛除巫魅”,也无非意味着通过积累而达到了突破,使得它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开始对我们变得历历在目、脉络清晰、优劣分明了。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无惊喜地发现,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拱顶石之一,西方的学术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辉煌地崭露给我们了!
此外,到了这个向前发展的节点上,虽说已化作现代汉语的理论书库,仍然嫌不够完备齐整,还需要我们持续的刻苦努力,可它也总算是“疏而不漏”了吧?可资参考的思想支点也已够多了吧?
而这样一来,无论哪位也不至于再像以往那样,最先读到了这书山书海中的哪一本,便鲁莽地倾向于此生都笃信这一本,甚至执拗地要为它去抛头洒血,——那才是最不擅于读书的书呆子呢,或者说,那样做只不过意味着,他是在把读书思考的可贵自由,糟蹋成了充满偶然的宿命。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一方面应当领会到,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分量,无论如何都应能摆得更正一些了,——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再能只用几句煽动性的理论,就让他的读者或听众为之膜拜,甚至为之如痴如醉;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了,这类的辞令就显得太没信息量了。
尤其是,在学术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今,如果你在跟国际同行面对面时,还只是毫无新意地去对人家讲,人家的学术界都出现过哪些理论,而你又对那理论何等五体投地,那也实在太缺乏原创性和反省精神了,只会让人觉得你是个不足道的可怜虫。
可另一方面,不能再一味地让理论来炫惑我们,却也并不自动地等于,由此就可以让那些理论上的门外汉,不再以自己的无知为耻了,——甚至能让他们不仅可以安然地“因陋就简”下去,还能反过来把“懂得理论”看成别人所犯的一种错误。所以,还是要公正而全面地看到,那些只会钻理论牛角尖的,和那些只愿拘泥狭隘经验的,全都显出了某种偏狭与简陋。
此外,还是要带着一点耻感来记取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评论,他曾经一语中的地把我们的简陋给说破: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说穿了就是并没有自己的特征,因为所有被人们舞弄的东西,无论它们表面上多么对立,都是从西方特别是从欧洲进口的,都属于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欧洲式总结。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要怀着急迫感地看到,由此所造成的种种文化被动,能否被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所顺利克服,其关键还在于能否完成理论的创新,——否则,我们终究还是只能祭起人家的理论总结,来扼杀自家经验的丰富与独特性,并让那些被污损的经验朝我们大声地发出抗议。
更进一步来讲,如果就人类的思维方式本身而言,它毕竟也要靠理论的形态来开拓自己:“理论虽说一经产生便为心智带来了无穷的纠葛与缠绕,其初始动机反而在于心智的自我整理与廓清。——心智若不乞助于澄明自身建构的理论模型,便不能在分化中得到预期的发育;而理论若没有相应的解释功能,也就无法转过来澄明心智,哪怕后来发现纷纭的物象中并无此类预设的齐一性。”
于是无论如何,一种理论既然能被称为理论,就总要表现为抽象概括的形式,由此也就总要朝向未知的领域,发出自己固有的辐射作用。而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理论一经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必然要进入陌生的领域,以来验证自己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
四
毕竟无论古往还是今来,都并不存在只适用于某一特例的理论,正如并不存在只能解释“这一只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的引力定律。顺势而论,如果我们能够再看得透彻些,则实际上,无论是“文明对话”还是“文明冲突”,都是它们的作为其价值内核的不同理论,在进行相互的对话、辩难与竞争。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种国际格局中,如果撇开爆发战争的短暂极端情况,则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力,主要会表现为进行商战的能力,那么,文明之间的冲突振荡过程,说到底也无非是“理论与理论”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辛苦译出的这套丛书,不管属于有意还是无意地,总还是显出了西方文明的强势或优势,那也只能归功于那边学者的自身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对于误用和滥用西方理论的苦痛悔恨,和对于表现为文化强势的西方理论的种种抱怨,也就应当转变为对于自家“理论缺失”的深切自责。谁叫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呢?要是你更善于在这方面进行富含想象力的创新,那么,不就轮到别人的经验世界会被你强行闯入,不就轮到由别人来质疑你的理论是否能普遍适用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痛切和急切地看到,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迟滞与落后,才真正属于文化造血机制上的、最为要命的落后。就此而论,既然仅只我们这一套丛书,都已被出版到“第一百种”了,那么,如果放开胆子来想象一下,这也许就该是从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节点了?无论如何,现在离我在丛书《总序》中提出的目标,总应当是越来越逼近了:
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而这种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由于近代以来的巨大外部压强,也由于学术文化的固有内在特性,又终要落实为理论层面上的反馈式对话。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逐渐具备了这种可能,去基于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也基于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还基于它自身的脉络与长短,而向那些外来的理论制造者们,明确地指出那些理论的误用与滥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或许是始料未及的恶果。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尝试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也就是说,就算它们和西方的理论一样,也要经历在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然而由于它原本就脱生于中国的经验中,所以至少当它们再返回这种经验时,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并遇到更少足以证伪的反例。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能够生出此念,则中国文化的自身主动性,也就势必要被调动起来,从而,业已失语很久的本土传统,也就势必要随之振作起来,信心满满地加入到国际学术的大潮中去。
而由此一来,也就势必提升和激活了我们的传统本身,使它不再被只当作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得以从价值理性和普世意义上,向世界重申自己由来已久和言之成理的人生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只要能在这方面成为有心之人,我们眼下所享有的这个历史瞬间,就应会在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转变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化上升期。
回想起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辉煌先秦时代,也无非就是有一批勇敢的思想者们,在各出机杼地进行着理论的创新,——君不见,直到眼下在哈佛大学那边,都还有人利用他们当年所创造的理论,来试着回答西方自身的道德判断问题,并且还让哈佛的广大学子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我们如果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则中华民族也就从价值理性的深处,开始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而不再只属于理论上的进口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生所钟爱的学术事业,跟我们此身所属的国家之地位,才算是合拍、交融和同步起来了。
同样地,如果我们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那么整个世界的文化——即使是号称“先进”的西方文化——也都将为此而大大地受益,而不再只是去当个自恋的水仙花,以为天下所有的美丽都长在自家的脸上。
当然,正像我早前曾经说过的,理论本身还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无论生活在哪个文明共同体中,我们作为全人类的一个分子,其自身的灵魂能否最终得救,都端赖能否借助于理论的滋养,而获得广大、高明而圆融的心智。
而弥足庆幸的是,尽管为了达到这套丛书的现有规模,自己也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苦熬,并且肯定是耗去了不少的年华,不过,如今注目一下镜中的自己,似乎也并未因此而耗得太老,——至少还没有耗到韩愈所谓“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所以,只要还能正常地天假以年,也许我本人也许就还来得及,再发动一次朝向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此外,这套厚重得几乎无出其右的丛书本身,也正站在自己身后的整排书架上,在为自己的年华毕竟没有被虚度,而留下了终归是磨灭不去的、让自己生出慰藉的印记。至少,这些图书还可以这么来安慰我:即使你自己未能在创新方面一蹴而就,也总算给学术界的后续梯队,留下了继续在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一排排阶石。无论如何,这在自己大体上充满坎坷的生命旅途中,也聊可充作一种不幸中的幸运、甚至不幸中的“侥幸”了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