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14-11-05 15: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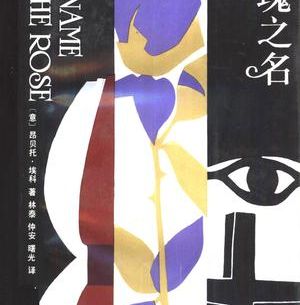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瓦当/文 关于艾柯,我们能谈论什么?符号学家、历史(中世纪)学家、博物学家、五万册图书(其中不乏各种珍本)的收藏者、超级畅销小说《玫瑰之名》、《波多里诺》的作者……对于这个当代达·芬奇式的人物所涉猎的每个领域,我们绝大多数读者都所知甚少,更无从置喙,但这丝毫不妨碍读者被他书里的那个广袤的未知世界深深吸引。因为书除了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之外,还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本身作为一种奇观存在,艾柯的写作充分证明了书所具有的这种奇观性质。
借用艾柯对古登堡圣经收藏者的评论——“拥有古登堡圣经就等于从未拥有”,个人以为,阅读艾柯的一个最多快好省的途径莫过于将他炫智般的博学视为虚构。这不仅因为以我们有限的知识对他书中虚实杂糅的内容无从辨伪,更因为艾柯本身就是一个伪书爱好者和伪书作者。根据《巴黎评论》记者Lila Azam Zanganeh的描述,在艾柯的书房中,既有托勒密的科学论著、卡尔维诺的小说、关于索绪尔与乔伊斯的评论研究,又有几书架中世纪历史书籍与神秘晦涩的手稿。艾柯痴迷于收集那些自己不相信的主题的书籍,比如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炼金术、魔法、虚构的语言,“符号学、奇趣、空想、魔幻、圣灵的藏书”。艾柯所热衷的这些书籍,类似于中国的民间宗教宝卷,从书籍的生成角度来看,多属于伪书之列。 他坦言:“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爱让我着迷”,“我喜欢那些说谎的书籍,虽然它们并不是故意说谎。我有托勒密的书,但没有伽利略的,因为伽利略所说的是真理。我更喜欢疯人的科学。”这好比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却痴迷于民科,这种“怪癖”透露出艾柯独特的知识观念。
对伪书的狂热爱好最终会演变成抑制不住的创作伪书的冲动,很多时候,艾柯就像自己笔下的波多里诺一样“捏造文献,构想乌托邦,构建世界的假想格局”。《德意志民族的巨大排便量》、《想象的瀑布、写作的洪流、文学呕吐、百科全书大出血、魔鬼中的魔鬼》,还有1500部文学狂人作品的《狂人文学史》、安德里厄1869年的一部关于牙签盒的缺陷的作品、毕宿五星某大学教授为火星学者写的一部关于地球灭绝研究的专著而写的书评……单他笔下这些“书名”和提要,足以让读者瞠目结舌。不同于中国古代伪书“专造一书而题为古人所著,以张其学(梁启超语)”的目的,这纯粹是为书而书的趣味使然。
不难看出,艾柯有两种基本的写作策略,一是类文本,即附着于一部真实或虚构文本上的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混成模仿体”。比如《一个陌生人的杰作》针对一首空洞无聊的民谣写下了两百页评论,让人不由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杰作《微暗的火》。二是元小说,即写作关于小说的小说,大量使用互文、戏拟、读者与作者之间对话等手法,最终创造“一种完全开放的文本,让读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无限的再创作。”这两种写作策略错综使用,构成异常复杂的超级文本时空。当然,这些并不是艾柯的首创,在他热爱的博尔赫斯、乔伊斯以及他的好友卡尔维诺那里都已有完美的表现。
毫无疑问,艾柯的写作是智性的,而非情感性的,这使他的写作奇观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客观来讲,这也造成他与上述文学大师之间的差距。也许,艾柯在意的并不是文学,而是书之为书这一行为。博尔赫斯曾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即“显微镜、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伸、犁和剑是手臂的延伸,而书籍是记忆和想像的延伸。”艾柯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他将记忆分为动物记忆、矿物记忆(如碑石、建筑、电脑)和以书为代表的植物记忆三种。而书的优胜之处在于,除了承载记忆,还具有物的属性,这使得爱书与藏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恋物的色彩。艾柯进而细心地区分了藏书癖与爱书癖的区别——前者多有主题,且侧重收藏的整体性,而后者泛爱,希望收藏永远没有完结。在一个电子书咄咄逼人的时代,艾柯毫不掩饰对纸质书的拳拳之情,几乎是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鲸鱼、地中海僧海豹和马西干棕熊,还包括书籍。”
在艾柯的笔下,书不仅仅是承载记忆之物,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他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一本电子书梦想成为一本纸书的焦灼独白,而对于纸质书而言,一本书只能活在一种文本里,未尝不是又一种痛苦。在一篇名为《书的未来》的演讲中,艾柯预言纸质书永远不会消失,但在另一篇小说(《碎布瘟疫》)里,他又想象着2080年一场碎布瘟疫袭击了所有文明世界图书馆,使无数珍本都化为白色尘埃。对于爱书者来说,无论何时,书的生死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