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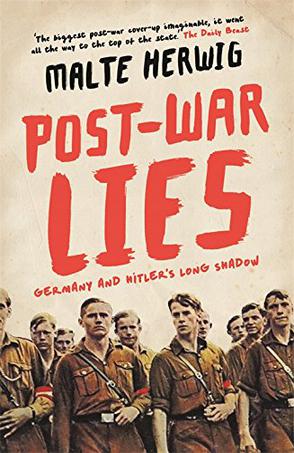
吕品/文
25年前,一座分隔东西柏林的高墙倒下了。在阅读许多纪念柏林墙倒下的文章时,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德国电影系列《故土》(Heimat)。《故土》被称为德国“普通人的历史”,以莱茵地区农村一户人家及其后代为主角,共有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跨越了一战结束到二战战败之间的历史,第二个系列以1960年代的慕尼黑为背景,第三个系列的开头正是1989年柏林墙上的关卡被打开的那一个晚上,男主角走在街上,一个满眼泪花的陌生中年男人忽然和他拥抱了一下,走开时还在喃喃自语:“从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今天”,那一晚分别多年的男女主角偶然相遇,决定重新走到一起,俩人一起见证了德国统一之后的社会经济变迁。《故土》以柏林墙倒下作为第三系列的开始,因为那标志着一个“新”的德国的开始。如果说德国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许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25年之前,当时的东西德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上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不仅经历了一场政治架构的重组、经济的整合,同时作为国家重建的一部分,德国人还必须再次构建一个可认同的国家身份,这一过程所依赖的,是德国人共同拥有的文化历史,也就是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记忆。
共同的“记忆”在构建国家身份中的关键意义,正是《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Germany: Memories of a Na-tion)一书的主题。该书的作者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尔(Neil MacGregor),这本来是他为BBC电台4台主持的一个系列广播节目,分30集,每集15分钟,选择一个事物作为德国国家记忆的象征,围绕这个事物讲述德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以及这个片断对德国、德国人的意义。这个节目在今年下半年播出,同时在大英博物馆举行同名的专题展览,展出这个系列中提到的物品。
这个系列有点像麦克格雷戈尔在2010年主持的通过100个物件讲述世界历史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A History of World in 100 Ob-jects,繁体字译本为《看得到的世界史》),不过在《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中,麦克格雷戈尔在选择象征物时显得更加自由。在这个30集的系列节目中,他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历史物件,如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同时被德国和法国人认为是自己第一个皇帝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皇冠、16世纪德国画家霍尔拜因(Hans Holbein)在伦敦为北欧商业联盟“汉莎联盟”(Hanseaitc League)中一位富有的商人所画的肖像等等。如果最近你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你会在其环形中庭前看到一辆1950年代出产的大众牌“甲壳虫”轿车。但是在这个系列的开头,麦克格雷戈尔选择的却是一座建筑:柏林的勃兰登堡,它不仅见证了许多德国历史,还曾是柏林墙一部分。在该系列节目中,他还到过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巴伐利亚州的瓦尔哈拉神殿(Walhalla)、二战期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等地,最后重回柏林,来到经英国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改造后重新投入使用的德国议会大厦。
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来讲述一个国家的历史,当然无法像编年史那样详尽,但是却能够突出这些象征物的重要意义。这种方法对德国历史尤其适合,因为“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1871年才第一次出现,在这之前是分散的大公国和城邦国家,而德国的边境线也一直是游移的。在这个系列中,麦克格雷戈尔走到的地方,一些在德国国家身份认同中占重要地位的城市,已经不是德国的领土。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为德国人带来了共同的文化身份,但是诗人大为赞叹的斯特拉斯堡,现在却是一座典型的法国城市;布拉格曾是德语文化的重镇,但是在卡夫卡之后已完全切断了与德国的关联;曾经是普鲁士王座所在地、反抗拿破仑的最后基地、德国哲学家康德故乡的哥尼斯堡 (K·nigsberg)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占据,变成了苏联领土,更名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能够让当代的德国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是文化的纽带:歌德、康德、马丁路德、丢勒、格林兄弟、卡夫卡,以及对历史的记忆:铁十字架、香肠、啤酒、集中营、二战后的废墟。
在麦克格雷戈尔选择的物件中,许多都体现出德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建设和创造的民族,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两个例子。第一个是15世纪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古登堡的活字技术是否来源于中国尚有争议,但是他的贡献还在于发明了用金属铸字的办法,使得活字可以大量生产,便于压印,这和德国的金属制造业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中,麦克格雷戈尔还选择了普鲁士王国颁发的铁十字架、铁质首饰以及把德国开国元勋俾斯麦塑造成一个铁匠的雕塑作为象征性物件。第二个例子是18世纪德国的梅森(Meissen)瓷器。中国瓷器流入欧洲时,极其珍贵,被称为“白色金子”,1717年萨克森(Saxony)君主曾用600名骑兵从普鲁士国王那里换来150件中国瓷器。在这之后,萨克森的技师通过反复实验,用当地材料找到了配方和烧制办法。11年之后,普鲁士王后收到一批来自萨克森君主的瓷器,和中国的一样漂亮,却是萨克森本地产品。在以后的两百多年中,梅森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还开发了不少新品。麦克格雷戈尔感叹道:“古登堡和梅森瓷器都说明德国人不仅能模仿、还能超越中国人的成就。”
说到“记忆”,对德国人来说自然离不开对纳粹德国时期的记忆。德国人大概是对这段历史反省最深刻的民族,但其过程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直接。盟军占领德国之后,曾对德国进行了历时约3年的“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过程,犯有战争罪行或曾是党卫军盖世太保成员的,当然要受清算,在纳粹德国政府内担任过公职或曾是纳粹党(NSDAP)党员的就不能进入政府,但是很快盟军当局就发现如果要彻底地“去纳粹化”,那几乎就剩不下几个人来重建德国了,这在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写1945年历史的《战后零年》(Year Ze-ro)一书中有详细描述。那时的德国人大概希望尽快忘记这段历史,埋头重建家园。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是和以后德国的重建同时进行的,负罪感成为德国的民族心理。其中最为难得的,是下一代对父辈、祖父辈在纳粹德国罪行中应付责任的追究。
去年在德国出版的《防空辅助员》(Die Flakhelfer)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今年译为英文,以《战后谎言》(Post-War Lies)为标题出版。该书作者、德国记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研究的是特定的一代人:他们在二战结束时年龄尚小免于接受“去纳粹化”,但作为十几岁的少年,已经能够理解纳粹罪行,这些人在二战后期被拉入担任“防空辅助员”,战后成为德国重建的中坚。他想分析的是这些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作了反省,是否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
赫维希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二战后期被盟军缴获的纳粹德国政府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战后大都被移存到一个专门建立的名为“柏林文件中心”的机构中,其中包括超过1千万纳粹党员的登记卡。柏林文件中心由美国人负责看管,他们对所有文件进行了翻拍和整理。这个中心的经费由联邦德国政府支出,但是据赫维希指出,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联邦德国一直不愿意从美国人手中把纳粹党员登记卡接收过来,美国人也十分配合,不仅对文件内容严格保密,甚至还会应德国政府的要求,如果发现纳粹党员登记卡中出现政府高官、高级政客的名字,就马上把这些资料抽起,锁进柏林文件中心主任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德国议会和舆论的压力下,德国政府才不得不接管了所有文件并接受公众查询。
在这之后,因为开放公众查询而透露出来的信息在德国社会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震动。因为人们发现,在“防空辅助员”这一代人中,一些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竟然曾是纳粹党员。当然这些人在二战结束前夕时也不过十七八岁,刚刚可以加入纳粹党,不可能是逃避清算的战争罪犯,但是人们从来都认为这些人历史清白,有些人还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过公开和认真的反思,颇有社会影响,难道这些都是该书书名所指的“谎言”?
这些人中有些是自己透露这段历史的,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2006年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参加过党卫军,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也促成了赫维希创作《战后谎言》一书。另一些人则在证据面前依然拒不承认,如著名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 坚称自己毫不知情,肯定是未经本人同意而被“成批”加入纳粹党的。赫维希指出根据各方研究,当时不存在集体加入纳粹党的现象,借口“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最让他担忧的是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公众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另一方面却又为了避免政治丑闻、维护社会安定而对这段历史进行长期隐瞒。
赫维希在《战后谎言》中强调,他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责任,或是抓漏网之鱼,而是为了引发讨论,如何更好地面对过去,保证纳粹德国的罪行永不重演。“防空辅助员”这一代在二战期间二十岁不到,在纳粹的宣传鼓动和为国献身的热情驱使下,自愿加入纳粹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后他们或许刻意压抑甚至忘却了这段记忆,或许自我反省、完成了“自我去纳粹化”的过程。作为他们的下一代,有义务去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用当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避免简单地把纳粹德国的兴起归咎于当时“邪恶的一代”。
德国人追究自己历史上的丑恶与罪恶时的深入,着实令人感叹,战后一代又一代德国人在历史反思上进行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这个民族的细致与执着。也许正因为德国是一个凭借“记忆”建立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家,才会不顾痛苦与羞耻,用这样冷峻和认真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历史。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