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敏飞/文 当代史家中,我读马勇最多,或断代史,或者人物传记,例如他的《清亡启示录》《帝国设计师董仲舒》等等。他最新出版的《中国儒家三千年》属通史,浩浩瀚瀚50余万言一口气读下来,第一印象是令我想起自己一次新疆之旅。
新疆巴音布鲁特,那草原辽阔无垠,直接天云。登临稍高处望去,一条大河从天而来,十八湾尽收眼底。我到那里旅游时,曾在那栈道上伫立凝望了许久。我困惑:家乡因为天为山欺而水求石放不难理解,这平平坦坦的大草原,何以“水求草放”?忽然两眼一亮:读史当如此!
读史当读通史,上下数千年全览!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代表中国历史,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代表他所在的王朝,如同任何一个季节都不能代表全年。如果只读某一个王朝、某一位帝王的历史,无异于蹲在某个小湾道里探望整条河流。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E·芬纳在他巨著《统治史》一书中提醒说:“唐帝国的寿命长达300年,其统治存在一个明显问题:王朝末期的统治体系和初期是不一样的。因此,选取某个特定年代或统治时期来代表整个唐王朝的统治无异会误导读者。”前唐、中唐与晚唐的差异多大啊!以盛唐断言全唐多辉煌,或者以残唐断言全唐多乱糟,无异于盲人摸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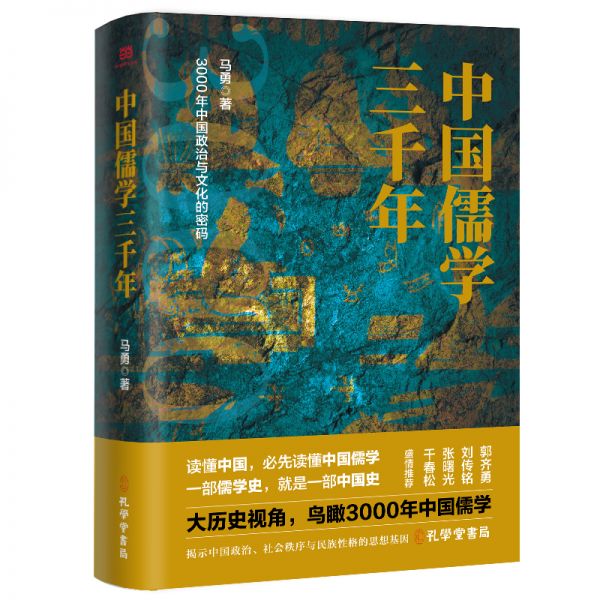
中国儒学三千年
作者: 马勇
出版社: 孔学堂书局
副标题: 3000年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密码
出版时间: 2021-10-11
马勇在此著序言及后记中坦言:“学界需要一部系统、简洁、全面的儒学史,而儒学史的写作需要一种逻辑自洽的个性化表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本书的主旨是希望从大历史的视角,给三千年的儒学发展史做一个鸟瞰式的描述,为读者诸君呈现一个宏观景象。”其实,不仅对于学界,对于我等大众读者也如此,对于儒学这样的历史尤其应当如此。只有在这样的儒学通史当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儒学曾经有辉煌,也有厄难,还可以进而理解张东荪曾描述的历史怪象:“中国历史上的尊孔者几乎从来都是利用孔子。他们利用孔子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曾被人们发现,于是一概记在孔子的帐上。于是推崇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痛恨孔子的人便愈痛恨孔子。” 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沉痛的教训。
想当年,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有着“法国的孔子”之誉的伏尔泰甚至公开呼吁“全盘华化”。然而,他们很快发现“狡猾的耶稣会士”带回的信息“褒奖过度了”,乾隆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宽容的典范”,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禁止‘危险思想’为名的)文献毁坏者之一”,“孔子和中国政府的美德就等于是耶稣会士的发明,是出于宣传目的的信口开河”。这样一来,耶稣会士教团失去了各方面的信任,被教皇取缔。更糟的后果是“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世界从未再次对中国感兴趣,也从未对这个国家兴起过那么高的评价”。这么说,中国“躺枪”了,——落到另一个极端,误以为董仲舒、朱熹等后儒的思想就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再一个极端是把儒家贬得一塌糊涂,连小学生也敢大批判孔子。所以,推出好一部儒学通史,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件大好事。
我对儒学没有专门研究,只是大致了解儒学的历史:周公制礼作乐为儒学1.0版,孔子为2.0版,董仲舒为3.0版,朱熹为4.0版。那么,如何从周公到孔子?又如何从孔子到董仲舒?这就不大了解,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孔子、董仲舒等人的历史意义。
从周公到孔子、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历史,由于史实缺乏,往往付之阙如。程志华《中国儒学史》从孔子开始,直接跳到孟子,接着直到《大学》《中庸》《易传》,再是荀子,然后就到董仲舒了。马勇则不然,迎难而上。在他看来,史实缺乏或许如无垠的天空,可以大展想象的双翼。
众所周知,史实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相。尼采甚至对历史的真相绝望,不无刻薄地称历史学家“是一群宦臣,而对宦臣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是女子本身,永远无法接近。而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离不开适当的想象。司马迁距那场鸿门宴大几十年,何以写出那么生动的言行细节?
马勇善于惴磨历史人物的心理。我最初是读他的《清亡启示录》,在谈到两路出国考察人马回到北京汇报建议时评述:“不要说中国人保守,也不要说中国的统治者保守……君主立宪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我觉得这种想象即心理解析十分到位。马勇也善于描写历史人物,例如他写董仲舒:“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虽然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马勇描述的群体或具体历史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儒家三千年》一书中,马勇保持了他这种写作风格,以人系事,描写了古今众多学者,通过他们的思想历程与成果,展示儒家千古绵延之变。对于从周公到孔子、从孔子到董仲舒等历史阶段的空白或者说漏洞,也由人物进行了适当的填补。马勇描述:
西周建立之初,殷商遗民中的儒者万念俱灰,人心惶惶。然而为时不久,却又因周公制礼作乐而带来了新的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这批儒者逐渐认同了周朝的统治者,不仅其人逐渐跻身西周贵族阶层的行列……逐渐摆脱亡国的阴影和恐惧,逐渐对周朝统治者产生了某些认同。
这一段生动的群体心理描写,显然是想象的产物。又如写具体人物:
当孔子明白在现实政治的道路上已不可能再有所作为的时候,他虽然一度表现为失望和消沉,但很快就寻求到新的人生的支撑点……稍经犹豫与困惑,孔子就毅然决定……
可贵在于这决不是凭空想象。马勇毕竟是史学专家,而不是作家。恕我直言,像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虽然烩炙人口,可是稍多读几篇,心里不免暗暗生疑:是否想象过度?
马勇的历史想象,或许更应该严谨些称之为推理。有段常见的引文:周公于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马勇注意到这里一个细节:“在短短一年或一年稍多的时间里,如果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工作班子协助周公,仅凭他个人的智慧,何以能够在鉴于殷商教训的基础上,完成一代制度的规范和制定?”由此深思,加之有旁证殷商遗民“确曾在亡国之后被分门别类地安排做自己熟悉的工作”,才断言“周公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一定组织过一个相当规模的工作班子”。
子贡为孔子接班人的地位似乎基本确定,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突然力推有若,简直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为什么呢?马勇分析,一方面是子贡性格“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似乎在某些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另一方面似乎因为有若“貌似圣人”,此外还似乎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连串的“似乎”,似乎可以想见马勇在写作这些文字之时手指头在电脑键盘上举棋不定的样子。
马勇注意到,东晋学者荀崧揭示孔子著《春秋》及三传发生的大致脉络之时,“内中虽然仍有不少猜测之词,但毕竟去古未远,他的这些猜测应该有自己的理据”。是的,历史的想象应该有自己的理据。这理据就是马勇所谓“逻辑自洽的个性化表述”吧?理据一充分,他的语气就完全不一样:“孔门弟子在孔子死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更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变成一连串“必然”。可见马勇的历史想象十分节制,如同纵马奔腾而不脱缰。
写一部系统、简洁、全面的儒学通史十分不易,而要写得生动好读那就二十分不易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