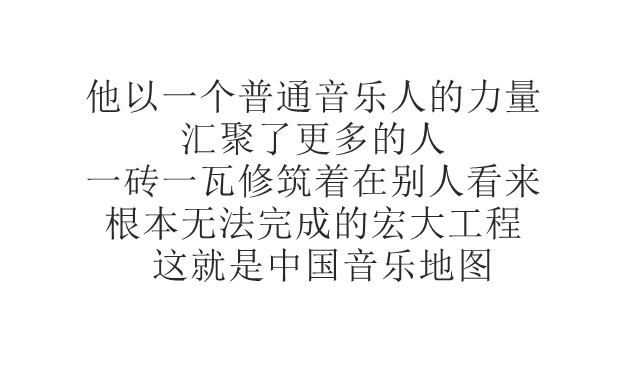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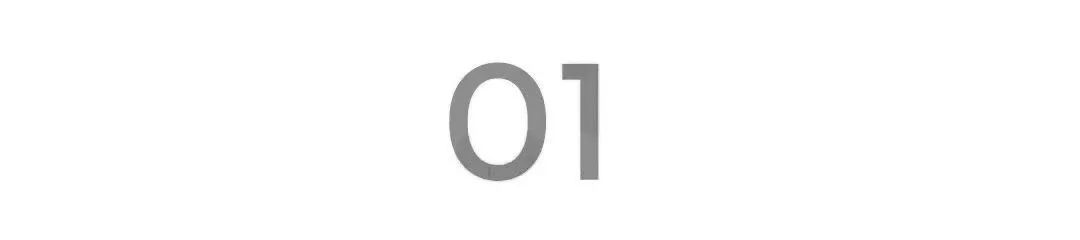
“告诉你一个小目标:我想让瑞鸣这些音乐放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全世界听见50亿次,触达200个国家和地区。”
一次聊天,叶云川这样说。秋天已经开始,仿佛全世界都在落叶,我听到某种飞虫正在振动自己的翅膀。
叶云川,著名音乐制作人。2003 年在北京创立音乐品牌“瑞鸣音乐”。一个实验者,一些人眼里的不靠谱的破坏者。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那种有着很明显的“僧侣性”的人——作为文化保存者,他会最大限度的与尘世拉开距离。他把传统的尽可能录入囊中,同时,他也努力做着更多有想象力的音乐。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代音乐人中的一个孤本,一块独立于时代之外的飞地。
近 20 年来,他创作制作了二千五百首作品,作品获得约一百八十个奖项及提名,包括美国独立音乐大奖、全球音乐奖、中国金唱片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等等,这是一下子难以列尽的荣耀。
“我制作的音乐看似凌乱,招法百样,却离不开民族文化、世界音乐八个字句。野路子有野路子的内在逻辑、武功秘籍。”他笑道,“我自仗剑走天涯,那管你定的规矩,饿死方罢。”
听很多人说过,他其实有一个很高的目标,那就是格莱美。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格莱美注册有投票权的中国会员,常常自费把作品邮寄到美国参加评选。2020 年,因为疫情原因,国际航线紧张,他给格莱美的评选会员们寄唱片的运费就花了两万多,“你都不知道费了多大力。”
自 2001 年谭盾的《卧虎藏龙》获得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专辑奖之后,中国音乐拉近了与格莱美的距离。但遗憾的是,这非常有限,特别在中国本土。作为致力用世界音乐语言来表达中国音乐的本土制作人,他一直希望这一局面可以改变,让世界听见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让中国音乐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2020,这一次又失败了。但他会“屡败屡战”。这次见面,我本想追问有关格莱美的事情,他却把自己的另一个“小目标”说了出来。这个“小目标”,一下子让我显得特别功利起来。

“我要的比别人多。”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也不会隐藏自己的失落,“坦白地说,这么多年来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的,”“我的幸福感和失落永远共存,只不过美好远大过沮丧,总归内心的满足要更多一些。”
其实,多年来他在无边世界旅行,“去大海里游泳”,刻意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看似为自己,其实更是在为中国音乐发声。
有一次,他带着 1000 张CD到德国参加世界音响音乐大展,英文不好,就在平板电脑写着,“我是中国音乐人,请您听我们的音乐”,两天时间唱片全部送完。在美国做展览,美国人听了他制作的音乐,看到他的唱片,就觉得是日本品牌。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亚洲品质最好就是日本,最潮就是韩国,而中国的东西,便宜就好。这个东方的堂吉诃德幻想改变这种认知。
改变的前提,是要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新的贡献。“而我,除了音乐,没有别的可以奉献。”
他的微信签名是“一个人的旅行”。但他以一个普通音乐人的力量,汇聚了更多的人,一砖一瓦修筑着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法完成的宏大工程——这就是“中国音乐地图”。在一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哪吒,三头六臂。目前,这个历时三年,囊括近40个民族,213种传统乐器,采录超580位民间音乐人,1056首曲目,1000个音乐视频,近30万字采集文字资料的项目已经收官。
有一刹那,他全身仿佛轻了三十斤。但是随即,另一个更大的心愿便笼罩了他:把这些东西存留下来,但还要努力传播到更多人那里去,传播到世界去。他说,“传播就是保存的最好方式”。如果把音乐也像佛教那样分为大乘与小乘,叶云川就是典型的“大乘音乐人”。这也是当代最为需要的音乐人。
他希望用一个完整的系统回答西方人常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音乐”。这些音乐世世代代相传,如今传到我们手里,却正以没有流量的名义遭到淘汰,“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民族到底是贡献还是犯下过错?”

从成功学的角度看,他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创业者”。他把自己的许多做法叫做“肉包子计划”,所谓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2005 年做音乐缺钱的时候,他卖了位于北京三环边的一套房子,然后租房住了 10 年,保证自己总有钱做音乐。“事实证明,财商极低智商不在线。”
“还是要跟木匠一样不断做东西。”在他心中,木匠这个角色,要比所谓“工匠”更有生命感。“我做的事情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没有用的东西远比有用的更加珍贵和有力量。”
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置装费”平均一年也就一千元。常年牛仔裤帽衫,夏天就牛仔裤、白T恤,这是他永远的标配。为人随和,弹性很大,似乎把他放到任何一个状态,他都能比较容易去适应。但有朋友说,这只是“表象”。他实际上偏执、苛刻、挑剔,不通人情世故。他也承认,“双子座嘛,实际上很分裂很顽固的。”
他总结出一个最能体现自己特征的字:熬。像煎中草药一样,他用慢火“熬”着自己的 “小目标”。屡屡失败的格莱美是一个。“中国音乐地图”更是一个,“找出中国音乐与世界文化融合的道路”,这是他为自己的过去颁发的另一种格莱美。
而让瑞鸣音乐——传统中国音乐——被全世界听见50亿次,100亿次,及至无数人次,则是他现在的目标。
“翻过一座山,见另一座山。”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彼岸。”

叶云川 摄影:刘丽杰

“我们唯一能做的东西,就是去留存一些必然消失的东西”
搜神记:因为疫情,这两年世界改变了很多。这期间你是怎么过的?
叶云川:我 2019 年和 2020 年是特别极端的两年。2019 年一年我坐飞机差不多有几十次,有将近 300 天不在北京,去了全国 14 个省,还去美国、日本录音,跨度极大。因为我在做一个项目叫“中国音乐地图”,疯狂地、紧锣密鼓地跑完了 2019 年。2020 年春节期间就去了越南西贡,然后回到北京,疫情就爆发了。等于 2020 年整个全年,全部埋头做我 2019 年的这些音乐的后期。因为 2019 年我的体量很大,涉及 30 多个民族、580 个民间音乐人,乐器都用了 213 种。这就是中国音乐地图,跨度很大,是一个别人叫做原生态我却称之为根源、母语的音乐项目。
搜神记: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叶云川:对于世界来讲,我就回答西方人常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音乐?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有点像哲学性的问题,就像什么是中国豆腐一样,没有办法去回答。因为我们有 500 种豆腐,怎么去讲?日本豆腐很简单,人说我们就是日本豆腐,中国人不服,我们有客家酿豆腐、麻婆豆腐等等几百种,怎么讲?所以我想用一个系统去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音乐。我用音乐地图的概念来回答世界,这是中国音乐,你可以从省、民族、地区、风格当中去解构它。
但我更想表达一个东西,我总结了一句slogan,“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从母语中寻找生命的缘起”。我们的故乡都被拆没了,你等于是用今天所谓现代化铲平所有人的记忆。不仅是我的家乡,是近乎所有人的,被铲平了、铺上水泥地以后,其实是所有东西都消失了,沉积千年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什么东西是可以保留下来的?音乐一定是其中之一。因为音乐很难篡改。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比如你这个图片,你这种文字,都可以篡改,可以面目全非。所以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音乐很难,因为音乐是内心流动、流淌的东西,你只要敢改一个音符,它马上就显得特别不和谐、不自然,一看就是改过的。所以它最能真实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我录的《西安鼓乐》,算是这次录音有传承记载距今时间最长的,最起码是 1300 年,据说是安史之乱从宫廷逃出的乐师传下来的,保存到现在几乎是原貌的状态,且不说更多的东西。当然有时候有些音乐无法记载不好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当 1000 多年前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端庄、雍容的气质一出来,你一听,哇,这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你知道那些演奏者是什么人?他们只是西安郊区的村民,但是他们的笙管笛、鼓一出来,一听就是宫廷音乐,而且是大唐的那种华丽的雅乐。所以,“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这是很好的一个路径。
搜神记:Slogan的下半句“从母语中寻找生命的缘起”,听上去也比较大而悬。给我们具体讲讲?
叶云川:比如我去梅州,这么小的孩子就不会讲客家话了,为什么?因为你讲客家话怎么上学?而且你讲会被嘲笑,是你很土。我也录客家音乐这些,你只要听到这个音乐一响起,马上就听到了中原,那种敦厚的东西显然在岭南地方不可能出现的,它就是千百年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的。所以只要音乐保留下来、语言保留下来,历史就能够很好地去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历史就是胜利者去书写,想怎么写怎么写,可能写的是面目全非的。我很在意“用母语寻找生命的缘起”,就是因为语言一旦扁平化了、普通化了以后,独特的多样的文化一定就消失了。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背后有着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遗传密码。
搜神记:要寻找那个中国,现在也只有到这些地方去了。你录的很多都是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也是因为语言吧?
叶云川:是的。语言是保留下来的,有些也掺杂时代的语言,普通话,比如说你听到藏族同胞用藏语讲电脑,他也讲电脑这样的外来词,但是绝大部分就是古老的语言。在这种语言当中,其实就能找到所谓生命的密码,就能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你才知道要到哪里去。
春节前我们去北京的郊区村子里面做一些原生态的语言和音乐采集,前面这个村保存得很好,相传几百年。可我们去新的那个村,所有房子全部推平、全部建新的,然后号称是有 400 年历史的村落。你凭什么说 400 年?你甚至可以说 4 亿年,因为这片土地存在了 4 亿年,但是文化本身呢?历史风貌呢?在你这里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比比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唯一能做的东西,其实也是我做“中国音乐地图”的重要动机,就是去留存一些必然消失的东西,肯定消失,语言消失、音乐消失,因为没有人听,你传统的东西谁去听呢?你在互联网上没流量,没流量就给你刷一边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了,音乐、影像、文字、图片,立体地把这种文化风貌基本地记录下来,之后不管多少年,就算一千年依然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就好像我们听西安鼓乐,一千多年前如果它没有演奏的方式传承记录下来,我们如何知道唐朝是什么样一种风貌?现在有很多山寨的那种都是想象的,但最起码来讲还有敦煌壁画还有音乐看到听到唐朝的这些东西。那其他的文化你看什么?可能什么都没得看,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状,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缺少最基本的尊重。
搜神记:后面会做什么项目呢?
叶云川:我自己喊的口号,是以一个普通的音乐人的力量,希望去聚合更多人,然后我们一起涌入海里。因为所谓的海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海洋。我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神叨叨的状态。2020 年和 2019 年两年的时间,基本是在做这个项目,2021 年我就是收尾。但是后面我会继续做下去,把传统的尽可能录入囊中,同时做更多有想象力的音乐。我觉得还可以做 10 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或者说一辈子,就一直做下去。
“因为 6 岁以前在乡下,我没有被束缚,就有无穷的创造力”
搜神记:你说你是客家人,为此经常去广东“寻根”。这是怎样一个来龙去脉,你能说清楚吗?
叶云川:我本身是四川人,是四川客家人,母语就是客家话。小时候我们就叫土广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叫土广东,所有的风俗跟四川人完全不一样,语言也完全不同。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族谱,也没有什么介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们跟周遭人是不同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吗?是直到我后来去深圳。我少年时去深圳,闯深圳,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站在罗湖区蔡屋围天桥上就哭了,那里是一个城中村,你想啊,一个人都不认识,举目无亲啊。然后我下桥,去找我姐姐的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人,发现城中村那些当地人说话我能听懂!这很可怕,因为我没有想到到了两千公里以外,那个村子里面的人说的话我能听懂。后来就开始琢磨为什么,由此就开始了自己对客家文化的一个兴趣。
搜神记:当时为什么要去深圳呢?
叶云川:不想在四川待着了。那时就觉得深圳是一个可以闯的地方,我应该去,就坐了 50 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深圳。50 多个小时的火车,结果是什么?下了火车睡在床上脚还是抖的,一直抖。深圳的几年是最艰辛的,但也是建立良好职业习惯的几年,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比如契约精神,比如永不停歇的拓荒牛精神。之后一度回到成都,享受了几年生活,但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后来看北京要开奥运会了,就来北京了。觉得奥运会那么重要,应该看看我有什么机会。
搜神记:我是2001年来的北京,你是哪一年?
叶云川:大约 2002 年。来北京的前两年,跟着人起哄干了一些事,上很多当,特别的糟糕。带着骄傲来,结果摔很大很大的跟头。也想要放弃,后来一想,别放弃啊,放弃就根本没戏了,在深圳不也熬过去了嘛。那做点什么呢?那就做音乐吧。
搜神记:为什么音乐可以做?
叶云川:因为之前的事情都是跟好多人一块儿做的,就觉得好多骗子,欠我的、骗我的钱,最后搞得我特别的惨,我就想,我要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我请了著名制作人张春一老师来做了一个案例,然后开了张,从此以后就是我了,我就一直做音乐做到现在。
要感激这么多年经历的东西,不管好的坏的,人生就是这样成长。可以自豪地说,在我的这些作品当中,确实比一般的要深刻一点点,它不是一个娱乐的东西,是可以让你听完以后会有些思考的东西,显然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历练,用音乐的方式给到了大家。
搜神记:一开始就是找人作曲、找人演奏吗?这个制作人究竟是做什么的?
叶云川:虽然小时候自己学习弹琴唱歌写歌,但弹不过别人唱不过别人写不过别人录音更不会。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学习,《三国演义》的刘备,武功不如关张,计谋不如诸葛,却可以凭借仁义勇气成就自己,哈哈。所以学习,是我从开始做音乐到今天都没有停止的成长方式。一个个作品不过是作业,我就一直学一直交作业,有时作业被人夸,有时作业被人弃我也无所谓,不过是作业,学到了,内心的进步才最重要。
我的音乐角色是制作人,像你一样,别人也总问我什么你到底做什么的,我说负责买盒饭,这是第一功能,你要让你请的音乐家吃饭啊。第二个说法是珍珠项链里的绳子,虽然价格只是两块钱,但没有这根绳子,这就不是珍珠项链。第三个,有些像汉字的“巫”字,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联接人,因为你听得懂神的语言,也感受来自常人的心声。
搜神记:你这样解释,估计很多人还是听不明白。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叶云川:成都,其实我们家就在现在的三环路。我之前回去过,去到亲戚家,拆迁早已抹去了我们所有的记忆,非常伤心。我特别感谢我小时候的那个生活状态。因为 6 岁以前在乡下,我没有被束缚,就有无穷的创造力。所以到今天我都很骄傲的是,我从来不缺创造力。你给我一把泥巴,我想塑造什么就塑造什么,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个玩具,你给我一个乐高,你告诉我它必须怎么拼,这个逻辑是怎么样,那我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机器,那没有价值的。恰恰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泥巴、泥塘、捞鱼、嬉戏,那长大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世界你随便去想象,是无限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吹牛说我在中国有超过 40 个民族的朋友,也去到过 40 个不同的国家,可以无限延展。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些在现代化当中全部被改变了,我们在从农业到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丢掉了最朴素的、最本真的东西,生活细节消失,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颗流水线上的钉子。
“只有在海里游泳的人才会充满敬畏”
搜神记:你是为数不多的在格莱美注册的中国会员之一,听说每年都自费把作品邮寄到美国参加评选。这是一件听上去简单、做起来比较复杂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做?
叶云川:2020 年又失败了,我当时好沮丧,伤心了好一阵。给格莱美评选寄唱片,你都不知道费了多大力,光运费就两万多。不过失落又不是第一回了,想想也就无所谓。我很少跟别人讲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实现的东西我不太讲。
搜神记:但我觉得很有价值。
叶云川:它应该算是一种情结。一个人在游泳池游泳,一会儿 50 米就游过了,每天游十几个来回,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厉害,但是只有在海里游泳的人才会充满敬畏。为什么?因为无论多强大的人,在海洋面前、在自然面前都不值一提,都会产生敬畏。像我们因为看的东西多一点点,就会产生敬畏。但是反过来,你也会产生惊喜,产生很多强烈的愿望,为什么?因为海洋里面会有无数的珍宝。
搜神记: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外面世界的?
叶云川:我最早一次去国外参展,大概是十六年以前去戛纳,跟着别人,自费去的。从戛纳去了巴黎,然后大家都去买名牌了,我就自己逛。巴黎有 18 条地铁线,我只记住一个站名,就开始各种晃荡,想去了解法国文化。从瑞鸣 2003 年一创立,我们的唱片上就中英文对照,而且中文用繁体字。因为简体字很多华人不认识,我要让国外的华人能够看懂。所以十六年前就开始了。
但是惨败的。参加过两次戛纳展览,一点不夸张,老外都是绕着我们走。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似乎跟辫子时代差不多。如何去改变这些狭隘的认知,就面临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去和别人交流,如果你只是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人家说再见、不送,人家很客气。但是你如果拿出真正的作品来,人家看你的时候就显然不同了。所以我的所有的作品都会把品质做得特别高,录音、制作、印刷,所以才会有了目前几十个国家都有一些听众的小小的氛围。
搜神记:从一开始就有意识这么做。
叶云川:不是我特别有意识这么做,而是他们都认同我的作品,因为我把音乐品质定位为TOP级的,我们的音乐品质是和世界一直在一起进步,大家都在这个水平,只不过这个风格你喜欢不喜欢。包括 2019 年我们在美国做了六场展览,还开了四场音乐会,就是尽可能去接触世界,去介绍自己的文化,希望自己能够站到那个顶端告诉别人,我们是优秀的。因为没有这个大家没办法对话。这之前,似乎亚洲最好就是日本,最潮就是韩国,而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便宜就好,就是这样一个认知格局。我希望像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话语权,因为没有话语权你说什么人家都不听你的嘛。所以我其实是刻意地去争取这些国际的影响力,虽然结果很失败,但一直在努力。我比别人要的要多。坦白地说,这么多年来都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的。2019 年还好一点,《荒城之月》在国际上获了几个奖,算是在国际上有些影响的作品。
搜神记:我个人觉得,你的作品是很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老外的。
叶云川:这是你考虑的,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把这个作品做好。我的作品是比较干净的,现在有太多作品不讲究,因为没市场,容易将就。但是我不行,我有精神洁癖,音乐里有一点脏的东西我就受不了,比如乐器与乐器之间产生的冲突性或者瑕疵。有一次混音中有一位录音师把凳子都踢飞了,被我气的,因为里面有我听到的不想要的声音我就要改,太苛刻招人烦。中国传统乐器以前基本都是独奏的,后来学习西方交响乐团要乐队化,它很容易造成冲突,包括我们要把 7 个人弄到一块吹拉弹唱的时候,你发现它全是冲突。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调节融合。这种形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哲理,传统文化里我们都是一个人,跟天地自然对话,所以我在长城的山谷中录了一个作品叫《天人合一》,那个反映很好,包括德国的伙伴说他也要在黑森林照我的录制。因为在山谷里弹琴,有很多自然的声音,鸟叫虫鸣,青蛙和鱼都在跳,特别和谐。当时海航、国航、南航的一些全球航线都播,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个很适合飞机上安安静静去听去幻想,但没有一家公司给我一分钱。
搜神记:可以去找他们啊,这属于商业。
叶云川:有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维权成本太高。反过来说,我最欣慰的还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大家觉得喜欢,影响了一些人,这不就挺好的?包括那天测一个网络平台的数据——真的不夸张,用我们的作品做背景音乐超级棒——我们其中有一首曲子被 31 万个视频使用,这带来的肯定是亿级的间接听过我们的音乐,我们有 2200 首曲子,那我就很开心,虽然它没有一块钱,因为它是免费的背景音乐。我认同这样的传播方式,我们是有合约的。让更多人听到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多少人给你钱,它是第二位的事情对吧?难道人家不给我钱我就把它藏着掖着了吗?那我做它干嘛?
搜神记:有很多机构跟你合作吗?
叶云川:是的,大家在网上听音乐的渠道我们都有合作,也还不错,多少都有些钱,我收到的最少一笔钱是 1 美分,也有月付费 20 元的。有一次去一大姐家,她让我喝了一包营养粉,价格是 40 元,我说这一口就喝了我两个月的钱。当然也有很多的,都很高兴。音乐对人的影响极大,如同盐,盐是卖的最便宜的,这或许是合理的,但会伤害从事音乐的人的心,大多数人会因此放弃,所以需要大家呵护。我们主要还是靠世界各地听众买我们的唱片、黑胶才维持这样的创作。我个人觉得,对于商业本身来讲,它一定是要有能力的人去做,假如没有能力的人去做,比如我们去做,显然就是猴子掰苞谷,你捡一个一定要丢一个。我为什么不愿意去捡那个,是因为我知道我捡那个我要丢这个,但是我这个是更重要的东西,我才不丢。那个有就有,没有就算嘛,对不对?因为你必然要取舍。如果你两个都给我,我也很开心,问题是不给两个,上帝很公平,给一个拿走一个,怎么办?那我肯定要我这个。你要做出好音乐,没准 200 年以后它还在啊。
搜神记:你肯定也有缺钱的时候吧。
叶云川:做音乐不怎么缺钱,因为钱都花在这了。我这么多年保持着置装费平均一年一千元(笑)。还有,最极端的是 2020 年疫情期间有半年中午就两个馒头,我一算,每餐 5 元就解决了。当然这是笑话,你把作品做好了,总是有无数的听众买单,支撑着你继续做音乐。最初做音乐缺钱的时候,我卖了房子,兑换成了录制音乐的费用。事实证明,财商极低智商不在线。那是 2005 年,三环边,五六千元一平米的北京。于是我租房住了 10 年,可以保证我总有钱做音乐。

在美国,叶云川与当地音乐家合作录制福音音乐
“我从小就信,我只要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爬到顶上葡萄就熟了嘛”
搜神记:前面你说过 6 岁以前在乡下,正是因为没有被束缚,才有无穷的创造力。想让你再跟我们讲讲你小时候的事。
叶云川:小时候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讲客家话?客家话就是我的母语,我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客家人,哥哥姐姐不会讲了,我还找回来了一些。6 岁前在乡下,没上过幼儿园,傻玩。傻玩其实是没有人跟我玩,因为我性格非常非常内向,你别看我现在侃侃而谈,像个话痨,小时候那简直了,见到女生脸红的不行,有人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是不上桌的,就躲一边去。一个人傻玩,最主要的玩法是什么?盼下雨。下雨的时候乡下的河沟里、田埂上都有鱼,可以尽情捞,很有收获。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鱼塘被开放了,所有人都可以去捞,但是所有大人小孩都在一个地方捞,只有我在没有人的另一个区域,一网,又一网,即使一无所获,也宁愿一个人捞自己的鱼。现在想起来,特别有画面感。
搜神记: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放养的状态。
叶云川:那个时候生态比较好,春天一打雷,那泥鳅就从泥里边蹦出来了。这时候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是我的战场,就拿个网去捞。有一次钓鱼的时候差点被鱼拖到水里淹死了,因为才几岁嘛,钓好长一条大鱼,鱼拖着我往下走,是附近游泳的大哥在池塘里面把我捞起来了。我 6 岁前所有的时间都是和泥土的关系,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就是人与自然的一个状态。这状态一直影响到我现在。
搜神记:音乐的启蒙是什么时候?
叶云川:也差不多 6 岁左右。因为我姐是学幼师的,她弹钢琴、唱歌什么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校园民谣,记忆最深的就是《捉泥鳅》,特别触动我,那就是我的天性,因为我就天天捉泥鳅。还有第二首歌是《蜗牛与黄鹂鸟》,我到现在都记得,黄鹂鸟啊你不要嘲笑我,等我爬上它的时候,葡萄就成熟了。很多人不相信,懒得爬那么高,费事。我就信这个话,我从小就信,我只要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爬到树顶上葡萄就熟了嘛,其实很小就建立了这样的价值观。
搜神记:后来呢?
叶云川:不好意思——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初中以后就没有受过官方教育,考不上高中,我连职高都考不上,因为成绩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数理化这样的课程我能考 2 分到 4 分,不是 5 分制,这是 100 分,那 2 分到 4 分全靠选择题蒙。上所有的课我只看小说,语文课我也看小说,我不听任何一个老师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老师气的不行,后来就说,你随意,只要不影响别的同学就好。
我不认识字的时候看连环画,而且攒好多,零花钱都买连环画书了。后来存放在乡下,有一年乡下亲戚说你们家老房子被烧了,啊?烧了房子不重要,但那些连环画全都烧没了,这是很痛心的。然后看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名著,没的看了就看港版的旧书。所以我认繁体字,你给我繁体书我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从小这么看。13、14 岁以前,就很幼稚地觉得把一辈子该看的书差不多都读完了,包括武侠书什么都看完了。
那读了很多书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很早就丰富了我的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是古代人的价值观,不是现代人的。因为它给我的太满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全在书里面讲得很明白,连《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都看了,小时候就对所谓的官场完全没有了兴趣。我在北京其实也没有刻意地交织,我也不会去迎合,我就做我的事,捞自己的小鱼小虾米,要不就看着天空幻想。
搜神记:其实到现在你还是处于一种野生状态。
叶云川: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处于一种野生状态的人。别人觉得很梦幻的东西,对我来讲无非就是要像蜗牛一样花更多的时间去争取。最后基本全都能实现。我特别在意自己这样两个成长阶段,6 岁、13 岁,可以说我 13 岁就停止成长了,后面的生活我认为都是在重复,就是不断在重叠自己信念里的这些东西。后来去欧洲做一些东西,去美国、去日本做一些事情,就是带着这种信念去做这样一些幻想里的东西。坦白来说学费交了无数,真的不敢去算这些东西,也没有必要去算。
“在一个快速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东西”
叶云川:我给你放一段音乐,正经地放,不是说作为聊天背景音乐的。这个是在 2017 年完成的一个作品《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其实也是受小时候看连环画和《山海经》的启发。这个作品花了差不多有 7 年的时间,过程很曲折,好在扛下来了。你看过《山海经》对不对?我其实不想去讲《山海经》里面的神神怪怪,九个尾巴十个脑袋,我觉得过度关注这些就根本没有理解《山海经》背后的东西。我是想从中找到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搜神记: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你找到了吗?
叶云川:我认为这些上古神话里有很多代表着传统中国的精神气质,但今天都丢掉了。所以我要从这个自己的作品中去再现它。比如说第一首叫《盘古开天》,就是开拓的。也有永恒的主题,战争、爱情,当然还有我一直更看重的另外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曲子叫《夸父逐日》。每次讲到这个,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就是他明明知道无法实现的东西,但他也要去做,也要牺牲,当他最后精疲力尽、无法追逐到太阳的时候,他把手上的桃木杖往东边扔去,他告诉别人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你想一想这样一种牺牲的精神多高贵啊!但今天的人不是这么讲,觉得傻,我就想从这里去讲中国人关于爱、关于奉献的这些伟大的东西。
搜神记:听了这曲子,确实汗毛倒竖的感觉。
叶云川:几个月前我们《神话》专辑的作曲家张朝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云川你是个“伟人”,我说你这是调侃兄弟啊。我们很熟悉。他说疫情期间哪都去不了,就把西方古典音乐全部淌了一遍,回头再来听《神话》,特别的骄傲和感动。当时做这个作品,张朝老师住北京的郊区,我从东五环往返一次大概 170 公里,我好像跑过八趟,三顾茅庐才跑三趟,我都跑八趟了。他说没有我不会有这样的音乐,我们是彼此成就。在商业社会,在一个快速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东西,而且录音的时候往返录了几个月,内心的那种悲凉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做就是赔钱的。一首曲子几十个人,而且都是找最好的演奏家来演奏,代价很大,大多数人未必喜欢,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去做,就不可能产生你想要的东西。结果未必就是多么好,但是你希望它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品,你就愿意这么去付出,对不对?
搜神记:你在录制的过程中,是不是总会找那种很特别的乐手或者乐器?
叶云川:对,你随便听一下,这个乐曲,古琴是 900 多年的,最优秀的古琴演奏家赵家珍老师演奏,那最后你听的那个弹拨,不是竖琴,是箜篌。我自己录制音乐使用过 400 种乐器,录音师李大康老师、李小沛老师、张小安老师,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录音师,这样可以保证作品的高品质。在不同音乐中会使用不同的乐器,不管乐器来自哪里,哪一个合适去用哪个。在不同的国家做音乐,我也都是选择那些非常棒的录音室。或许大多数人制作音乐不这么挑剔。但我觉得所有花的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追求极致,好的东西才有机会留下来。

与印度音乐家在一起
搜神记:你所有音乐当中,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
叶云川:对,哪怕是我看上去很欢乐的音乐,但内心也是孤独的。我的微信名叫“一个人的旅行”,因为我知道,就算咱们关系再好,也不可能一块“旅行”的,你注定了做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那这些作品当中,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带着这样一种状态。
搜神记:就是微信开机页面那个人,孤独星球。
叶云川:但是这种孤独也不是说因为什么事,是因为我从小就这么过来的嘛,就是从几岁就这样。
搜神记:孤独是音乐的本质嘛。实际生活中你不觉得孤独吧——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朋友。
叶云川:还是觉得,还是有。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蛮辛酸的东西,但是我有个好处,我会把它转换成力量。当我觉得这里面承受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把它转换成能量。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嘛,这种状态会帮我,而不是说会影响到我什么。生活当中你看很多人都高高兴兴的,会享受,那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在音乐当中,我每天在这就已经很享受了。问题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我另一个更大的心愿,还是希望把它传播到更多人那里去。很多人不是说不喜欢,而是因为不了解你,都不知道你有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充斥的都是那种属于流量的东西,我们不占流量。
搜神记:那在你这样一个人看来,实体唱片会消失吗?就像我们的传统媒体一样……
叶云川:这个问题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不是会不会消失的问题,就是必然消失的嘛。我跟你讲,你认识我很荣幸,我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唱片的传承人(笑)。这是没有悬念的,但是我基本上会做到最后那一个。今天我们面临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无论你付出多少艰辛,最后也无法体现你的价值,因为人们不会为这些价值去买单。比如我做“中国音乐地图”,那么厚重的东西,如果把它全部数字化,它全是碎片,那怎么去体现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所以最后,还是要做成一个载体,像这几年我弄的黑胶、CD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这种东西有一定的仪式感,有美学上的认同感,很多东西可以浓缩到这个上头去。你尽力去在你能够承受的条件下做成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且确实是对标世界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这些作品拿到美国去,都说漂亮,book。美国现在做的东西很简陋,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印刷很贵,简陋的纸片、塑料就那么一弄,艺术家出门,拿个包就带着走了,现场签售破纸片。我每次去国外的时候,都是带整箱的唱片,我有一个超级大的箱子带着去,走到哪全部发完就高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品质代表着中国。
搜神记:做这种展览,中国是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呢?
叶云川:理论上应该就是这样,因为它不划算,不划算的买卖只有傻子才干。我上次在中科院做演讲,我说下面没有一个傻子,所有人都笑了。我说没有傻子的世界很可怕的,每一个人都那么聪明的话,那傻子都不够用了。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