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黄纪苏/文
庚子年(阴历)五月二十日,京城某士绅在日记中素描了一幅火灾远景图:
将午,忽正南有烟,黄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曰:“此焚屈臣氏药房也”,市肆无惊,若豫知其事者。午后烟不止且变黑色。是日南风,其直烟变而为横,从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北逾鼓楼,仿佛汽船之在海,度其势不止屈臣氏一家矣。
这是晚清史上一场著名的大火,纵火者的初心只是一家西药店,结果却是商家一千八百多户、房屋大小七千余间烧得干干净净,人员倒没什么伤亡。那一带店挨店铺连铺、横梁立柱、门板窗幔、桌椅板凳都是易燃物,这样的下场并不意外。意外的是,火是白天放的,烧了一天一夜,抢运财物不缺时间,可老板伙计们却只剩得一卷账本、两袖清风。他们缺什么呢?
京城另一居民在日记中为我们记录了大栅栏火场的近景实况:
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梵香叩首。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乱。即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纵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当时若不听团民愚弄,先将货物抢挪,虽云劫数难逃,究可保留万分之一也。
义和团可以不让大家救火,但拦不了大家撤离——那么多家哪里拦得过来?大栅栏人之所以没紧急搬迁,是因为他们相信义和团指哪儿烧哪儿、不及无辜的先进技术。即便是火势蔓延开后,据其他史料记载,他们也没认为义和团技法无灵,而是埋怨隔壁广德楼的扑救干扰了神术的正常发挥。他们觉着自己是“良民”,不是教民,本该在火外而不在火里。

《义和团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5月
平心说,大栅栏被烧并非必然。如果义和团不把纵火作为常规武器,改烧教堂为拆教堂,焚洋行为扒洋行,火不听指挥刀听指挥、镐听调遣,那么就有可能实现精准灭洋。问题是,因此而不在火里的大栅栏人乃至更大范围的人,是否就在火外了呢?答案后来人早就知道了。可“市肆无惊”的当时人呢?
一
得先对“祸”做点分解。庚子之祸可以分为直接祸和间接祸。直接祸包括杀人放火,针对的是洋人、教民以及涉洋人群;间接祸是直接祸引起的连锁反应,包括社会动乱、经济凋敝、联军报复、巨额赔款等等,牵涉就没边了。直接祸中的毛子金发碧眼好分辨,暂可不论。“二毛三毛”可都是龙的传人,由于直隶甚至山东进京的义和团人地生疏,他们如何知道谁是谁呢?老德记卖的西药以及众多洋行挂的招牌倒是“三毛”的身份标记,师兄师弟逛街时就能发现。但藏在小胡同里的“二毛(教民)”要是没群众举报是不容易找到的,这其中,你本来不是汉奸,但仇人或政敌非说你是的可能性就不容忽视了,而且时人的笔记日记中也确有反映,例如杨典诰的《庚子大事记》便记有:“编修刘可毅,既非在教之人,第平时喜谈时务经济,竟被义和团民所戕害。不仅编修一人遭荼毒,以是而丧身者实凡有徒。”想必义和团不会搜索并研读刘编修的文章,他之被难,很可能是庄亲王领导的联拳灭洋工作组与义和团联合执法的结果。另外,义和团说二毛子脑顶有十字,一般人看不见他们能看见。几十年后康生也凭借类似的特异功能侦破了不少“敌特内奸”。义和团还有一项甄别奸良的绝技,就是点燃一道符箓,烟若是直的,嫌犯即可回家和亲人团圆;若是曲的,身子和脑袋就分家了。我在史料中读到最冤也最不冤的,要属一些女性教民,她们在街上见了义和团吓得跪地求饶,义和团并不念其主动投案,“率被拉去斩之”。
面对朝自己脑门飞来的直接祸,毛子的反应虽有快慢之分——法国的主教樊国梁有教民帮接地气,一上来就意识到大事不妙;而英国领事窦纳乐更多依赖清廷的上谕诏书、总理衙门官员的说辞神色以及其他上层线人的小道消息,刚开始并不觉得形势有多严重——后来都紧着调兵遣将、构筑工事。二毛也多扶老携幼涌入使馆教堂。西城有位教民想到亲友家躲躲,可哪家敢接那祸呀,他们后来艰难辗转才逃到了西什库的北堂。总之,他们对直接祸的反应,可能没羚羊豹子那么敏捷,但都能把灾难看成灾难而不是地坛庙会或淄博烧烤。
间接祸不容易说却最值得说。间接祸位于直接现实之外,因果相对复杂,考验的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文化的理性推断能力。理性推断不需要脑子多聪明,但需要脑瓜别太热,太热就成了傻瓜,会被骗子像牲口一样地吆喝,别说见了棺材,就是进了棺材还偷着乐呢。理性推断还包括借助他人的经验,尤其是淬炼成常识的经验,同时明白经验常识也不总管用,迷信不得。再有,头虽不能太热,心却不能太冷,要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同情心既是一种情感能力,也是理性推断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对别处别人的苦难如果一点感觉没有,当轮到自己时他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反应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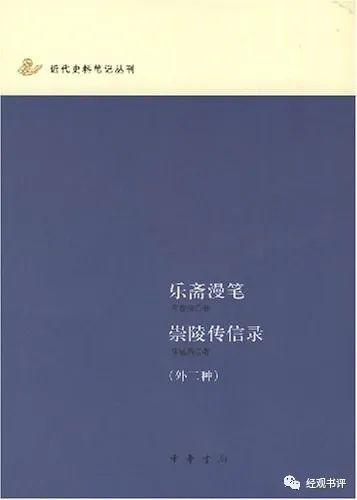
《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
岑春煊 恽毓鼎 王照 高树 /著
中华书局
2007年7月
大栅栏化作青烟的那一千八百家,商户应占不小比例。对此我一直困惑:能把别人的钱挪到自己兜里的人,谁能蒙得了他们?我小时候换纪念章,两个小红章换来换去换成了一个,而同伴却一个倒成了俩,让我一劳永逸地明白了自己脑子不够用,后来谁下海我也不下。大栅栏的商人,怎么却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常识都被义和团忽悠没了?真不知他们的判断力在中国商人中算高还是低的。上海的商人明显高出一块,1900年6月9日《新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论关心国事者惟商人》,说京津大乱的消息传到沪上,“货物不敢畅运,银两不敢划兑,过客(商)不敢启行”,商人都急成了热锅上蚂蚁,天一亮就派伙计买报,半夜还到报馆来打听新动向。不久之前,上海的商绅一千多人联名致电朝廷,恳请不要废黜光绪,其政治站位令人刮目。
二
不过同在上海,官员跟商人又不一样。据该文讲,某巨商紧急求见当地某领导,巨商说得上气不接下气,领导“怡然蔼然拈须对之”,末了来一句,国家兴亡随它去,操那心呢。巨商又求见了另一领导,领导说,我们这些外官跟京城的事没啥关系。文中分析了官商差异的原因:商人的利益来自贸易,贸易江海相连,远处也是近处;而官员的利益另有来处,北边乱了他在南边官照做、俸照领。该文感叹道:事情只要不切己就不是事。其实,庚子的间接祸是否“切己”,官跟商的理解固然不同,官跟官也不完全一样。东南互保的前提是东南疆臣的“大局意识”,即对间接祸的充分体认。其中的发起人兼联络员即是亦官亦商的盛宣怀,这应该不是巧合。
京中的官员对间接祸的态度也形形色色。这种复杂性在侍讲学士郓毓鼎一人身上都有体现。郓毓鼎写于庚子十年后的《崇陵传信录》很有名,有些专家会根据此书把郓毓鼎划入“剿拳和洋派”甚至“汉奸”。但从其当年的日记看,还真不尽然。以下顺时针摘录数则。
他五月初六日记到,“黄霾蔽天,日色无光,日有焚杀,大乱将至,心焉忧之。”
十二日,他请人用周易算了一卦,“其兆京城无恙”。
十五日其伯母七十六寿辰,傍晚他正和宾客一起聚餐,忽然传来日本领馆书记被甘军杀害的消息,“大衅将起,同人相顾失色,狼狈散去,座客一空。”
十七日,“教民老幼妇稚,死无孑遗,尸横路衢,火冲霄汉。京官来往者,不复常度,咸谋送眷出都。余义不容去,家累亦过重,听之而已。”同日,他又找人算了一卦,算的结果是:“京城甚安,交小暑节即可渐定。”
二十五日,他带着问题去了关帝庙,一问义和团是否真得到了神灵帮助;二问洋人能否歼灭;三问京城是安是危。得到的答复是一首诗加一首解诗,两诗其实什么都没说,但他却读出了“晓然圣意所在,拳民必可成事矣”。为了双保险,他又用蓍草占了一遍,得到《周易》中一个搁哪儿都行的金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他解读为:如果不将灭洋进行到底,国家就等着蒙羞吧。
第二天他在城外,“未刻,探事人出城,知十余国使馆俱付一炬,洋人兵丁男女聚而歼之,无一生者。义和团奏凯而出。数十年积愤一旦而平,不禁距跃三百。”
之后,他的乐观情绪随战场形势每下愈况,六月二十六日他写到,“一路拳民蚁聚,服饰诡异,神色狂悖,知祸不远矣”。
郓毓鼎对形势的推断,依据的是常识感、历史经验、当前实践(战场形势)、求神问卜几项。他的“心焉忧之”,应来自以往哪次灭洋中国都赔得吐血的历史经验(受神侠教育的民众还真不一定了解这些),以及大乱之下玉石俱焚的常识。对于这样的经验及常识,1900年初夏的郓毓鼎也认也不认。之所以不认,是因为他相信鬼神,并通过占卜从鬼神那儿得知,义和团属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术。也就是说,义和团既不归常识常管辖,还可能废了历史经验。之所以也认,是因为义和团一败再败的当前实践让他“微悟此辈之不足恃也”。应该说,对于郓毓鼎,当前的实践是检验神术的最终标准。这种实践标准当然比焚香拜表强,但它踩着现实的后脚跟儿,也只能是承认事实而不能推断或预测事实。没推断预测也就没提前量,而没提前量等于撞上南墙才发现南墙。我阅读这一时期的史料有得到个未必可靠的印象:在知识结构和推断力上,可以把的郓毓鼎看作当时士大夫群体的平均数或中位数——也许略高一点。
 《袁昶庚子日记二种》
《袁昶庚子日记二种》
袁昶 /著
戴海斌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7月
和郓毓鼎相比,大理寺卿袁昶可谓高瞻远瞩了。其《乱中日记残稿》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写到:“区区各驻使,胜之不武,屠此数人,彼族即不敢报复耶?”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在一道奏折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东南督抚的态度也差不多,被紧急委以议和重任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前给清廷发电,恳求千万别再戕害外国使臣,否则他白发苍苍也只能白跑一趟。把幼儿老妇打残打死不难,难的是人家的猛男找上门来怎么办?这个常识不少动物都无师自通,可那些王公大臣却一时都忘了,以为拿下西什库、东交民巷就万事大吉了呢。郓毓鼎也是“距跃三百”之后好一阵才想起来。
三
当间接祸步步逼近、快质变为直接祸时,不少官员或安排或率领家眷悄然离京。郓毓鼎听说诗人樊增祥也在流民图中,特在日记里写下“名士之可鄙如此”。樊增祥后来又跻身红娘的大队人马,写了著名的《后彩云曲》,将联军统帅瓦德西和妓女赛金花撮合在了一起。也有很多官员没选择离开,情况不一。如首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金石学大家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后长叹一声:老天这是让我死在这儿啊!这位“看街老兵”筹措枪械弹药求人求到远在武汉的妹夫张之洞那里。北京城破,他与老妻、长媳先服毒后投井,和天门山约死群的模式相同。京城绅耆“仰药以殉、引火自焚、投井而殁达一千九百九十八员名”,这些儒门书生确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郓毓鼎留下的原因比较复合:有他从挂签蓍草那儿得到的定力:有出于职守纪律方面的考虑——他日记里对那非段常时期单位签到点卯请假销假等记之颇详;也有迁大不易的苦衷——我印象中,在清人乃至民国人的日记书信中,交通费或盘缠是笔很大的开销,像徐志摩那样打飞滴穿梭于名媛之间简直是特殊化到了逆天。
还有一些留京官员恐怕是没想到“祸”也通“涡”,会像旋涡一样把自己从祸边旋到祸里,跟鬼子汉奸殊途同归。他们或许是以为水再大也得从脚往上淹,脚上有腹,腹上有胸,自己属中国头部,且轮不到呢。这的确是社会的常轨,只是洪水确如野兽,先咬哪儿还真不一定。据当时人的书信,“东四牌楼头条胡同起至王府井胡同止十余条胡同,满汉官大宅门抢去不下二千家”。二千未必是确数,也就随口一估吧。当过帝师的孙家鼐没能幸免,从家里逃出来连换的衣裤都来不及带,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就不如现在有些官员,纪委同志来敲门,人家拉着行李箱正候着呢。与孙中堂地位相仿的徐相国也摊上了,其家被“抢得一空,屋亦烧去”。徐桐老先生是联拳灭洋学派的首席专家,按常理真不应该。
那些缀满朝珠花翎的官宦,无论哪种睡姿也梦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一些“”临时农转非人员”拉下马拽出轿跪在路边,会被洋兵抓去抬尸体运渣土,一夜回到童子试发榜前。就连这个群体的“群主”及“群副”也是单衣薄褂仓猝“西狩”,全无“预案”。平日喝玉泉山特供山泉,这会儿途中口渴了,井里却浮着人头,只好拿根秫秸秆边嚼边嘬。夜晚寄居民房,太后冻得跟皇上背靠背苦捱到天明,自光绪亲政以来,母子俩的心从来没挨这么近过。虽然怀来县接到通知,叫给副国级以上的领导预备满汉全席,但规格归规格,乱离中的接待水平最高也就是碗粥。吴县长在逃空的民宅里广搜博求,得到比天然鸡蛋石还美妙的五个柴鸡蛋,“亲自”生火煮好呈上去,老佛爷吃仨给光绪留俩。

《庚子记事》
仲芳氏 杨典诰 华学澜 高枬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辑
中华书局
1978年
再说义和团。京城有严格的城门启闭制度,大官回城晚了,照样吃闭门羹。但这是世间法,义和团随到随开,因为很多人,包括守城官兵及其上司都相信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神兵,不同于一般勤王兵马。他们开到北京后,“京城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后来的西纠东纠都没负责过这样关键的岗位。杀袁昶、许景澄等大臣,由他们押送菜市口。除了灭洋,他们还挖出其他颠覆势力如白莲教。官方一直有人给义和团扣该教余孽的帽子,他们主动切割也能理解,问题是他们从“四乡抄获”的那些“白莲教”就是一帮穿上龙袍冒充万岁、戴上凤冠冒充娘娘的戏剧爱好者,一群躺平却还要叉腰的草民,这些人“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惨不忍读。说义和团接管了京城的公检法似不为过,而且从捉人到砍头,你说是一锅煮也行,叫“一元化”也没问题。当他们红得发紫、举着“兴清灭洋”的大旗、揣着“清家”发的十万两红包时,能料到不久被官兵拖着辫子一刀两断,鬼子在旁边摄影存照么?
还有大众,说多不忍,抄两段时人的日记吧。其一在事变之初:“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幌动街市。”其二在城破之日:“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拥塞道路,无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带水而行,嚎哭之声惨不忍睹闻。”两段的主语差不太多,状态可差太多了。
还得说说洋人,他们是直接祸的受害者。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弃孩病婴义务当保姆的修女,何罪之有?据说山西某位修女被扔进火堆时说我救了不知多少中国孩子,你们怎么这样对我呢?面对这样的天问,有种回答闻着特别离谱:没人去你家打你,是你上门找死的。照这逻辑,五一长假哪儿也别去了,路过人家门口就活该头破血流。不过事情也确有另一面:1840年以来,列强没少欺负中国,距庚子最近的日本割台、德国占胶,都属原汁原味的强盗行径。庚子年中国官民针对洋人的那些做法,很难脱离这个大背景做孤立的理解。庚子被难的外国人士,固然是当日颟顸王大臣、愚昧师兄弟的直接受害者,又何尝不是此前洋枪洋炮及不平等条约的间接受害者?后一点,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想到。不过据我浏览到的教会文件,事后他们还是有反思的。
还得说说教民,庚子年属他们灾难深重。此前所谓的“民教寻仇”其实并不对等:抛开是非曲直的错综参差不论,即便教民在日常争讼中借助教会势力对地方官吏施加了影响,非教民也多是赔几桌席或几台戏,而义和团对教民则是非抢即烧、非烧即杀,感觉就像打乒乓球的遇上踢足球的。不过联军来了,一些教民如宣武门的安三儿又狐假虎威以搜捕义和团为名敲诈东家勒索西家,真让人叹息不置:还是只顾眼前,不想因果。你这一脚出去,踹倒的固然是别人,等转一圈,飞来块砖头,不定谁家玻璃粉碎呢。
(作者为社会学家、剧作家,本文参考文献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义和团史料》;中华书局:《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