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果尔达》电影截图)
韩福东/文 果尔达·梅厄的自传《我的一生》被两次改编为电影。1982年的那一部是《一个叫果尔达的女人》,饰演她的英格丽·褒曼获第40届金球奖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奖。不过这部电影中国观众看过的不多,豆瓣甚至没能形成评分。另一部就是今年的《果尔达》,由获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海伦·米伦出演,这部电影只聚焦“赎罪日战争”——《我的一生》中的一个章节。

《我的一生: 梅厄夫人自传》
[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 /著
舒云亮 /译
读库 | 新星出版社
2014年7月
“赎罪日战争”发生时,当时果尔达任以色列总理。在巴以冲突中,她以作风强硬而闻名,那时撒切尔夫人还没出任英国首相,果尔达就是当时的“铁娘子”。不过,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以色列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以色列因情报失准而毫无军事戒备,被埃及和叙利亚联军打得措手不及,虽然战事后来反转,但最终2500名士兵死亡的事实,还是让果尔达遭到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果尔达平安度过危机,半年多后,却还是在责难的喧哗声中辞去总理职务。
在《我的一生》中,果尔达称“赎罪日战争”是她最难于下笔的事件,是一场灾难和恶梦。那时她已经75岁,罹患白血病,在电影《果尔达》中,我们能看到她即便在接受治疗期间,仍不顾健康状况一根接一根抽烟——这是她个性的一种表现。她卸任后便开始写作自传,《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1975年在美国出版,3年后,她便与世长辞。
毫无疑问,果尔达的自传带有鲜明的以色列复国主义视角,她的这种倾向性也影响到了《果尔达》这部准备冲刺奥斯卡的电影。这部电影非预期地与今年10月发生的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相遇,想要不引起争议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翻阅果尔达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自传,并检讨这些年来巴以局势的得失,或许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一
果尔达1898年诞生于沙皇俄国时期的基辅,1978年逝于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恰是当下举世瞩目的战争焦点。似乎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果尔达的一生与战乱纷繁交织在一起,形同犹太复国主义命运的一个缩影。
在《我的一生》的结尾,果尔达说:“现在我还有一个愿望:永远不忘从我在沙皇俄国的一间小房间里听到犹太复国主义起,直到我在这里度过的半个世纪,我应对我所得到的一切表示感激,我在这里看到了5个孙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作为自由的犹太人成长。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
“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这句箴言一样的愿望,始于果尔达的童年时代。记忆是零星而散乱的,《我的一生》提供的关键词包括贫困、饥寒和恐惧。她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听闻犹太人将遭集体屠杀的传言,虽然她那时对“集体屠杀”意味着什么还缺乏准确的理解。
果尔达从小受姐姐谢伊娜影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死后,谢伊娜从1904年夏天从姨母那里听到消息的那天下午起,在两年时间中只穿黑色衣服,为赫茨尔带孝,一直到她们举家搬到美国密尔沃基为止。谢伊娜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沙俄从事秘密政治活动,这令母亲极度焦虑,这最终促成她们去美国与在那里打工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去美国也没能改变谢伊娜,在她的影响下,果尔达也最终走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并且比姐姐走得更远。果尔达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的时间确定为1918年冬天,当时费城举行美国犹太人第一届大会,主要目的是草拟纲领,提交给在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保卫欧洲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果尔达被选为密尔沃基的代表,那一年她20岁。3年后的1921年的5月23日,果尔达和伴侣莫里斯、姐姐谢伊娜搭船去了巴勒斯坦,谢伊娜远离丈夫还带上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出发前二十多天,巴勒斯坦刚刚发生一起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全面骚乱,40多人被杀害。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的意愿。
《我的一生》并没有交代太多背景资料,果尔达甚至没有阐释最初决定去巴勒斯坦的完整动机。相关数据显示,截止1921年,一共有18500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很大程度上是受1917年11月2日的《贝尔福宣言》影响,英国政府开始公开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
巴勒斯坦的生活非常艰苦,不是每个犹太人都能留下来,但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有着超强犹太复国理念的人。果尔达很快加入了一家基布兹(集体农庄),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半。她陶醉在集体生活中,但常年生病的丈夫莫里斯认为基布兹“由于教条主义的原因使本来已经困难的生活更为困难是荒谬的”,她们于是离开了基布兹,生活陷入短暂的困顿。那时恐怕没有人预见到她会成为第四任以色列总理。
英国学者托尼·朱特也是犹太人,1963年他去以色列的一家基布兹工作了7个周,回到英国后已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左国家。”他这样评价,“我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亲身经历,使我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最明显的是为以色列摇旗呐喊的美国犹太社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遭遇的是更加狂热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这让以色列建国史始终被一阵氤氲的血色所笼罩。果尔达实际上和托尼·朱特一样,是个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她的原生家庭并不特别信教,父母只是有着犹太教的饮食习惯,并庆祝所有犹太节日,仅此而已。果尔达本人也“记不起我在孩提时曾常常想到上帝或向我个人崇拜的神灵祈祷过。”但碰巧她信奉的世俗理念也是狂热的。如果不是这种基于宗教或世俗理念上的狂热,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可能落到实地;而她们的对手的基于信仰与理念的狂热,让耶路撒冷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块撕扯着阵痛的圣地。
二
在赎罪日战争之前,巴以最剧烈的冲突当属1967年的六日战争。按照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描述,阿拉伯世界在战场上集结了50万人、5000辆坦克和900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而伊拉克总理阿里夫解释道:“我们的目标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但6月5日凌晨,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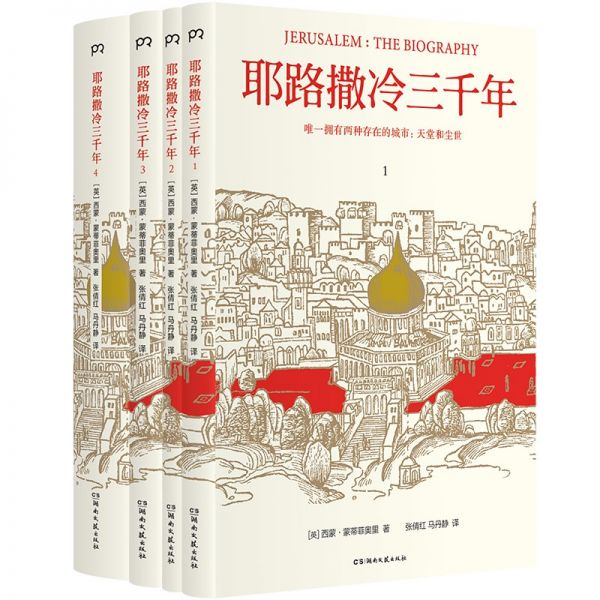
《耶路撒冷三千年(全新增订版)》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张倩红 马丹静 /译
浦睿文化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
六日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扭转了以色列的战略劣势。果尔达回忆胜利后的日子说:1967年夏访问以色列的人都能证明,犹太人处于异常的欢快状态中,好像一次死刑被撤销。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具体事件来说明总的气氛,当然是拆除1948年以来把耶路撒冷城分为两半的混凝土路障和铁丝网时的情景。这些可怕的路障比任何东西都能说明我们生活的不正常,它们被推土机铲除后耶路撒冷在一个晚上变成了一座完整的城市,“城市里射出了光芒。”
但阿拉伯人显然不这么看。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六日战争的延续。以色列拒不归还占领的土地,在国际上也有非常大的非议。果尔达在自传中争辩说:“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自称他们的目的只限于到达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全面征服以色列国。我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阿拉伯国家的真正目的一直是彻底消灭以色列,我也从不怀疑,即使我们退到远离1967年边界线的一块小小的飞地,他们依然会力图把这块飞地和我们一起连根拔掉。人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便能理解,如果我们是在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上,以色列的形势将会是怎样。”
果尔达的意思很明显,如果当年归还了六日战争占领的土地,那么在六年后的赎罪日战争中,早期的失败将使以色列遭遇亡国之痛,再无翻盘空间。但果尔达也必须直面一个问题,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的胜利,只会进一步激发阿拉伯激进分子的斗志,而来自阿拉伯的袭击,又会进一步拖累以色列进入以眼还眼的深坑。
六日战争之后,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于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这个故事可参看斯皮尔伯格2005年导演的电影《慕尼黑》。而以色列以眼还眼恐怖行动的最明显案例来自阿里尔·沙龙。沙龙也是赎罪日战争以色列转败为胜绕不过去的关键军事人物,他后来当上了国防部长。在1982年的一次战争中,为报复巴解组织针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沙龙领导下的民兵对难民营中数百名巴勒斯坦的平民进行了屠杀——沙龙为此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这已是果尔达离世4年后的事情了,巴以局势还没有好转的迹象。
而哈马斯在1987年后的崛起,更是赎罪日战争后被激化的阿以相互仇杀的产物。和哈马斯比起来,阿拉法特的法塔赫都算得上温和。哈马斯崇拜的是1935年被英国警察打死的卡桑,作为一种致敬,他们命名自己的武装部队为“卡桑旅”。
1980年代的巴以冲突以不妥协为根本特征。对立阵营中的鸽派人物一旦表达和平意向,常常不得善终。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因此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暗杀,预示了这10年灰暗的基调。1990年代的巴以谈判似乎有好的进展,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甚至共同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一年后拉宾死于犹太狂热信徒的枪击,让和平的幻象破碎。
拉宾是继果尔达之后的以色列新总理。他是果尔达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年在耶路撒冷出生的,正好小了一个世代。果尔达在自传中说:“拉宾的一代和我的一代有许多不同之处,但这些差异不如相似处那么重要。像我的一代一样,这代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将作出努力、斗争、犯错误和取得成就。和我们一样,他们决心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以色列国的发展和安全和实现在这里建成正义社会的理想。和我们一样,他们知道要使犹太人民继续存在,必须有个犹太国,在那里犹太人可以像犹太人那样生活,不是靠别人的宽容,不是作为少数而生活。我深信他们为各地犹太人带来的好处至少会同我想做的一样多。”
那么以色列的前途如何?在1970年代末期,果尔达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相信我们将同我们邻邦讲和,但我相信没有人愿同一个孱弱的以色列讲和。倘如以色列不强盛,就不会有和平。
在拉宾之后,以色列似乎仍信奉这一点。
三
1890年——果尔达出生前8年,赫茨尔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他在维也纳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促使他走上犹太复国主义道路的诸多理由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俄国1881年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是“反犹主义”一词在1879年被生造出来之后的一种现实应对,果尔达所在的基辅,也是“反犹主义”的重灾区。
在1888年到1914年,有差不多170万俄国犹太人去了美国,果尔达一家正在其中。所以我怀疑《我的一生》夸大了果尔达的姐姐谢伊娜从事政治活动对促成移民的作用,它可能确有推动,但整体上将其看作一次席卷俄国的逃避“反犹主义”的迁徙一部分已经恰如其分。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将“反犹主义”归结为一种对现实的扭曲:“犹太人总是代表了一种国际贸易组织,一个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们到处都一致的利益,一种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将所有的有形可见的政府都降为一种表面之物,被后台操纵的傀儡。由于他们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密切关系,犹太人就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权力,并且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内,所以总被人怀疑是在毁灭一切社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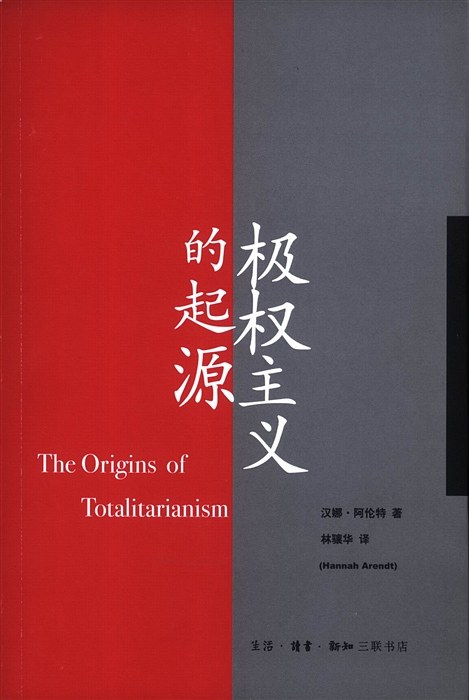
《极权主义的起源》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0月
而“反犹主义”在各国兴起后,那些与“权力”无涉的犹太家族也不能置身事外,譬如出身平民的果尔达一家。“反犹运动”动辄以大屠杀的面貌出现,加剧了犹太人的内心紧张感。果尔达清晰地记得那些关于纳粹死刑毒气室用犹太人尸体做肥皂和灯罩等可怕的消息传来时,她们立刻完全相信。但果尔达过去一直欣赏的一位英国官员则认为这完全是奇谈怪论,并带着奇怪地表情瞧着果尔达说:“你肯定不会相信这一切的,对吗?”果尔达能从他不安而仁慈的蓝眼睛里看出他以为这些相信阴谋论的犹太人发疯了。“你不能相信你听到的一切,”英国官员在辞别时温和地同果尔达说。
对大屠杀的敏感,最终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建立,也塑造了以色列人的狼性。托尼·朱特就曾在《思虑20世纪》一书中做过反思,他说:“今天的以色列类似于沙俄帝国终结之后出现在东欧的小型民族国家。如果以色列跟罗马尼亚、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成立于1918年,而非1948年,那么它将跟‘一战’所催生的那些狭小、脆弱、充满怨愤、主张民族统一、不稳定和种族上排外的国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以色列直到‘二战’之后才出现。其结果是,它坚持其略显偏执的民族政治文化,并过分地依赖大屠杀——它的道德拐杖和用来抵挡一切批评的武器。”这样的批评出自一个犹太人之口,相对而言更容易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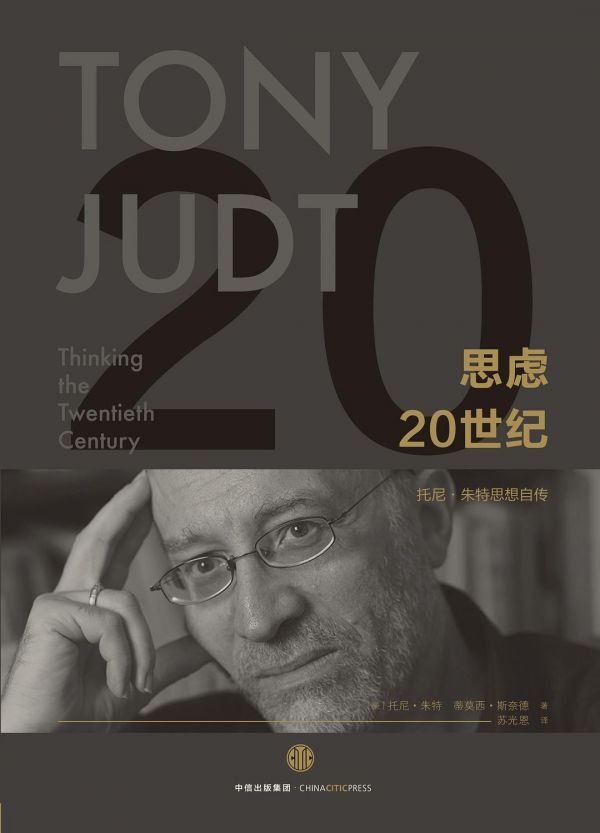
《思虑20世纪: 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英] 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著
苏光恩 /译
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
2016年2月
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仍算得上是一个在不断反思并寻求进步的国家。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人权记录有很多污点,果尔达在世的时候自不必说,她去世后尚有1982年针对阿拉伯平民的屠杀。但如果用一种比较的眼光凝视耶路撒冷,我们该承认,他们正在变好,且不说日常弥合阿以冲突的各种举措,即便是反击哈马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他们也必须顾忌战争法的诸多约束。
果尔达临终前在自传中强调“自由”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重要意义。对阿拉伯世界,“自由”又何尝可以被轻忽?以自由看待巴以冲突,在耶路撒冷——西蒙·蒙蒂菲奥里所谓的唯一拥有天堂和人间两种存在的城市,和平无法在单方拥抱现代文明的前提下实现。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