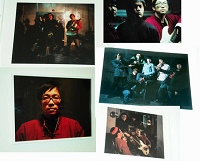
经济观察网 王隽/文 3月13日,难得温暖的周六。798里到处都是挂着卡片机的游人,他们好奇的站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外,打量着暂时不对公众开放的展览——《有种》,阳光打在他们充满疑惑的脸上,人群中偶尔有人交头接耳道,“他,放出来了?”
尤伦斯里同样也到处都是人,与外头的游人不同,这里有范儿的青年们都挂着单反。他们围着高大的卷毛的张元不停的拍照——穿着西服和深蓝色牛仔裤的他,站在照片墙前面,这一次扮演的是摄影师。围住他的单反青年们没有提及敏感的词汇,都煞有介事的指着墙上的某一幅作品向他询问。说起来,他最近少有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一次面对媒体,算得上“有种”的行为。
半年前,尤伦斯的策展人郭晓彦开始和张元谈起这个展览,他们都想到了十多年前的那部电影。1993年,刚刚毕业不久的张元在北京城里观察生活,他看到一些愤怒的年轻人,为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处处表达着自己“有种”的价值观,于是他拍了《北京杂种》,一个江苏籍的导演替北京青年们记录了青春,也许作为南方人的他骨子也有这分拗劲儿。
十多年的时间,当电影里的年轻人们已经拖家带口四十不惑,京城里的青年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只不过,从90年代初期的诗人、摇滚歌手到现在的80后CEO,青年们追寻的目标似乎从理想化更多地为生活所迫转向世俗。但张元相信十多年前的那个人群仍然存在,仍然在这个城市里扮演着充满力量和梦想的“有种青年”。
策展人郭晓彦说,这些照片上的人物,都将是张元新电影里的角色。这是我们第一次先于电影看到了角色,也算是张元的突破。这里有平和的摇滚乐手、纹身青年、焦虑的女演员、年轻的和尚、沉迷于整容的男孩、满脸戾气的女作家,对于80后的有种青年的选择上,张元似乎一再的偏爱特殊群体——这里没有普通人。我原先对于微博上发起的这次“寻找有种青年”的活动充满期待,以为会充满了机修工人和盗版碟贩子,可惜展览上看到的都还是些阳春白雪,原来,他所定义的“有种”,还都是些文艺的“有种”。
只不过,相比较《北京杂种》里社会边缘性更加强烈的卡子、大庆,《有种》里的青年们更为这个多元的社会所接受。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止是“有种”的意义,更多的还有价值观和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北京这座城市,不会缺少有种青年。在看完所有的照片后,这是我从张元的眼睛里看到的答案。
他在发布会上唯一说的故事就是那个整容的男孩小谭。大年三十的傍晚,张元接到小谭的电话,说他今天要在医院里进行鼻子的整形手术。张元立刻驱车到了小谭所在的医院,他一直不能理解这个男孩为什么对自己容貌一再不满意,习惯性的要去修修补补,似乎在医院里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小谭坐在医院的病房里,鼻子上贴着纱布,张元从门外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很难找到焦点所在,几乎一切都是模糊的,从小谭的眼睛到到插在鼻子里的管子。张元说:“当时这个男孩子的眼睛像猫一样,我觉得很……怎么说呢,就按下了快门。”
这个男孩的入选,让我们对“有种”一词有了新的看法。张元选择的并不是表面上充满愤怒感的群体,而是内心里为追寻某种不可达到的愿望而不停跋涉的人生。他称之为“有种的人生”。
漫长的发布会上,张元占用的时间很少,他慢慢的讲完小谭的故事,回答了一个提问,就结束了自己的部分,接下来马来西亚籍的华人艺术家开始用英文讲述自己的装置艺术,而春季展览系列的另一位黑人艺术家还未到场。张元在蹩脚的英文讲述中歪着头睡着了,他十多分钟后,黑人艺术家戴着墨镜端着红酒走进来,对着他座位旁沉沉睡去的张元有些错愕,身旁的尤伦斯馆长杰罗姆桑斯稍显尴尬,摇醒了他,台下的记者们都忍住了笑声。
随性至此,也算是挺有种的。
- 刘香成:用镜头记录历史 2010-03-08
- 政协委员谈春晚:媒体把农民品味想得太低 2010-03-04
- 《觉》音乐+艺术 2010-03-03
- 接下来,请欣赏…… 2010-01-26
- 廖伟棠:用摄影摸索灵魂 2010-01-19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