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炖边角的八卦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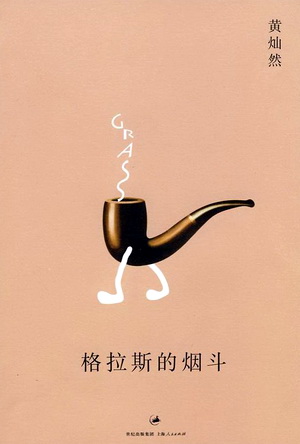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丁杨 翻开黄灿然的 《格拉斯的烟斗》最初几页,忍不住想起黄集伟的“语词笔记”或“读书笔记”们。“二黄”都是任万千语词、资讯过眼而深知取哪瓢饮的有心人,他们的角度和取舍在信息海量到令人窒息的当下算是难得。哪怕阅读这样私人化的事,偶尔借助“二黄”这样的慧眼,也没什么不好。
《烟斗》里的文章大多只占一页篇幅,偶有两页甚或三页的,显见是港报专栏的标准字数。用这么短的篇幅,完成引文、缘起、解读、评价、调侃等任务,还要筋道,还要不那么水,其实相当考验作者的新闻敏感与表达、思辨能力。我未认真统计,但大略觉得《烟斗》中话题发端,多自西书、外刊而来;当然,黄灿然对港台、内地的“阅读”也相当不薄。他庞大而驳杂的阅读量在这些小文里清晰可见。每篇文章缘起各异,读书阅报上网都能带给他灵感,再风雅的文坛也有笑料,再端庄的大作家也难免鸡零狗碎,这些“边角料”在他看来自是最有滋味最堪咀嚼的美味。
书中我最有共鸣的并非关乎作家、作品、文事、八卦的章节,而是《心里有一本书?》。文中说美国有个民意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内心怀揣一本书,而且值得写出来。我不知道在基本生存状况上仍然操心的中国人有多少想写本书的,起码在我的交往范围,多是写字为生(我并不认为这和真正的“作家”有什么关系)的朋友,认真也好玩笑也罢,一部分人前赴后继地出了书,另一部分也未必不觉得自己有本书始终委屈在心里、电脑里。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写一本书,尤其是当很多真正写了些书的人实际上心里并没有一本书——至少没有一本别人会在乎的书的时候?”黄灿然这样问,美国散文家爱泼斯坦这样答,“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写一本书,其背后原因是三流书实在太多了。因此,从不远处看,写一本书似乎是件挺容易的事。毕竟,当我们读了一本坏小说之后,不知多少次想过:我也可以写得这么好。令人悲哀的事实是,我们真可以写得这么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