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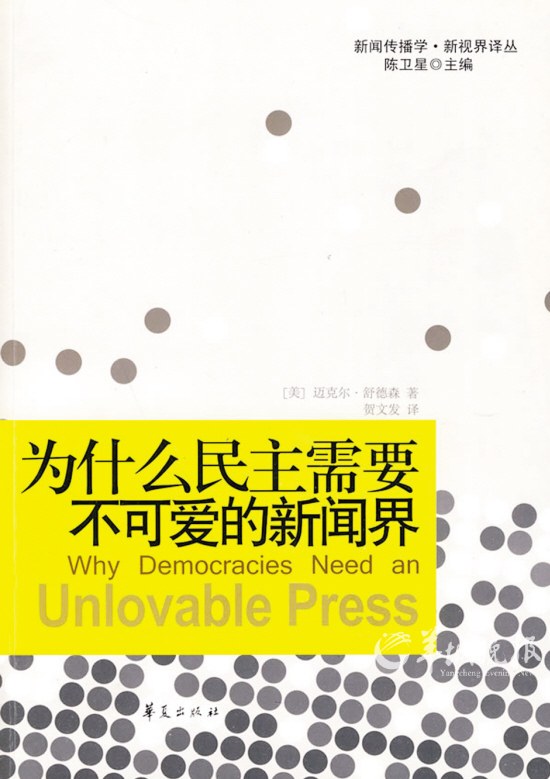
我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爱与其说是出于它的善举,不如说是考虑到因它而被禁止的恶行。
——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记者是“不可爱”的
记者职业的危险本质上来自于其天性。用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舒德森的话说,新闻业是“不可爱”的。
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舒德森归纳了时下美国对于新闻界“不可爱”的各种批评声音。这些“不可爱”包括,“对事件关注的顶礼膜拜、一种病态的近乎如体育迷一样对于格斗式辩论的迷恋、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政治警惕与反抗的愤世嫉俗,以及对于他们所报道的团体与社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疏离。”
不过,逐一分析这些批评之后,舒德森指出,正是新闻业的这些“不可爱”的特征而非其他特征,使得新闻成为“民主社会中一支有价值的力量”。
但我以为,新闻业更本质的“不可爱”并非迈克尔·舒德森所概括的那些,而是伦敦《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所形容的记者所应扮演的“盲流和不法之徒”的角色所带来的。
古希腊本没有什么新闻业的存在,大秦帝国也不曾有过记者的行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闻业的出现只是相当晚近的事。可它一经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便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轨迹。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包围着我们,笼罩着我们。
它是我们获取信息做出决策的基础,是我们了解他人沟通交流的渠道,是我们发表意见评论时事的平台;它是客厅咖啡屋里的谈资,也是一些内阁会议的决策推动力;有人为荣登一篇报道而欣喜若狂,也有人为一篇批评言论暴跳如雷;为了成为新闻的主角,有人不惜金钱与尊严拉拢记者,也有人为了避免丑闻而不择手段……一句话,我们的生活与新闻是如此地紧密相关,以至于无法想象没有新闻的生活。
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美国宪法首席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将新闻的最高职责简单而贴切地概括为:让民众知晓政府的所作所为。
麦迪逊说,在一个共和制国家,民众才是最终的主权者,他们有权“获得政府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全部信息——公共意见的交流与传播乃是遏制腐败的最有力途径。”因此,媒体必须能够自由地“彻查公众人物的品行和作为”。
但从本质上来说,新闻业的职责既非某个新闻从业者如伯纳德·莱文的自我痴想,亦非詹姆斯·麦迪逊的凛然钦命,而是社会安全运行的内在要求。
迈克尔·舒德森在开篇就指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任何制度,如果缺失了对自身的监督、批评与修正的话,这样的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对之忠贞不二;反之,那些能够真正对自身进行监督、批评与修正的制度则值得我们赞成与拥护。因为“在对抗力量缺失的情况下,所有的人类组织都可能退化为乡村俱乐部和兄弟会。毫无约束的话,‘书生共和国’将变为‘铁哥们共和国’。”无论情愿与否,媒体,最终被历史推到了这一制度性对抗力量、权力制约者的位置。当然,新闻业不是唯一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其他还包括法院、大学。
更直白地说,民众需要“看门狗”来保障他们的知情权,他们选择了媒体来承担这个角色。但对权势阶层而言,媒体就不是“看门狗”,而是牛虻了——难以想象牛虻会是“可爱”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麦迪逊是个倡导出版自由的浪漫主义者。他在1799年写道,“当媒体对政府滥权加以监督时,世界应该为理性与人道最终战胜了谬误与压制而感到庆幸。”只是,媒体要做到如麦迪逊所说的“让民众知晓政府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可以浪漫以对,至于对“政府滥权加以监督”,简直就是在玩儿命。
因为政府不是简单开放的,不会主动向记者展示自己;相反,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被隐藏在种种隐晦的结构和系统中,甚至可能会被故意隐藏起来。虽然对权力不加约束的诱惑永恒存在,但官员们几乎从来不承认自己滥用权力,他们总是坚决对抗与抵制新闻业对其进行的调查与探究,媒体——通常是惟一能为遏制权力滥用而战的斗士——不可避免地会与权力迎面相撞,也就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舒德森说,这样的执业生态意味着,新闻记者需要学会容忍和承受高分贝的噪音、大嗓门、举拳相向的愤怒、严重违法和道德败坏的辞令与巧辩、蛮横无耻与肆无忌惮的言语修辞,要学会掌控和驾驭竞争、对立与敌对的政治做秀,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欺骗、欺诈与阴谋诡计。
“这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东西。”他说,“政治是肮脏的,而政治报道就是要直面这些肮脏的东西,并且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恐惧感。”
想来,能合格扮演这种角色的,只能是伯纳德·莱文所说的那种“盲流和不法之徒”了。因为只有这种角色“方能保持对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的忠诚,探求其他人无法接近的真知,发出其他人发不出的声音”。也因为这种角色,决定了“媒体根本没有义务对官方负责,倘若有一天它们必须承担这种责任时,那只能是自由的灾难”。
身为记者的凶险
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处于危险之中——社会需要媒体扮演权力制约者的角色,与记者切实扮演起这一角色之间存在着难以轻松逾越的鸿沟。只有当新闻业与记者如实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让权势人物如芒在背的时候,他们才会招致权力的记恨与打压。
很遗憾,相当一部分国家和新闻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能承担起牛虻的责任。早期的新闻业自身并未意识到或者说并不准备扮演这一角色,而几乎无不是资本的吹鼓手、政治的扛轿夫。
以今天新闻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从舒德森呈现出来的美国新闻史中可以看到,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各大报纸都没有派驻各地的记者,最初华盛顿的记者都同时为六七家甚至更多报纸写稿子,这些人同时是国会议员的办事员或是政治人物的演讲撰稿人,记者的兼职是为补贴工资收入。
新闻与政治的职业领域在当时没有什么差异,编辑记者从属于政治党派,也常常追随他们的政治赞助人入仕为官,参与政治分红。同时,联邦政府和主要党派也是报纸广告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城镇,办报也不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沟通信息,而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聚集人气的手段。
统治者也深知新闻业如果成为对抗性力量将会有多危险,差不多所有的专制主义者都试图压制新闻界的独立言论。压制的惯用手法,一是事先限制,即对所有新闻出版物的许可证制度;二是事后追惩,一旦新闻记者出现一点瑕疵、失误或错误,就会被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严惩不贷。
不要抱怨新闻业的失职,更不要鄙视记者的胆怯。贫瘠的土地上无法开出艳丽的花朵,记者大展拳脚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土壤——请注意,麦迪逊在概括新闻的职责时,逻辑的起点是“在一个共和制国家”。
作为一种职业,记者要想扮演权力制约者的角色,要想使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士感到恐惧、焦虑和有所敬畏,其前提是:政府机关里的人相信总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一直密切关注着新闻报道,而在公众面前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会引发公众的争辩和怀疑,从而降低政府在公众中的权威。
这又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在意自身在公众中的权威的。
专治统治之下,统治者不会容忍任何对抗性力量的存在,其控制一切的强大力量足以彻底封杀新闻业的任何声音,把媒体变成任自己摆布的传声机、应声虫;或者根本漠视新闻界的一切声音——无论是多么令人震惊的黑幕揭露还是多么尖锐犀利的批评抗议,他们只要公众害怕他们而不敢反抗就行,了解再多的真相都无所谓。
20世纪80年代的智利、弗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都选择了后者——漠视,但更多的独裁政权选择了前者——封杀。不是因为封杀更简单、更容易,而是因为更能让极权统治者享受到权力无所不能的快感,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强势压制下的恐惧。
对于从专治向民主转型的社会而言,新闻业的处境要复杂凶险的多。在道义上,至少是在名义上,当局固然宣称政府需要新闻业的监督、需要舆论喉舌。这些宣示无疑会激起一些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激情,可当他们一旦付诸行动,他们便发现自己面临的禁忌与危险无处不在,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里,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警示就受到迎面而来的公权力的敌意与打压。
只有在民主的语境下,因为权力只是暂时授予的,才可以接受约束和问责,政府才会在乎其在民众中的威信和声誉,新闻业所扮演的监督者角色也才会被认可,“不可爱”的记者也才可以大展拳脚。
当然,这并不是说记者从此就安全了,他们仍然会遭遇当局的各种刁难、陷害与抱负,但因为新闻作为一种制度性制约者的角色被接受,加诸记者的制度性危险——主要是各种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法律,这是新闻人的梦靥——渐渐消失,至少在道义上会遭到唾弃。因此,记者虽然仍不乏安全之虞,但已可循确定的司法程序解决,而不至于陷入无边的凶险莫测之中无法自拔。
从这个意义上讲,著名新闻学学者詹姆斯·凯瑞说地不错:新闻业不曾创造出民主,但不在民主的逻辑和理论下践行新闻业是不可思议的。
或许正是因为深知媒体这种地位的来之不易,政治学大师托克维尔纵声高呼,“如果我们以为报纸仅仅确保了自由,那我们就低估了新闻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维持的是文明”。
中国的记者更不安全?
回到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中国新闻记者的从业环境。
睽诸近年来的中国新闻界,记者们的表现有声有色,令人肃然起敬:孙志刚之死的报道将一部恶法送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黑砖窑雇佣智障工人的披露让这个国家获得了人道底线的共识,三聚氰胺奶粉的曝光使众多的年幼生命免遭荼毒,邓玉娇案中的穷追不舍让一个弱女子幸免于司法不公的伤害……依靠文字的力量、依靠真相的力量,记者们“拯救”了这些身处困境的人们。
不过,就在为此而津津乐道之时,总有一片阴云挥之不去:对记者安全的威胁和加害。
一个省级高官可以在万众瞩目的“两会”期间于人民大会堂抢夺记者录音笔的国家,阻挠采访、殴打记者已不足以让人惊讶,罗织构陷罪名、打击报复记者亦不罕见,但当辽宁西丰警察捧着县委书记手令公然进京抓记者、当浙江遂昌警方违法全国通缉记者的时候,人们仍不得不震惊于公权力竞肆无忌惮至此!在牢狱之灾的恐吓面前,记者——这个曾经的“拯救者”——除了躲藏,别无他法。
那么中国的记者面临的危险是不是更多?
也不一定,要看是什么样的记者。狐假官威的记者可以备受礼遇、风光无限地走州过府;以牛虻自励的记者则被视为水火——“防火防盗防记者”之说在“天朝”广为流传。但整体而言,新闻作为一个行业的存在,在中国并会获得应有的权利保障。
在法律上,80年代初还曾有人呼吁过出台一部《新闻法》,20多年过去了,不仅这部法律至今踪影杳然,更连呼吁都已销声匿迹。在体制上,所有的新闻机构都不得不低三下四的为自己找个“主管主办”单位,被迫把自己弄成既非政府机构又非市场主体的怪胎。在微观操作上,“舆论导向”、“新闻纪律”让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看起来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
总之,媒体能在新闻理想的道路上走多远,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更依赖于其所获得的政治宽容。无疑,这是一个讽刺,更是一个死结:新闻业所要监督的是官方,但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却取决于官方是否足够宽容。
归根结底,中国新闻业的困境在于当局并不希望有外在于自身的力量存在。在这种逻辑下,新闻业不仅是“不可爱”的,更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戒心而拒绝给予新闻业明确权利保障的后果是,不仅使新闻记者在公权力面前不堪一击——根本用不着起诉,一个电话、一个批示、一个招呼就可以让他们丢掉饭碗,像公然通缉拘捕记者这种做法只有愚蠢至极的官员才干的出来——无法成为公众的“看门狗”;也使任何一种强势力量——资本、名人,都可以视记者如寇仇草芥,甚至连烟柳之徒都不及!对付记者,更是不择手段,毫无顾忌。这简直让一个文明的国度蒙羞!
其实,大可不必对新闻业戒心重重,更不用恐惧。中国向以历史源远流长著称,如果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新闻史就会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对新闻业戒心重重的迷雾中走出来转而捍卫新闻自由的,新闻的开放不仅未使一个国家崩溃,反而使它们变得更稳定更安全。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斯图尔特大法官写道:“媒体在国家安全领域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一领域,通常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很难实施,国会和法院往往会偏袒总统。因此,对政府政策和权力惟一有效的限制……也许就依赖于一个开明的公民社会……没有自由而开放的新闻界,就没有开明的民众。”
如果我们期待出现中国的《纽约时报》、中国的CNN,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给予记者权利保障、给予社会言论自由。毕竟,螺蛳壳里带着镣铐的舞蹈是不会精彩的;如若精彩,余韵也会让人感到悲哀。
- 当天津再遇达沃斯 2010-09-11
- 2010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闻发布会 2010-09-10
- 谁是不可爱的人 2010-09-06
- 凯旋先驱:数字媒体成为公关行业重要工具 2010-09-01
- 文化中国转亏为盈 觊觎无线新媒体业务 2010-08-31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