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0-12-14 15:2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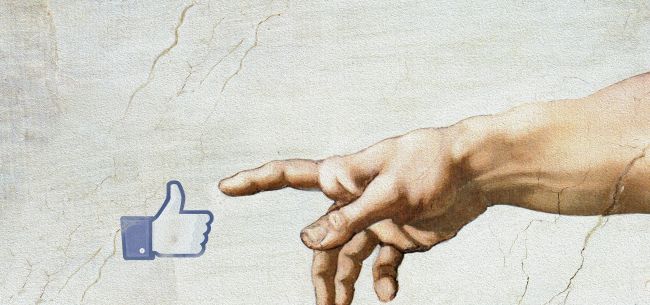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超级平台】
陈永伟/文
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正式对脸书提起诉讼,对其指控之一即猎杀式并购——通过2012年收购Instagram与2014年收购WhatsApp,消灭竞争威胁,巩固垄断地位。这是今年美国第二大反垄断案,仅次于不久前的美国司法部诉谷歌案。
在业界,脸书对创业企业的收购素以彪悍著称,一旦发现潜在对手,就毫不犹豫地通过收购来消灭。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这种收购,才导致了脸书今天的垄断地位。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很多人对于大型科技企业收购创业企业的行为颇有微词,认为应该禁止这种收购,或者至少大幅提升这种收购的审核标准。
大型科技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购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应该对其抱有怎样的态度?不妨就从脸书说起吧。
收购、复制和扼杀
在坊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扎克伯格是克里斯坦森理论最忠实的信徒。我们知道,克里斯坦森(ClaytonChris-tensen)教授是著名的“创新者的窘境”理论的提出者。根据他的理论,对于市场上在位的那些大企业来说,最为可怕的威胁是那些进行“颠覆性创新”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产品往往在边缘市场进行突破,大企业在开始时甚至不会感受到它们的威胁。这种发生在边缘领域的创新很有可能会出现高速成长,最终演变成一股革命性的力量。等到大企业反应过来,往往就为时已晚了。
尽管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扎克伯格和克里斯坦森教授曾对于“颠覆性创新”理论有过直接的交流,但从扎克伯格的竞争策略上看,他确实对这套理论非常重视。事实上,自从脸书成为了社交媒体领域的巨头之后,扎克伯格就一直十分提防边缘领域的创新,生怕那些并不起眼的小企业会迅速成长起来颠覆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他对于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防御策略。
大致上,脸书的这套防御策略可以概括为“收购、复制和扼杀”(Acquire,Copy,orKill)。具体来说,脸书一直花费很大的精力监控潜在的竞争对手,一旦发现某个新兴的企业会在未来对其造成潜在威胁,会立即尝试对这个企业进行收购。当然,一些新创企业可能会拒绝脸书的收购。为了对付这部分对手,脸书会尝试开发与对手功能类似的应用,与其展开竞争。由于脸书掌握了强大的社交网络,在应用的推广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多数的新生企业难以和其展开有效的竞争,最终,要么被脸书收购,要么就在竞争中失败。对于这种策略,扎克伯格本人毫不讳言。在2012年的一封内部邮件中,扎克伯格就明确指出,脸书必须确保对潜在竞争对手功能的“克隆”和对其本身的并购,以此“确保脸书本身有更多的用户,同时不让竞争对手站稳脚跟”。
根据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从2004年成立至今,脸书至少收购了63家企业。纵观这些收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不是以单纯的盈利,或者弥补自己在业务上的不足为出发点,而是以消灭潜在对手,将潜在的竞争扼杀在摇篮当中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很多收购当中,脸书甚至愿意承担远高于市场估值的价格,而在并购后,则会容忍并购对象在较长时间内的亏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脸书对Insta-gram的收购。Instagram成立于2010年,其主要业务是向用户提供一款能够以快速、美妙和有趣的方式分享图片的应用。在被脸书盯上时,Instagram其实只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公司。但是,这家小公司的一个特点让脸书感到了恐慌,那就是其迅速的成长速度。
面对这样一个暂时还很弱小的对手,扎克伯格嗅到了威胁。在一次内部会上,他向自己的属下表示:“Instagram的快速成长很令人不安。它很有冲劲,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后患无穷。”为了消灭Instagram的威胁,脸书方面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方面,它启动了一款与In-stagram功能类似的竞品 FacebookCamera的开发;另一方面,它开始了与Instagram的接触,讨论可能的收购事宜。
扎克伯格在发给Instagram公司CEO凯文·斯特罗姆(KevinSystrom)的邮件中,多次向他提到了FacebookCamera,并向其暗示,这款应用的功能和Instagram十分类似,如果Instagram方面拒绝收购,这款应用将与Insta-gram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面对来自脸书这样一家巨头的压力,斯特罗姆胆怯了,他感觉一旦冲突正面展开,成立不到两年的Instagram很难是财雄势大的脸书的对手,这让他不得不考虑脸书提出的收购提议——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如果当时脸书方面没有着手Face-bookCamera的开发,那么他很可能会拒绝扎克伯格,继续独立运营Insta-gram。当斯特罗姆开始动摇时,扎克伯格抓住机会,开出了一个让斯特罗姆难以拒绝的价格——10亿美元。面对这样一个在当时市场上不可思议的高价,斯特罗姆彻底屈服了。就这样,一款本来可能挑战脸书在社交领域霸权的产品,就此成为了脸书的一部分。
在收购Instagram之后,这种以复制和扼杀作为“大棒”,以高收购价格作为“胡萝卜”的收购方式就成了脸书打压潜在竞争对手的标准做法。例如,在2013年的时候,脸书发现社交应用Snapchat的成长十分迅速,可能会对脸书造成威胁,于是就想故技重施,对Snapchat进行收购。然而,Snapchat对脸书抛来的橄榄枝反应冷淡,拒绝了其开出的30亿美元的报价。在遭到拒绝后,脸书直接仿照Snapchat最受欢迎的SnapchatStories功能,在旗下的Instagram上推出了Insta-gramStories。虽然由于Snapchat本身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一功能的推出并没能完全扼杀Snapchat,但它确实对Snapchat的市场份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其他企业,脸书在识别、确定潜在的竞争对手时,更多采用了一种“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模式,十分重视大数据起到的辅助作用。
2013年的时候,脸书花费1.2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以色列的移动应用分析公司Onavo。根据脸书的官方说法,进行这一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发起的互联网普及计划Internet.org提供支持,因为Onavo公司的VPN产品可以帮助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用户获得更为便捷、流畅的上网体验。但是,当时就有很多分析指出,脸书收购Onavo的目的并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么冠冕堂皇。事实上,对于脸书来说,它更感兴趣的是Onavo的两个功能:“Count”和“Extent”。从设计初衷来看,这两个功能是帮助用户优化自己的手机资源配置,但在完成这一目标的同时,它们也可以获取和记录用户对手机内所有应用的下载和使用状况。这意味着,一旦脸书收购了Onavo,它就可以通过这两款应用,完整地获得这些信息。
根据一封脸书内部信件披露的信息,当时脸书决策层认为,这些信息将可以被用来帮助“加强对用户行为和市场趋势的相关分析,并通过这些数据来提升对目标受众的广告效果”,但很快,脸书方面发现了这些数据还可以有另一个功能——识别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完成了对Onavo的收购之后,脸书方面很快利用其提供的非公开实时数据构建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earlybirdwarningsystem),据此来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进行识别和评分,并采用收购、模仿、扼杀等方法对威胁最大的对手进行对抗。
这套早期预警系统最成功的一次应用可能是2014年脸书对WhatsApp的收购。当时,市场上与WhatsApp功能类似的应用有很多,要识别哪一个会对脸书构成潜在威胁并不容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脸书借助自己的早期预警系统对所有月活量在9000万以上的移动应用都进行了分析,最终锁定了WhatsApp为头号威胁,并果断对其进行了收购。
2018年,苹果以Onavo非法搜集和使用用户数据为名,下架了这一应用。为了对这一系统进行弥补,脸书又在今年5月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在线动图搜索引擎Giphy。这一搜索引擎可以允许用户进行动图的跨应用搜索,因而可以帮助脸书监控各社交软件的活跃状况,以及内部信息的交流情况。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购入了Giphy之后,脸书将可以有效地修复自己的早期预警系统,继续为自己的数据驱动型收购策略提供有力支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脸书之所以可以在社交领域获得如此持久的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坐拥数十亿用户,这套“数据驱动的”收购、复制和扼杀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脸书没有对手?答案很简单:在那些对手成长起来之前,它们早就已经被脸书消灭了!
大型科技企业并购的影响究竟何在
虽然脸书用并购来防止竞争的做法过于彪悍,让很多人感到不适,但在如今的市场上,这并非是个例。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型科技企业采用了和脸书类似的做法——为了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超越自己,就在它还没有成长起来前就将其收购。
围绕着这种类型的收购,现在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类收购可能会对市场的竞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并购的反垄断审查时就应该予以禁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类型的收购其实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不必大惊小怪。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方面有道理呢?在作出具体的判断之前,我们不妨将这类并购潜在的负面影响列出来,然后一一对其进行考察,看看哪些影响更可能发生,哪些影响相对来说难以发生。
在传统的反垄断实践中,对一项并购的评估主要会考察两个方面:并购的单边效应(unilateraleffects)和协同效应(coordinatedeffects)。其中,单边效应指的是由于并购后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减少了,因此企业可以拥有更强的市场力量,从而将价格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对消费者福利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协同效应指的则是随着市场上竞争者的减少,剩余的企业之间更容易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谋,从而对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两个影响中,单边效应的考察通常会多一些。在分析大型科技企业的并购时,这两个影响当然也会继续被考虑,但总体来说,它们在判断并购合理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一方面,由于大型科技企业通常采用平台模式,其提供的服务有时会采用免费模式,因此单边效应通常很难被测定;另一方面,平台模式的采用也导致了市场的高集中,而在原本就“一家独大”的市场上去讨论协同效应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相比于这两个传统因素,现在的人们更关心的是几个问题:一是这种类型的收购会不会扭曲市场上的竞争,导致创新和创业被抑制;二是并购后,企业会不会利用被收购方的数据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力量,从而对市场产生进一步的损害。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逐一进行考察。
大型科技企业的并购一定会破坏创新创业吗
先看对创新和创业的影响。总体来说,这种影响可能通过三个机制发生:第一个机制是所谓的“猎杀式收购”(killer acquisition),即发起并购的企业在并购发生后,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能搁置被并购企业正在进行研发的项目,甚至雪藏其已经取得的成果,这可能会影响市场上新产品的推出。第二个机制则是,当预计到自己的创业成果会被大型科技企业收购,创业者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第三个机制则是,大型科技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购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对于新创企业的信心,导致新创企业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融资,从而间接对创新和创业造成扼杀。那么这三个影响是否成立呢?在我个人看来,类似的影响固然可能存在,但在具体的个案中,它们却未必一定会发生。
首先,类似并购未必就会产生“猎杀”的后果。关于大企业的“猎杀式收购”的讨论最早来自于制药企业。有三位经济学家曾在经济学界的顶尖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们对制药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制药行业的并购中,至少有5.3%会产生所谓的“猎杀”后果,也就是被并购企业的研发项目会在并购后被搁置,已有的研究成果则被雪藏。这种现象更多会发生在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存在业务竞争的环节——如果发动并购的一方已经在市场上推广了某种药物,那么被并购方与该药物存在竞争的研发将会被暂停。很显然,这种效果的存在会对药品市场上的创新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会对人们的健康构成潜在的损害。
但是,这种推论能否直接被移植到数字经济领域呢?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在市场特点上,数字经济和制药行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总体上看,制药行业的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是比较硬核的。这些创新的投入巨大,而一旦企业获得了创新上的突破,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方式来对这些创新进行保护。此外,在制药行业,进入资质非常高,因此企业对于竞争对手的识别是容易的,即使发现了竞争对手,它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所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制药行业,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去维护一种旧有的产品,也有能力去雪藏一件既有的创新。
而数字经济领域则完全不同。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要是模式创新。举例来说,无论是Snapchat还是What-sApp,从技术上讲,它们都不难实现,只要知道了它们的模式,像脸书这些企业很快就可以仿制一款与之十分类似的产品。相比于制药企业的硬技术,这些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它们的模式本身,以及通过这些成功的模式迅速积累起来的用户规模和数据。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们即使被大型科技企业收购了,后者也不可能将它们雪藏或者消灭。恰恰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创业团队本身不愿意解散,那么收购方通常会整体保留这个团队,并且还会对其投入更多的资源,确保他们的运作和研发。例如,脸书在并购了Instagram之后,就基本保留了Instagram的团队,并给予了他们较多的自主性和很多的资源。这些支持都保证了Insta-gram虽然被收购,但其服务并不会因为收购而消失,事实上,它还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品牌存在于市场上。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着眼于整个市场,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并购发生的前后可能并不会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对于产品的用户体验还可能在并购发生后得到改善。
退一步讲,如果某个创业企业的服务真的在并购发生后被消灭了,那只要这个服务本身是有价值的,市场上出现一个类似的模仿者也是很容易的,这一点和制药市场有着十分本质的区别。
其次,类似并购对于创业信心的影响可能是两面的,应该综合加以考虑。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他们投入创业的目标是不同的:一些创业者对待自己的事业是秉承“养孩子”的心态。对于他们来讲,自己的产品就是一切,即使有人愿意出很高的价格也不愿意将它们出售。但另一些创业者对自己的事业所抱的则是一种“养猪”的心态。对于他们来讲,能在较短时间内做成一个产品,然后套现退出就是目的,对于项目本身他们并没有特殊的感情。这里需要多说的一句是,“养猪”的企业家未必就是没有责任心。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有更高的追求。例如,马斯克在起家时,如果不是果断选择将自己创建的X.com与PayPal合并,又在合适时刻出手了PayPal,那么他很可能就没有机会创办后来的特斯拉,更没有机会去着手探索星辰大海。
很显然,对于这两种企业家,大型科技企业的并购所造成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对于那些视企业为孩子的企业家,这样的收购无疑是横刀夺爱,会对其创业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但对于那些视企业为猪的企业家,被收购本身或许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大型科技企业的收购可能会打击一些企业家的创业热情,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激发另一些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而从动态的角度看,两种效应中,后一种可能是更占优势的。
再次,类似收购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这种收购的出现可能会加快投资者资金获取回报的时间,从而增加他们对初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的目标主要是获得收益,实现变现,至于这种变现是通过上市还是其他的方式,他们并不会特别的在乎。当存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收购时,很多的创业企业事实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退出渠道,这使得投资者变现变得更为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会更倾向于对有价值的新创企业进行投资,给它们以更多的扶持。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大型科技企业本身事实上也扮演了投资者的作用。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些大型科技企业本身完全有实力去探索很多新业务,但在实践当中它们更愿意发挥创业者的积极性,把这些业务交给新创企业去做,自己则主要通过财务投资来进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收购的存在事实上保证了大型科技企业的投资热情,让它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扶持新创企业——毕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给自己做事。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大型科技企业对新创企业的并购,既有可能对创新创业产生阻碍,也可能对其产生促进。笼统地说其影响究竟是好是坏并不可取,相比之下,对于每一个个案,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恐怕是更为可取的。
如何看待并购所引发的数据垄断
人们对于大型科技企业并购的另一个忧虑是源于其对数据的控制的。在脸书的案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影响。例如,脸书对于Onavo的收购,让其具有了更好监控对手的能力,使得其“数据驱动”的并购策略成为了可能。再如,最近脸书试图打通Instagram、WhatsAPP等的底层数据,以求综合利用其数据优势来提升自身广告效率的尝试,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一些人认为,为了避免大型科技企业通过并购来实现数据垄断,应该对这些并购予以阻止。
不可否认,以上的忧虑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是否由于这些忧虑,就要对大型企业的并购采取过于严格的态度,这一点却很值得商榷。
一方面,脸书借助Onavo来监控对手,从而对对手实行有针对性的打击确实有可能对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策略的实现其实未必需要对Onavo进行并购。事实上,市场上存在大量的第三方咨询机构,都对各种应用的下载和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因此,即使脸书不收购Onavo,它也可以借助于这些机构来了解对手的动态。或者更为直接的,它还可以通过与Onavo有类似业务的公司签订一个合同,委托它们为自己提供报告,这样完全可以在未实行并购的情况下获得同样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试图以提高并购的门槛来达到仿制大型科技企业从事数据驱动的竞争行为,其实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脸书打通Instagram和WhatsApp底层数据的尝试确实有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在理论上还有很大的争议。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脸书尝试打通Instagram和WhatsApp底层数据的时候,事实上距离对他们的并购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打通其实更类似于脸书将内部业务的数据进行打通,通过加强对于并购的限制来阻碍企业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很难办到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脸书凭借其并购所得的企业的数据扩展了自身的市场力量,并采取了相应的反竞争行为,但这些负面效应其实很难通过事先的并购控制来实现。针对这一问题,与其在事先通过抬高门槛来抑制各种负面影响的产生,倒不如采用一些对事后的管控。例如,在企业进行并购时,规定其在一段时期内不准将被并购对象的数据与自己已有的数据打通。或许通过这样的办法,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发挥并购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尽可能抑制其负面后果。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