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眼中的中国 严翔中/文
于是世界似乎从那些书页中流出
像黎明时在田野上消散的雾。
只有当两个时代,两种形式被
连结在一起,它们的易读性
被扰乱,你才能看到不朽
和当下并没有什么不同。
——米沃什《一本废墟里的书》
总之,两个问题:
审查和压抑能指。
权力的存在方式、性质和场所。
——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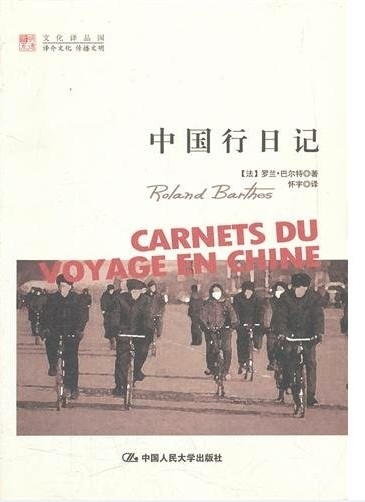
《中国行日记》
[法]罗兰·巴尔特/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历史,是片面的,即使它为自己做了辩解,也仍是片面的,它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片面性。作为80后,经历成长中种种价值幻灭与观念更替,像许多朋友一样,我努力在各种断裂的叙述中寻找一个支点,信仰(或者幻想)这个支点可以厘清当下的价值颠乱,实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让我们可以更加完整而平稳地看待自我和生活。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在玩一种拼图游戏,游戏者从一开始就相信答案就在拼图完成时展现。
随着阅读和经验的深入,我开始明白,要放弃企图将各种碎片放进同一个图框的做法,因为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经验世界:每个人谈论的文革和改革开放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它们的相似性只在日期中,某个确定记载的日期就是历史。历史像一幅油画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和笔触,成为一张黑白印刷品。只有回到一个个日期,才能从旁观者的眼中看到景观、细节、身体、话语以及行动和它掩盖的动机。
1974年4月11日,罗兰·巴特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索莱尔斯以及他大名鼎鼎的妻子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四人,时值“批林批孔”热潮,五人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等城市,参观了各地的重点景物、历史古迹以及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工厂。
作为法国公认的继蒙田之后的散文大师,巴特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简洁而鲜明地记录下来,形成了蓝色圆珠笔和碳素笔写下的三本中国行日记,这些文字配合安东尼奥尼的影像,还原出一个70年代的中国。
动身前,巴特打算塑造一个多重意义的中国,“抽象地讲,中国有着无数可能的意义:历史概念的意义、伦理概念的意义,等等。但是,在法国人看来,中国只有一个意义。”但是下飞机后,巴特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我不禁回想起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天安门广场,
北京,五月的一天,
今天我们开始了短暂的中国之行,
把电影机对向这里,
中国的人民就是这部片子的明星,
我们不企望解释中国,
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
从欧洲到达时,我们期待着爬山和跨越沙漠,
但很大一部分中国是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
虽然中国人打开了几扇门户,玩起了政治乒乓。
我们笑眯眯的导游,让我们跟随他们严格规定的路线……
同样是规定路线的游览,巴特一路感慨,在中国,连发型都是有规则的,“真让人印象深刻!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他进一步分析,服饰的完全一致所产生的趋变效果:“平静、清淡、并非粗俗,以废除色情为代价——爱美之荒芜”。
巴特多次怀疑,中国人的性欲是如何表达的?为什么人人都像在坐禅,清心寡欲。
“这是一种没有性器崇拜的文明吗?出生率高吗?”
“性欲,仍然是、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谜。”
“这种语言学并不属于索绪尔语言学系统。没有个人习惯用语。他们大概没有谈情说爱的和社会逻辑学方面的话语。”
“在这里,无任何色情。”
“我被剥夺的东西:咖啡,生菜沙拉,调情……我烦透了。”
短短几天里,巴特经历了旁听革命委员会报告,参观商店、家庭、学校。其中斟茶次数繁多,各负责人思维呆板、尤其善于背诵数字,“统计”关键词,“砖块”汇总,一切都充满了政治套话和辞不达意,在流露个人意识、情感的时候,俗套就立即跟随出现,“像是在掩盖自己”。观看表演时,法国代表团被围在中间,不能与无关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夜晚,巴特偏头痛发作,无法入眠与恶心。“难受、心灰、恐慌。对于这一点,我最终认为,它象征着对白天生活的完全拒绝,象征着对俗套的厌恶……整个政治话语就像一种精神投入对象、一种压抑对象”,让人变得顺从,个体完全被消解: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
在和医生的座谈中,巴特问到有没有心理层面的疾病。
医生回答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引发溃疡的心理疾病很少。通过唯物辩证法可以治愈?
那年轻人的性张力呢?
年轻人都引导到努力学习和工作方面去了。
婚前有无性自由呢?
性自由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年轻人不接受……
“没有任何偶遇事件、皱痕”,没有细微差别,巴特感到乏味至极。在中国,唯一的能指等于毛泽东的书法和大字报。最后巴特下了总结:
“绝对的政治集权制。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之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种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
巴特认为汉语是非常明确的,可以非常明确地表达人们的所思所想,但在当时,新颖性已经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到处都是不假思索就被接受的观念,强烈的、个人的思想只能在俗套的缝隙中才被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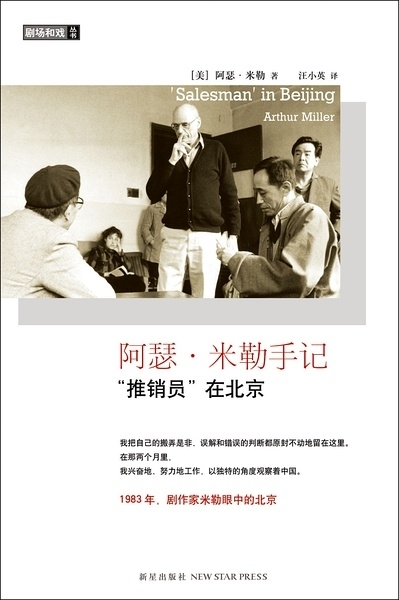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
[美]阿瑟·米勒/著
汪小英/译
新星出版社
2010年8月
巴特来到中国差不多1 0 年后,1983年3月21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第一次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那时他刚到中国,导演《推销员之死》,演员里只有一个人懂英语,剧本的形式和它所讲述的社会,对中国观众来说完全陌生,各种困难都让这次合作显得勉为其难。起初排练时,人艺的一位导演读过剧本,宣称演这样的戏完全没有可能。之后,好几位演员也坦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米勒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比夫坚决反对威利追求金钱,但这不是出于整齐划一的政治觉悟或社会要求,而是出于个人的经验和道德,换言之,米勒是在根植当时中国缺失的一种东西——个人意识,个人视角。一个人动辄心血来潮,不停地改换职业,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显然这已经成为当下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
米勒用爱、怜惜、幻想这些共通的情感和演员进行沟通。刚刚从文革极端平均主义中走出来的中国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想要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穿着跟这个城市一样灰暗,又让我想起这儿有多穷。我已经觉察到,中国急需发展经济,人们渴望得到很多东西——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物质上的发达和享受知道的越多,这种渴望就越强烈。”
离开中国时,米勒感慨:
“总之,中国的难解有一次浮现出来。我知道中国观众和西方观众会在同一个地方发笑,我看见了他们为威力流泪。也许,我的问题是多余的。也许,当中国人问这出戏发生的地点时,我应当仔细回答。既然他们不能化装成外国人,当这出戏发生在想象出来的地方——在那里的人有着中国人的面孔和黑直头发,他们的行为举止却如同另一个文明中的人。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我们曾经相遇,一起凭空造出了一座房子、一个家,一起挣扎求生。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的所有。”
米勒希望文化的作用是让人们品味文化核心的共通之处,而不是用来让人们捍卫自己的文化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他看到的中国要温和得多,街上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也许,谨慎已经成为生存的必须,融入到了人们的血液中。但是,毫无疑问,不少人仍然遵从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自己的现代交响乐极有情感,很多人也喜欢听莫扎特。总之,这里的人们似乎同时生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纪之中。”
观看30多年的中国历史,个人是在一点点被解放出来了。但我们依旧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分成很多群体,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纪中,空洞的政治话语再也不能把这些群体简单地团结起来。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认为有组织的生产最终会影响人们的存在和信仰,而中国恰恰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生产高度组织的时代——关键在于你做什么,而不在于你想什么,我们需要伫立、反思和冥想。
在纪录片《中国》的结尾,安东尼奥尼精辟地总结:
“中国在开放它的大门,
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
基本上不为人所知的国度。
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
古老的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米勒则用一种美国人特有的乐观说道:
“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
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