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14-04-29 13: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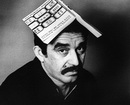
张伟劼/文
4月18日凌晨,我在广播里听到哥伦比亚大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病在墨西哥城去世的消息。随后播出的另一则消息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将于当天晚上在央视开播。大师离世和《舌尖》归来,成了那一天被重复最多的两条文化新闻。我不敢断定会有很多人在闻说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后争相点击鼠标下单购买《百年孤独》,但可以肯定的是,《舌尖II》的首播会吸引好多好多双眼球。
越来越多的图像充斥人们的业余时间,快速变换的画面取代印刷文字,似乎是时代的趋势。在今天,一部小说能不能畅销,与是否被改编成影视剧以及影视剧的成败与否密切相关。在视觉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所谓的“严肃文学”正经受着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尔克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自2011年第一次“合法”地在中国出版以来,在畅销书榜上一直名列前茅,仿佛成就了一个奇迹。那些为中国长久偏低的国民阅读率而担心的人们可以为此欣慰:毕竟,经典的魅力还在,“纯文学”还是有人看的。
我的书架上摆放着三本《百年孤独》。面目最苍老的一本是我在西班牙语专业读书时系里印制的阅读材料,土黄色的封面,简简单单地印着中西文书名和作者的西文姓名,书脊上的书名“CIEN AOS DE SOLEDAD”还是我自己用钢笔小心翼翼地描上去的。作为一本“非法”印制的西班牙语阅读教材,它又土又清纯,只是小说原文的全部内容,没有前言,没有后记,就像是用牛皮纸简单包装、不注商标也不留产品信息的绝味特色美食。书的第一页曾经脱落下来,我用透明胶带重新粘好。页面上遍布着圆珠笔做的标记:尽管行距很小,不少词语下面还是缩头缩脑地写着中文释义;一些动词的下面附有下划线;有十多个前置词被框上了梯形记号,不知是做句法分析用,还是为了探究前置词的用法……第一页之后,这些标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些记号并不是我做的。这本书来自于我在修读西语专业时一位进修生同学的馈赠,这位朋友为了从事外贸工作,从河北跑到南京来学西班牙语,为了学西班牙语,又苦心搜罗在那个时候所有可以买到的西语材料,其中就包括这本用十块钱购置的土制《百年孤独》。我是在完成西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习后开始读这本书的。老实说,文字不算很难,无须频仍查阅字典,再加上之前已看过该书的中译本,所以读起来感觉非常畅快。这本原文小说我读了两遍,算是实现了学习西语之初立下的梦想。刚入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西语文学中,有两本经典是不可不读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还记得在西班牙语课本第一册上,某一课的课后练习,有一题是看图说话。在其中一幅图里,简笔勾勒的书架上,就有一本“CIEN AOS DE SOLEDAD”——它似乎一直在召唤着我。
我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我第一次读到的《百年孤独》——它的众多非法中译本中的一本。封面上有一个异族装束的旅人,正坐着吹奏某种古老的乐器,背景是森林和几排蘑菇状的房屋顶,由下至上逐渐清晰地浮现在一层雾气中,仿佛童话里的场景。这本书是我的意外发现。在前电子商务时代,有时候寻找一本书如同打猎一般辛苦而有趣,常常有偶得的惊喜。对于当年的那个西语专业一年级学生来说,《百年孤独》是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读到它的原文本,然而因语言水平所限读不懂;都说它是一本伟大的书,可是因为版权问题,市场上已很难觅得曾经在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中译版,而图书馆里的收藏也往往是一回到书架就很快又被人抢走,只剩下一些有关《百年孤独》的研究专著或文学史著作可供借阅。出于一种并非源发自文学爱好,而是出于对所学专业必读书目的了解的需要,我便翻阅这些外围文本,了解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讲述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背景是在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叫“马孔多”的世外桃源,融合了西方现代派写作技法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传说,其结构与《圣经》相仿……然而无论如何,每回去泡书店,我总还希冀着能看到这本书。
我不曾想到,我会在自己的家乡,在那座江海之滨的小城里找到《百年孤独》。它是我在一个暑期打折书市上的截获。怀着对那个据说极为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期待,我翻开了这本盗版名著。多年以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试着以马尔克斯的方式描述那次相遇:“多年以后,重读这部经典时,或许我还会想起自己被这个‘非法’译本的第一句话引领入拉美文学殿堂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百年孤独》成了我的文学启蒙。在此之前,拜语文教育所赐,我所了解的外国文学要么是雨果、巴尔扎克,要么是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社会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我所认识的简单又模糊的信条。拉丁美洲和西语文学都是隐身在晦暗角落里的未知岛屿。《百年孤独》给我一种从未曾体验过的阅读快感:故事的魅力不在于揭露什么批判什么,而在于故事本身,这个尽出怪人的家族的历史让我欲罢不能。故事中所述的种种灵异现象,虽则不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却一直是自然科学致力于破解的谜团,而在睡梦中遇见故去的亲人,时而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巧合,难道不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吗?我并非未曾读到过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无论是以泥土为食的小女孩,还是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雨,或许都可以在某一版讲述奇闻异事的小报上读到,然而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如此集中地在故事中出现,而且有如被赋予了一种魔力,吸引着我从头读到尾,读到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尾:原来这个家族所有的历史都已被预言,记录在一份羊皮卷手稿中,为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所发现,他读完之时也就是故事发生的整个世界消逝之日。
初读《百年孤独》,伴随着我的是一种发现和探索新大陆的兴奋。在阅读小说前迷迷糊糊了解的那个叫做“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在大师扣人心弦的叙述中兑现了“魔幻”的承诺。所谓的文学经典,不再是严肃、深沉、一本正经的现实主义,而是对世间一切可能性的探险之旅,是想象之丰富有如物种繁多的热带雨林的魔幻小说!这样的小说,展现在我眼前的并非一个高于或低于现实生活的世界,而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小说中的这些人物,表现为一个个仿佛各自带着隐秘内心的孤独形象,既不崇高也谈不上可爱,算不得是代表了哪种典型性格,却以他们的荒诞、他们的疯狂令我回味良久。
我一边读着这并不算糟糕的译文,一边展开对那个遥远大陆的想像。记得那一阵我还迷恋夏奇拉,喜欢一遍遍地听这位性感歌星激情四射的西语歌曲专辑,用的是笨重的松下CD播放机,听的是在大学门口的小店里淘来的打孔光碟。马尔克斯和夏奇拉或许是一对奇怪的组合,尽管他们同是哥伦比亚人。但无论如何,在那个暑假里,他们的作品的的确确成为了我藉以想像哥伦比亚、想像拉丁美洲的仅有材料。在国内能看到的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献实在太少,《百年孤独》在我身上点燃的不仅有文学热情,也有求知欲——在哥伦比亚的海岸,真的留存着西班牙大帆船的残骸?在这个国家,真的有过一场让奥雷里亚诺·布恩地亚上校经历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的漫长内战?哥伦比亚女孩真的有如抓着床单升天飞走的俏姑娘雷麦黛丝那般漂亮吗……
我在阅读和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一步步走近真实的拉丁美洲。原来在拉美文学“爆炸”年代的尾声,有一位乌拉圭记者写出了一部记录拉丁美洲殖民历史的影响深远的著作——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读过这本书之后回看《百年孤独》,才知许多骇人听闻的情节是有所指涉的。小说就像一幅形象众多的寓意画,充满了隐喻,呼唤着读者去做用心的解读。我曾与哥伦比亚外教威廉·桑切斯共事一年,一起喝过啤酒也喝过他亲手煮制的哥伦比亚咖啡,听他阐述乔姆斯基是如何批判“帝国主义”的——这个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再被频频提起的名词,对于拉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仍是鲜活的、有现实意义的,是在《百年孤独》的故事里有具体而微的再现的。威廉还给我看过一部名为《俄狄浦斯市长》的哥伦比亚电影,影片把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搬到了现代哥伦比亚,以主人公弑父娶母的残酷命运批判这个国家长期内战的惨烈现实,而担任编剧的正是马尔克斯。原来《百年孤独》讲的都是真事。原来马尔克斯所说的“我的所有小说,没有一行文字不以真事为基础的”,并不应该在“他们视为真实的,在我们看来是魔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在去除了“魔幻”外衣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如果考虑到《百年孤独》诞生的背景,那个全世界都在轰轰烈烈闹“革命”的1960年代,那个拉丁美洲在火热激情中急切地寻找身份和自身命运之路的年代,《百年孤独》的现实意义就更为彰显了。
作为一个拉美文学的翻译者,我要感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我与拉美文学结缘,遗憾的是我从没有翻译过马尔克斯的书,倒是从翻译马尔克斯的好朋友——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开始,发表一部部译著的。我通过富恩特斯走近墨西哥,又通过在墨西哥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进一步了解《百年孤独》——半个世纪前,马尔克斯正是在这座城市开始创作这部巨著的。
墨西哥城,不管是好是坏,在那里生活过,你总难再忘掉它。这是一座充满矛盾冲突和强烈的对比、在巨大的张力中不断生长的城市。它耸立在时间仿佛停止流动的高原上,每一天都有可能被火山突然喷出的岩浆吞没,却集中了这片神奇土地上最丰富多彩的活动。它拥有拉丁美洲最现代化的建筑,也存放着年代最久远的文明遗产。尽管它堪称拉丁美洲最开放的城市,遍布外国品牌也吸纳国外流亡者,21世纪的市民们仍称它为“大农场”——这座曾在殖民时期管辖范围远达加利福尼亚的都城,毕竟不是纽约伦敦,“现代化”的承诺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兑现,一如波哥大、利马或是加拉加斯,一如拉丁美洲其他的大城市。在《百年孤独》里,马孔多的先民把手按在冰块上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的宣告,这一片段读来令人莞尔,却也是作者对拉丁美洲长久闭塞的自嘲。在这座被官方宣传定调为“运动中的城市”里,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底层人为了活下去抗议不公、向体制宣战的斗争,每天都在上演;爱恨情仇酿就的悲剧荒诞剧,也每天在街头小报上刷新。为《百年孤独》打着腹稿的马尔克斯一定也曾看到了这些,将之融化在对自己的祖国和故乡的想像性记忆里。
我书架上的第三本《百年孤独》,是访墨归来后上网购买的2011年版中文本。它的装帧质量和厚度都要胜过前两本书,腰封上还霸气十足地印着:“中文版全球首次正式授权”。伴随我成长的名著,如今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中文正版,买一本当是向大师致敬吧。回首往昔,《百年孤独》与中国的相遇与相知,几经坎坷,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当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热销、轰动文学批评界时,我们却沉浸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热里,与马孔多的闭塞而孤独的居民有几多相似?当我们解放了思想,热烈而又谨慎地拥抱外国文学时,它以它的别具一格成为中国的畅销书,却因为未经授权的翻译出版而惹怒作者本人,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的闭塞和孤独。当我们的出版界真正与国际接轨,重金买下马尔克斯作品的版权时,人们津津乐道于出版商的高投资和收获的高回报,文化事件成了商业案例;《百年孤独》出现在报纸每期畅销书榜的前列,关于这本书的深度思考和评论却并不多。《百年孤独》印证了经典的定义:人人都在谈论它,却没有人能坚持把它看完。《百年孤独》成了一个新时代的神话,其丰富内涵被缩减为几个诸如“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之类的标签,聊作媚俗者的谈资。如今大师离去,有学者发出了“一个文学时代已经终结”的慨叹。
的确,从三十年前人们如饥似渴、“不择手段”地争相阅读外国文学名作,到今天媒体热捧《百年孤独》、继而热烈地鼓励平时没时间没精力读书的人们以阅读行动来欢度“世界读书日”,时代的变化令人晕眩。一方面,我们从孤独走向拥抱世界;一方面,我们发现初识《百年孤独》的热情已经难以重现了。就连我们西班牙语系的学生也厌倦了文学课,更情愿通过看电影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不曾重读《百年孤独》久矣,我也相信经典作品应当在不同的年龄段拿出来重新阅读以期新收获的道理。读书是自己的事,且不管有没有“世界读书日”,无论何时,只要时机适当,自当放松心情享受阅读经典、浮想联翩之乐。或者,借着某一次阅读课的机会,我会挑出这部名著的片段,与“童鞋”们一起聊聊我的《百年孤独》,你的《百年孤独》,还有他或她的《百年孤独》……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