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14-10-07 16: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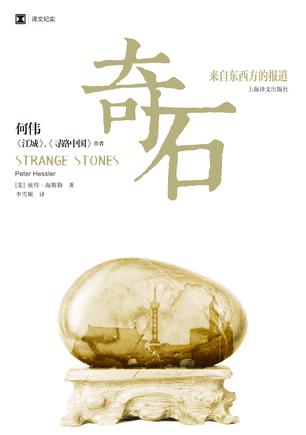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侯思铭/文 回到中国,彼得·海斯勒又成了何伟。此前一直在国内社交网络上酝酿和发酵的对于何伟的狂热一下子喷涌而出,正如何伟笔下的主人公常常不知道为何他会对自己产生兴趣,中国读者的热情同样使何伟感到好奇与惊讶。事实上他每次来中国,这种惊讶都必定被刷新一次。今年3月,他的第三本书《奇石》在中国大陆出版。
为了保持观察中国的视角,也为了写作不同的东西,何伟与妻子张彤禾(《打工女孩》作者)定居埃及已经三年。埃及和中国一样,都是经历着剧烈社会变革的国家,最大的区别或许是“一个基本没有政治变革,一个几乎没有经济发展”。被政治改变着的埃及与中国不同,有关政治的书写不可避免,但何伟的眼光依然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身上。虽然要写出不同的国度,但这是何伟最本质的理念:小地方、小人物。所以与其说何伟逃避写作大话题与大城市,不如说他是不肯浪费自己的机会。生活在剧变国家的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而何伟觉得自己的责任是“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中国,被何伟看作是自己的机遇,因为正是从这时候起,中国人的心态开始逐渐开放,人的想法也越来越复杂,这给何伟与普通人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当西方媒体记者专注于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臆想中国政治时,何伟默默无闻地在小城涪陵教书与观察;在许多中国本土作家都蜂拥去测绘大历史却一事无成时,何伟笔下的人物已经逐渐丰满。
这些由小人物登台的细节历史,经常会有追逐成功的故事跳出,被问及这和传统的“美国梦”有何不同?何伟觉得“在中国,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虽然美国与欧洲也曾经历类似的经济迅速发展时代,但过程比中国长很多,而“速度太快让中国人心有焦虑。”这种焦虑感既影响着国家转型时期的普通中国人,也从何伟的笔下时时流露。这些故事很多都发表在《纽约客》的“中国通信”栏目。如果说同样以报道和书写中国事务见长的欧逸文像鹰一样,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犀利的政治视角在俯察中国,那么何伟如同一颗大树,和他的描写对象扎根在同一片土地,并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伸展根系。证明之一是直到离开中国三年后的今天,何伟仍然与当初的采访对象保持联系。这次的中国之行,何伟依然回了涪陵,见了见分散在各地的学生和朋友。
在中国,作为知名作者,何伟接受了各种采访。即使是作为被采访者,他仍然习惯于带着本子和笔。然后,他会问:“你为什么喜欢我这本书?”
访谈
问=侯思铭 徐见微 朱天元
答=何伟
没有不可冒犯的题目存在
问:你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中国,直到三年前离开,因此你对中国的观察是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首先是越来越感兴趣了,1999年我把写完的《江城》交给一个美国代理商,那本书被送到美国出版社手里时,大多数出版社都不要。他们说我写得很好,但在美国这样的故事没有市场,因为美国读者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城市不感兴趣。但变化来得很快,2001年《江城》刚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三年之后越来越受欢迎,这其实是随着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而增强的。我去和平队的时候,人们还感受不到“中国制造”,但到了2001年,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身边的产品是谁制造的,进而觉得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国家。
第二个原因是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在80年代,一个外国记者很难写关于中国的书,首先外国记者受到的管控比较严,很难找到人接受采访,其次那时候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时情绪还很紧张,你甚至无法和当地人自然地交流。所以我觉得如果早十年来,我写不了这些东西,90年代才来到中国也是我的机遇,比如魏子淇虽然是普通农民,但我今天可以采访他很多次,聊很多话题。80年代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外国人的写作里只是个符号,但我运气好,可以跟他们聊天,中国人的思想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问: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都是从媒体获得的,所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重要,你觉得西方主流媒体描述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现在会说汉语的西方记者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人在美国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学习过,语言的学习让西方记者有了更多与中国普通人交流的能力。
还有一个变化是西方媒体写的题目比以前杂了,这可能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一些影响。除了传统媒体的记者,现在还有一些自由撰稿人,比如我自己、梅英东(Michael Meyer)、张彤禾(Leslie T. Chang)等等,我们不在传统媒体工作,所以可以写得更长、更深入,而以前这样的文章并不是很多。
问:你所供稿的杂志《纽约客》是否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答:我觉得是这样,很多媒体文章短、截稿压力大,时间不足以做充分的采访,而我在中国可能一年就写两三篇文章,想研究一个地方或者采访一个人可以去很多次。为了写一篇浙江丽水的故事,我对那里的观察持续两年,期间去了超过十次,在当地总共待了一百多天。报纸和周刊很难做到这样,这是《纽约客》和其他媒体的一个最大区别。
另外《纽约客》非虚构写作用的工具比他们多,在美国和英国,传统媒体有很多规定,比如采访对象本身是你的朋友就不可以写,但《纽约客》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更能当个好朋友;同时我也可以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这点很重要,因为我需要用第一人称表达我的幽默,没有这个视角就很难写一些好玩的事情。从这些意义上讲,《纽约客》无疑写出了不一样的中国。
问:欧逸文是你之后“中国通信”栏目的继任者,你们是否讨论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话题?
答:实际上我只跟他见了一次,我们邮件交流比较多,当他开始为《纽约客》撰稿时我已经走了。最后几年我研究中国经常在三岔、浙江等地,很少在北京。我本人与西方记者联系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怎样的,知道自己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流。并且《纽约客》的记者都比较独立,虽然我和他为同一个栏目供稿,但我们不需要成为一样的人。
问:他写中国的书叫作《野心时代》,以“野心”为切入点解读中国,那你在中国和埃及分别读到的是什么?
答:中国和埃及同为剧烈变动着的国家,但它们之间区别很大,今天的埃及其实处于一个被政治改变的年代,发生了很多革命、政变;与之相反,我所经历到的中国剧变是社会、经济、思想的,可以说,中国没有政治变化,埃及则基本没有经济变化。
埃及经济确实很糟糕,来到埃及的三年间,我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进步,政治却风云变幻。更多地解读政治,是我写作埃及与中国的最大不同,我不能用看中国的视角看埃及,这也就促使我写出不同的东西。
更安全的环境,更便宜的面包
问:不管是写作中国还是埃及,你的关注点都是普通人,既然政治对今天的埃及影响最大,那么政治在普通埃及人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埃及是个没有什么系统的地方。在中国,你永远都知道谁在管理国家,即使是如三岔这样的小村子,也有党员和政府官员管理,地方上也会接到一些政令是上面下达的。而在埃及,如果你去农村或者小城市,就算在人口众多的区域,也没有穆兄会(穆斯林兄弟会)的办公室,政府部门也很少。埃及仍然信奉传统的部落社会,发生事情不是找政府部门,而是问部落领导人,他们的部落领导人一般年纪很大,百分之百男性,人们坐在一起开会喝茶,谈一谈事情怎么解决,这是一种不正式、也不太现代化的政治。
埃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和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那里三分之二人口住的地方都是违法建筑,也没什么人管;多数人的工作也是非正式的,比如我写到的一个清洁工人,他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障,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合同,靠从废品里回收的东西以及人们给的小费生活,当然小费也是不稳定的。其实这个清洁工的收入已经比一般埃及人好很多,但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有生活在系统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也正因如此,普通人也许一开始对政治变革是有兴趣的,但现在不那么重视了。很多埃及人感受不到为不同的人投票有什么区别,埃及普通人最大的诉求就是更安全的环境和更便宜的面包。虽然政府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但便宜面包还是给了一些。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求什么,就只能得到什么,要求不高,得到的回报也不高。当他们说要改变,最后经常落在很小的地方,但真的革命应该有一些社会的缺点要改,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你在《奇石》里提到,开罗街头最让你惬意的场景就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你觉得埃及的社会支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那么你怎么看待群体意识在埃及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答: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矛盾,如果你在埃及街头遇到困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摔倒了有人扶你起来,不认路有人为你指路,这些帮助都是自发和主动的,或许很多国家的人做不到,但埃及可以。也许是宗教原因,毕竟伊斯兰教对此很重视。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些细微之处可以感受到的群体意识和亲切感,在政府和领导人身上看不出来,事实上埃及人对下台的领导人非常不友善。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每次去法庭受审都被关在笼子里,我曾经亲眼看到过穆尔西穿着白色的衣服,在笼子里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当时我作为外国记者出席,在场的埃及记者都在狠狠地谩骂穆尔西,坐在我旁边的正好是个中国记者,他与我一样感到震惊。
问:你对中国的观察从九十年代开始,跨越很长时间段,对埃及的观察是从近三年开始,所以你也许可以把埃及和中国做一个跨时间段的对比,比如埃及和中国的其他时期有哪些相似?
答:这两个社会区别比较大,不仅是时间概念,两国传统和基础也不同。中国可能曾经有过一些部落社会的特色,但解放之后变了很多。由于区别太大,我不能说埃及是中国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当然还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对比,但不会太直接。
我偶尔也会以中国的眼光看待埃及,刚才提到的群体意识是一个区别,还有中国人和埃及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也十分不同,埃及人相对不那么爱赚钱。我家里有东西坏了需要修理,埃及工人可能会回答我,“今天我不去,我现在想休息会儿。”但中国人不会这样。这也有好有坏,好处是埃及人轻松一些,不会像中国人压力很大,坏处是他们可能有点懒。
问:中国和埃及都是处在急剧变化中的国家,都走在转型路上,你如何看待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答: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的影响是必然的,中国主要是经济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埃及由于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感受到政治变革带来的变化,因为生活水平方面的改善极其有限。假如问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对你有影响吗?或者他与他的家人出去打工了,或者他的地被卖了,但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影响无可避免,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改变。
当然人的思想上也会改变,比如中国和埃及的个人主义都在增多,尤其是中国,国家转型促成的人口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到新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在外打拼就会很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关注的也是这样的人物。
我的责任是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问:你会写到中国人去追逐一些世俗的名利,提高社会地位。这和传统的“美国梦”有什么不同?
答:两者很相似,美国工业兴起的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一样的。比如也有很多女人从乡村走出,开始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但中国最大的不同是速度太快了,美国和欧洲虽然与其形式上相似,但都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而中国是突然发生这一切的。速度太快让中国人心里有种焦虑感,因为尚未习惯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问:你在观察了中国的汽车工厂后觉得中国人“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比美国人还美国化”。但是中国也有反对西方,敌视美国的思想,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
答: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这个矛盾可以说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国内比较自由,体制有它人性化的地方,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这样。美国人自己也很少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不太了解伊拉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富汗又发生了什么,所以虽然总统选举会投票,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一个民主的事情。很多人说中国人对美国的思想有矛盾,但其实美国的政策也有矛盾,特别是9·11之后,美国人对外抱有一种恐惧心里。美国虽然在文化输出上很成功,但其本质上是排外的。
问:《奇石》里有美国的故事,有埃及的故事,当然也有中国的故事,你在描写不同的国家发生的故事时,会刻意去区分和提醒自己其中的不同吗?
答:对我来说,写作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小区别,但最根本的角度没什么不同,我也会尽量基于同样的态度去观察这些国家。非虚构写作就是将感兴趣的问题搜集起来,用时间观察,最后写成故事。我写过美国一个药剂师的故事,主人公也是个普通的美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不重要的人,他自己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但是我会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有故事。这种态度和在中国写普通工人和农民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中国人现在已经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你在埃及也会接触到很多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中国既是你长久以来的观察对象,也是你观照世界的一个尺度,你留意那些在海外打工的中国人,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结论么?
答: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近几年我去上埃及(埃及南部)比较多,主要研究埃及考古和传统部落社会,我会偶然碰到一些外出做贸易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浙江温州,我也会写到关于他们的文章,但现在还没有采访完。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和我一样,在埃及既是外来人,也是观察者,所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了解到不同的埃及。
在埃及的中国人大多住在特别偏僻的地方,其中许多人一句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或者也只能讲一些特别简单的词语,比如“多少钱”和一些数字,和讲价没关系的词就不太会说。埃及发生一些暴力事件的地方也有中国人在做生意,那些危险的事儿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否赚到钱。
问:普通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你在建构关于普通人的历史的时候,会给自己一种使命感吗?
答:会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埃及,我处在的年代都非常重要,但剧烈的变化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忽视和遗忘许多细节,而我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些东西。因为我是从国外来的,可以花的时间也比较多,本地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却可以观察和记录这个过程中细微的东西。虽然非虚构写作在任何地方都有意义,但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国和埃及的工作更重要。从我个人而言,记录美国当今的历史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但埃及和中国需要这一点。
问:相比起张彤禾写的东莞,梅英东写的北京和东北,你选择的城市都不“热门”。什么样的城市更能够激发你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欲望?
答: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资料已经很丰富,写作者也比较多。许多传统媒体的记者无法写小城市和小人物的生活,他们供职的媒体有他们的规定。而我拥有写小地方的条件,如果我不去写,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机会。而且对我来说,记录小地方的故事更有意义,我更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