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张艺谋新作《第二十条》在各大影院热映。该片片名取自刑法“第二十条”,讲述的是关于“正当防卫”法条背后的公理人情。其实在现实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吵不完的法律热点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法考男神”罗翔的《法律的悖论》一书,通过分析法律中经典的案件,辨析了法律中的盲区,揭示了法治的核心,并引导读者探讨和思考法律中的悖论。书中可以读到的,不仅是法律知识之繁杂,更有批判性思维和接纳多元观点之重要。

《法律的悖论》
罗翔 著
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法律与道德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尤其是一些出现伤害结果的案件,如何正确区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互殴、伤害的界限,对于很多检察官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其中一个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
影片《第二十条》中,韩明为了说服张贵生放弃上访,拿出案发时的视频录像一帧帧进行分析解读,认定张贵生与“咸猪手”的打斗从最初的正当防卫,转化为互殴,甚至是故意伤害。此时的韩明,站在事后的角度,以理性冷静局外人的视角,围绕暴力升级的时间点,将整体案件割裂进行分析。虽然他参考了很多既往判例,对案件的分析和处理好像也符合法条规定,但却没有做好对法、理、情的兼顾。
冰冷的法律逻辑,需要考虑人类的情感吗?需要,又不需要。这是一个悖论性的回答。从公认的前提推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就是悖论。悖论包括真悖论和假悖论。假悖论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看似合理但其实不合理;真悖论则是“似非而是”,看似荒谬的结果却被证明是真实的。
罗翔认为,悖论的出现,提醒我们:人类是有限的,理性是有瑕疵的,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把握对世界整体性的全局认识,无法完全开启上帝视野。这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了大象的全部,但其实不过是摸到了大象的部分。
法律与道德、理性与感性,是一场古老的争论。中国古代有儒法之争,主要涉及的正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儒家认为道德是可以影响法律的,但是法家认为道德绝对不能干涉法律,法不容情。
法家强调“刑名”,所谓律法与名实相符,大致相当于后世的演绎逻辑,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比如西汉的法律规定,殴伤父亲者枭首。结果张三的父亲与他人斗殴,张三用木棍去打他人,不料却误伤其父。按照法家的观点,那就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判处张三死刑。但是按照儒家的观念,法律不应该那么机械,要考虑背后的情理。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提倡“《春秋》决狱”,也就是用儒家的道理来软化机械的法律。如果犯罪者的动机是好的,就可以从宽甚至免罪,所谓“君子原心”,论心不论迹。
“张三伤父案”是西汉武帝时的一个真实案件,廷尉张汤请教董仲舒应该如何处理。董仲舒举了《春秋》的一个典故,来说明张三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春秋时期的许悼公生病,太子许止给父亲送药,结果父亲一命呜呼。太子很伤心,觉得自己有错,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自己郁郁寡欢而死。《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但《春秋公羊传》认为,许止的动机是好的,不算为罪。董仲舒以此典故主张张三不构成犯罪,张汤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
在罗翔看来,不讲道德的法律,只把民众当作威吓的对象,这样法律将沦为纯粹的工具,民众丧失人格和尊严,法律人迟早也会成为刀笔吏,甚至成为酷吏。但只讲道德的法律,也很虚弱无力,太过理想而不现实。所以,后世的封建统治者采取儒法合流,内法外儒,用儒家的理想主义来约束法家残酷的现实主义。
犯罪之恶
《第二十条》的故事启示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本意,不能站在事后的角度,去分析和判断防卫人的行为动机和主观目的,不能割裂案发原因和自然演进过程,将整体案件切片看待,也不能简单以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重于不法侵害造成的后果,就排除防卫人具有防卫意图,而应当把自己代入现场、代入当事人的角色,综合案件起因、案发具体环境、矛盾激化过程、双方力量差异、行为人一贯表现等方面,作出客观全面、符合常情常理的判断。
在刑法中,这样需要综合考虑的情况比比皆是。
2021年,一名高校女生因为罹患抑郁症,从海外购买精神类药品。她如实填写了收件地址,被轻松抓获,后被控走私毒品罪。通过这起案件,大家才知道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既是药品,又是毒品。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法院考虑到此案情有可原,而且被告身患重度抑郁,经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最后对其判处了缓刑。虽是缓刑,女生也被贴上了犯罪的标签,她的人生轨迹被改变了。
这涉及犯罪本质的争论。犯罪是一种恶,这种恶是因为“它是犯罪所以邪恶”,还是因为“邪恶所以成为犯罪”呢?随意虐杀他人,自然是一种邪恶的行为,所以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但是抓几只鹦鹉,在刑法中也可能是犯罪,这也是因为行为本身邪恶吗?
《法律的悖论》指出,早在古罗马就有自体恶和禁止恶的争论,自体恶是指某种行为的恶是与生俱来,该行为本身自带的。禁止恶则是指某种行为因为法律的禁止所以成了恶,恶并非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因为邪恶所以犯罪,还是因为犯罪所以邪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它既是逻辑问题,又是现实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书斋中的空谈。”
“从形式上来看,这符合走私毒品罪的构成要件。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既是药品也是毒品,但只有当毒品具有一定的扩散性,才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即便将此罪侵犯的法益归结于毒品管理秩序,那也应该还原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因此,罗翔认为,以治病为目的购买精神药品不应该以犯罪论处。2023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终于规定:“因治疗疾病需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携带、寄递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出境的,不构成犯罪。”
无数个案推动了法治的前进,但起到推动力量的每个个体,却不得不承受百分百的痛苦。《法律的悖论》认为,犯罪是一种恶,这种恶不仅因为它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被贴上了犯罪的标签就成为一种恶,更为重要的是因其内在的道义上的可谴责性而成了一种恶。缺少二者中任何一种的恶,都不是犯罪。
稳定与灵活
现实中,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如何既尊重立法权威,又进行合理的司法修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法律并不等于真理。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立法错误其实都比比皆见。美国阿肯色州曾出现一个明显的立法错误——婴儿获得父母同意也可以结婚,让人大跌眼镜。法条表述如下:“年龄在18岁以下,并且没有怀孕的人如果要领取结婚证明,必须出示父母同意的证明。”后来发现这一乌龙是误写了“没有”两字。
罗翔认为,法律肯定是需要解释的,立法者把一些经常发生的行为用语言进行规定本来就很困难,用条文来穷尽它所应涵盖的所有情节,无异于一种过于理想的刑法乌托邦。加上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立法时不能预见的事情发生是自然而然的。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司法机关不能创造新的法律,不能进行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但却允许扩张解释。一般认为,尽管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很难划出一个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扩张解释是将刑法规范可能蕴含的最大含义揭示出来,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解释极限化;类推解释是将刑法规范本身没有包含的内容解释进去,是解释的过限化。在民事领域,允许法官探究法律精神,类推定案。但在刑事领域,不允许法官做对行为人不利的类推解释,因为刑罚指涉的是公民的自由、生命、财产等最基本的价值,如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在某种意义上,少打击一些过分行为,总比滥施刑罚要强得多。
清末修订的《大清新刑律》草稿补笺,就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法律规定道路禁止牛马通过,那么举轻以明重,自然也禁止骆驼和大象通过;池塘禁止垂钓,自然也禁止撒网捕鱼。但是,这种自然解释其实已经超越语言的限制了。牛马包括骆驼吗?垂钓包括撒网吗?
罗翔觉得,无论如何,司法不能突破语言极限创造对行为人不利的规则。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如果毒驾呢?是不是更应该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这样的话,那醉酒开飞机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醉驾呢?原则一旦突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罗翔说,对于入罪的当然解释,必须要卡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质标准,举轻以明重,另一个则是形式标准,不能超过语言极限。
公元1142年,在南宋临安大理寺狱中,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岳飞之死让大家知道了什么叫“莫须有”:也许有。几百年后,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罪名逮捕了袁崇焕并将其凌迟,京城不明真相的百姓们竟然恨袁崇焕入骨,行刑之日,纷纷出钱买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吃,还骂袁崇焕是个“叛徒”。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否则就不会再有对这两位英雄翻案之事了。
刑名关乎性命,自当慎之又慎,保持谦卑和敬畏。在罗翔看来,人们像蚂蚁一样,生活在有限的世界,但在我们的视野以外,还有更多、更美、更神奇的存在。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虽然公义眼不能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很多人认为法律人是理性的,感性是职业大忌。但哲学家阿奎那提醒我们: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性之中。”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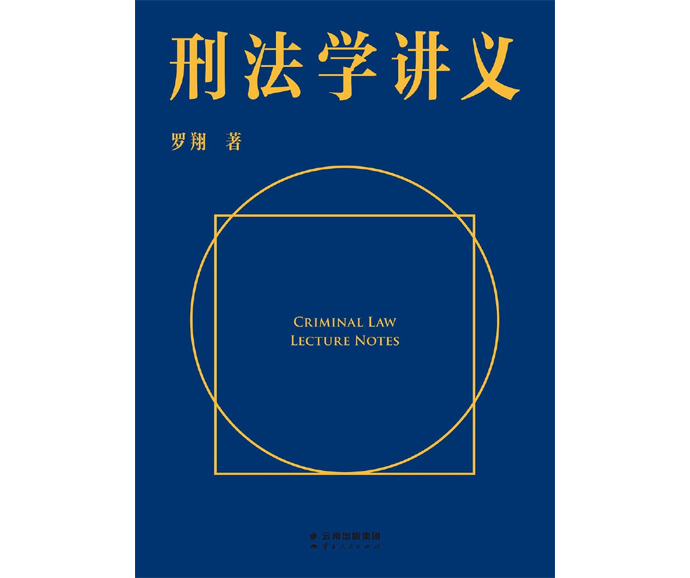
《刑法学讲义》
罗翔 著
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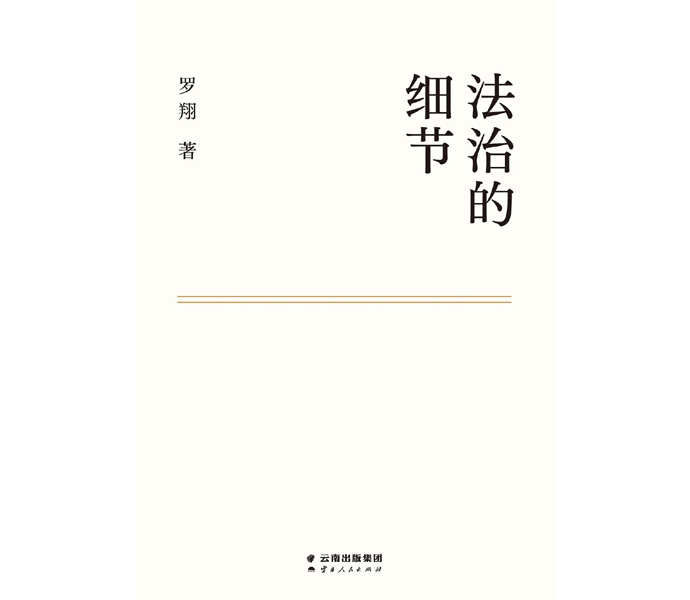
《法治的细节》
罗翔 著
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季东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