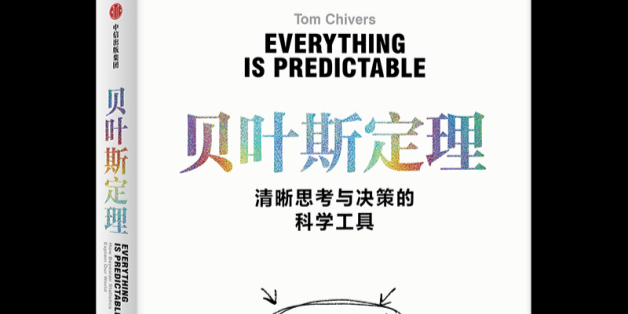
你是不是也感觉——AI 越来越像人了?
它能理解你的问题、给你建议,甚至还能陪你聊天谈心;
大模型(LLM)不仅在说话,简直是在思考。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模型为什么像人类一样“思考”?
是因为数据多了?参数大了?算法复杂了?LLM背后的逻辑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应该是——LLM 背后其实是利用了一个 18 世纪的“人类思考公式”: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
贝叶斯定理是以18世纪英国数学家和神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的名字命名的,是一种用于更新我们对某个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通俗地理解,你可以将其比作一种“修正”或“调整”我们的信念。
假设你有一个关于某件事情发生概率的初始猜测,这个猜测可能是主观的、基于经验的、或者是先验知识。然后,当你获得新的信息或证据时,你可以使用贝叶斯定理来重新评估你的初始猜测,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估计。
每次我们面对不确定的事物做出决策时——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都可以利用贝叶斯定理来判断该决策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个好决策。
事实上,无论是怎样的决策过程,无论你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对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无论你掌握的信息多么有限,无论你是正在寻找高浓度葡萄糖环境的细菌,是正在利用复制行为传播遗传信息的基因,还是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政府,只要你想把事情干好,你就离不开贝叶斯定理。
AI(人工智能)本质上也是贝叶斯定理的一个具体应用。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AI 所做的事情就是“预测”。一个可以分辨猫狗图像的 AI 应用,本质上就是在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和当前的图像信息去“预测”人类对图片的判断。DALL-E 2、GPT-4、Midjourney 等各种优秀的 AI 应用,正在以令人应接不暇的速度一次次冲击人们的认知。
不过,这些和你谈笑风生、为你生成高质量图像的 AI,本质上也是在做预测,只不过它们预测的是人类作家、人类艺术家面对这些提示词时会如何作答。这些预测行为的基础都是贝叶斯定理。
AI 本质上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抉择。谷歌的密码学家保罗·克劳利告诉我:“如果你懂贝叶斯理论,你就会发现 AI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到了大量贝叶斯思想。”
现代的那些 AI 神经网络存在大量节点,这些节点就像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AI 会在学习过程中为不同的节点链接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加强或削弱各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
保罗·克劳利表示:“AI 内部有一套评分机制,权重体系越复杂,它的得分就越低,反之就越高。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迫使它尽量采用更简单的假说,而不是更复杂的假说,这看上去完全就是贝叶斯思想;其先验概率就是建立在奥卡姆剃刀原则之上的。进行完整的贝叶斯计算需要耗费大量算力,所以现代这些 AI会尽量使用算力需求较低但性能表现并不会逊色多少的简化算法。”
不管怎么说,贝叶斯思想都是 AI 的基本原理之一。“大多数现代AI 系统的基本思想都是贝叶斯定理,因为它们关心的都是不确定情况下的推理方法”。
事实上,有一种 AI 算法就叫“贝叶斯机器学习”,它的整个构架都在模仿贝叶斯定理。
假定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AI,它的任务是识别老鼠、狗、狮子的图片。如果是十几年前,这种 AI 足以令人感到震撼,但放到今天来看,它简直太普通了(其实就在 2017 年,我为第一本书的创作而四处走访时,AI 能够将猫狗区分开来还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至于现在,你只需要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它甚至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将照片库中的狗狗、婴儿、海滩等类别的照片全部给你筛选出来)。
理论上来说,它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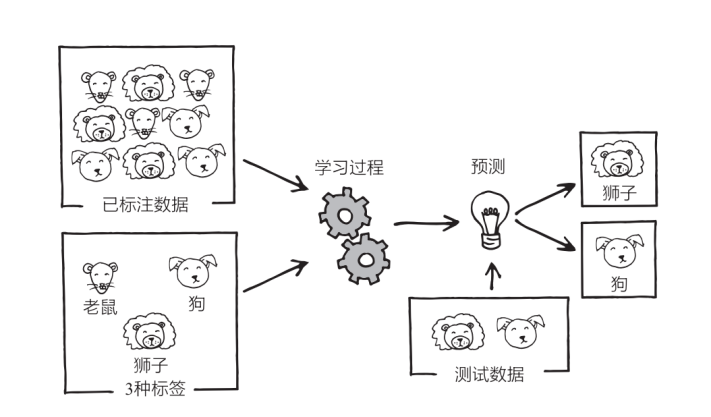
你“喂”给 AI 几百万或几千万张分别标好“老鼠”“狗”“狮子”的图片,让它利用这些“已标注数据”进行训练,然后它就会以某种方式反复学习数据。学习完成之后,你需要再拿几张它没见过的图片(“测试数据”)进行测试,此时它会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对这些测试图片做出最佳猜测,并给这些图片分别标上“老鼠”“狗“狮子”的标签。
AI 的这种学习方式就是所谓的“监督学习”。它所干的事情,就是预测“那些喂给自己学习数据的人类”会给新图片标上什么标签。”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贝叶斯思想去解释这一过程,二者几乎是一样的:在看到某张图片之前,这个 AI 可能会主观地认为这是一只狮子的先验概率为 1/3,即 p ≈0.33。看到图片之后,也就是得到新信息之后,它会将这一概率更新为 p=0.99,或其他什么数字。先验概率、似然比、后验概率。
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现在我们将情况进一步简化,把上面的例子看成一张图,图上面有一堆数据点。此时 AI 的任务是分析图像,然后找到一条能够穿越这些数据点的最佳拟合直线。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强大的 AI 来干这种事,因为这只是线性回归而已,高尔顿那个年代的统计学家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原理是一样的。
假定这些数据点表示的是人们的鞋码与身高——你随机抽取了一大群人,测量了它们的身高和鞋码。图上 X 轴表示的是鞋码,Y轴表示的是身高。通常来说,这些数据点会分布在左下至右上的区域附近。
AI 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些数据点的最佳拟合直线。当然,你也可以凭感觉来画,但我们最好采用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方法,即最小二乘法。在图上画一条直线,然后测量每个数据点和这条直线的垂直距离,这一距离就是“误差”。将每个点的距离,也就是误差,取平方值(平方是为了让所有数都是正数),然后将所有平方值加总,得到平方和。
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能让平方和达到最小值的直线,即每个数据点的平均距离最短的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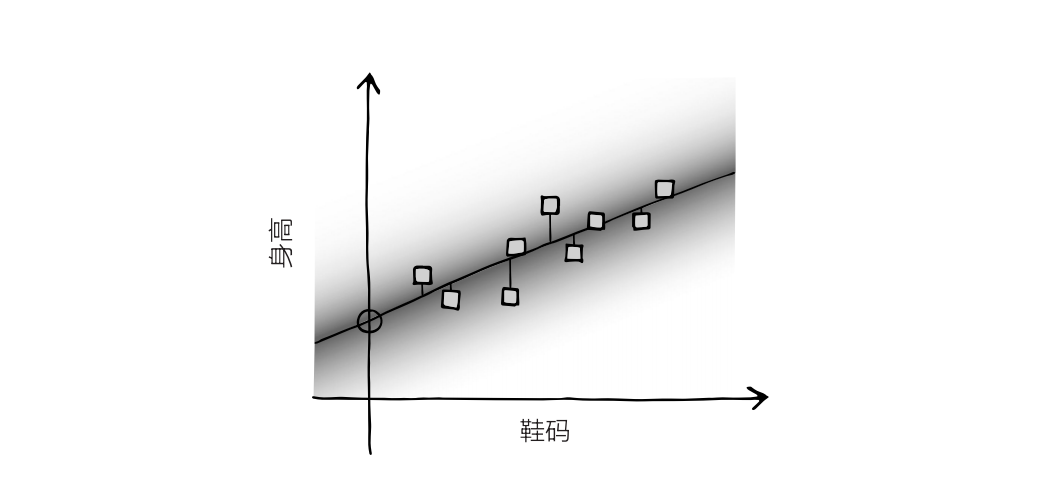
这些数据点可以视为 AI 的训练数据,而这一过程也用到了贝叶斯思想。首先,图上分布着一条直线,代表着宽泛的先验概率。然后我们在图上加入了数据点——代表数据。之后这条直线会根据数据而移动,得出后验分布。最后这条直线又会成为下一批数据的先验分布。
假如你现在知道一个人的鞋码是 11 号,想用它预测这个人的身高,那它就会用最小二乘法画出一条最佳拟合直线,然后读取横坐标 11 所对应的纵坐标,这个纵坐标就是 AI 对身高的最佳猜测。它有多大把握,取决于训练数据有多少,以及训练数据有多分散。数据越分散,把握就越小。
当然,这只是 AI 最基本的原理,实际上它们要比这复杂得多,涉及的参数也不会只有鞋码、身高,而是成千上万个,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所有 AI 都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然后根据某些参数去预测另一些参数的值。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这条线是直线,其实真实情况下它更可能是曲线。如果 Y 轴表示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全球病例数”,X 轴表示的是“时间”,起始时间是 2019 年 11 月,那么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是条指数曲线,因为病例数量每隔几天就会翻一番。有的时候,最佳拟合曲线会长得像英文字母 S 或 J,也可能是一条正弦曲线,或其他什么形状的曲线。当然你可以让 AI 一直依照直线去模拟,但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会导致这条线“欠拟合”。
同样,你也可以让 AI 变得极为复杂,这样它就会画出一条七扭八歪的、完美穿过每一个数据点的曲线,此时误差的平方和等于0。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这很可能无法反映出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出现新数据时,这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很可能距离新的数据点相去甚远,因为这条线已经变得“过拟合”了。
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 AI 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去拟合曲线,这种程度就是自由度。自由度有点像前两节中的“超参数”——除了最佳拟合曲线这个问题,我们还应当关心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即这条曲线应当有多“扭曲”。AI 对这些参数的先验判断就是它的超先验。通常情况下,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AI 会在两条线中选取更简单的那条。还记得吗?在讲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时候我们曾提到,我们要权衡假说的简单程度和符合程度,AI 也需要做这种权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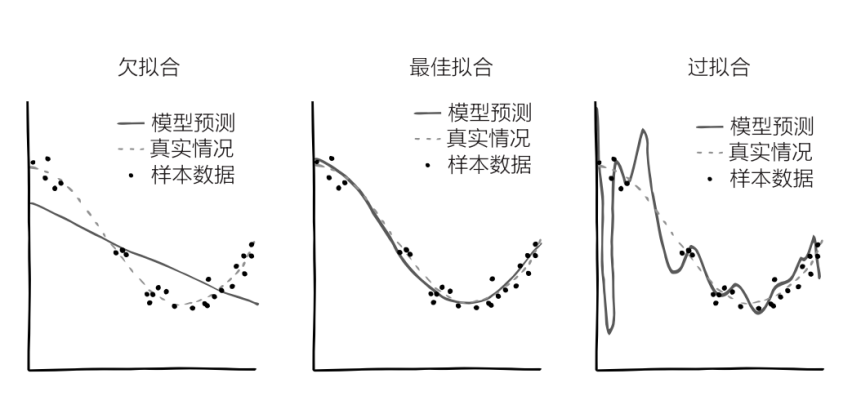
医用 AI 在试图分辨癌症的扫描结果时,ChatGPT 在试图仿照《英王钦定本圣经》中描写的一个男人努力取出电视机里的三明治的情节时,都用到了贝叶斯思想。它们都在根据训练数据生成先验概率,然后用这些先验概率预测未来的数据。
虽然贝叶斯定理不是万物理论,但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一旦你开始站在贝叶斯定理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你就会发现贝叶斯定理真的是无处不在。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