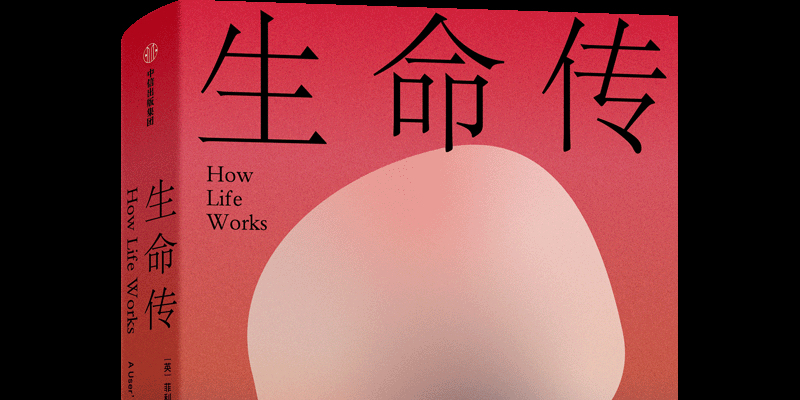
大约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生命”。那或许只是一团包裹在脂质膜中的核酸与蛋白质,在原始海洋的热泉口附近完成了第一次自我复制。但……等等,什么是生命?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困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数千年。1944年,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曾试图用“负熵”为生命下定义,却也承认这只是描述而非答案。书中跨学科的观点启发了后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但要真正理解生命,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从未停止。亚里士多德提出“生机论”,认为生命体具有特殊的“生命力”;笛卡尔则将生物视为精密的机械装置;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理论解释生命的多样性。进入20世纪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突破,我们逐渐揭开了生命的层层面纱。但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运作机制仍然充满了未知,许多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答案。比如,癌症为何难以攻克?衰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意识的起源和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困扰着科学家,也激发着我们对生命的无限遐想。
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员、《自然》前编辑菲利普・鲍尔(Phillip Ball)以20余年科普写作的积淀著成的《生命传》(How Life Works),正是聚焦这些核心疑问,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演化理论等多学科视角为支点,层层剖析生命运作的底层逻辑。
作为同时深谙科学细节与人文视角的科普作家,鲍尔的独特之处在于:既不沉迷于基因序列的琐碎数据,也不满足于“生命是台精密机器”的简化模型,而是将生命视为一场“多维度的即兴演出”,打破了“基因决定论”“生命机械论” 等传统认知的桎梏,通过解析DNA与蛋白质的动态交互、细胞信号网络的混沌与秩序、多细胞生物的自组织原理等前沿发现,展现出生命作为复杂系统的灵动与韧性。
在《生命传》中,鲍尔颠覆了传统生物学的认知,提出了三大新观念:
基因是仆人,而非主人:DNA并非生命的唯一指挥官,细胞、蛋白质、组织等层级各有其自主性。
生命拒绝简化类比:将生物体比作机器或计算机是误导性的。生命通过分子噪声、随机性和自组织实现动态平衡,而非预设程序。
生命是层级的交响乐:从RNA的转录纠错到细胞群体的集体决策,生命通过多层级协作“创造意义”。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方斯华·贾克柏所言:“生命可不只是一种单一组织,而是一系列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互相嵌套的组织。”
熵增是宇宙的法则,生命选择逆熵而行
多层级协作的生命图景,或许正是生命能够“逆熵而行”的核心奥秘。
“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提出,用于度量一个系统的“内在混乱程度”。简单来说,熵越高,系统越无序;熵越低,系统越有序。
熵增定律指出,在一个孤立系统中,如果没有外力做功,系统的总混乱度(熵)会不断增大。这就如同我们的房间,如果不加以整理,会越来越乱;一杯热水放在桌上,热量会逐渐散失,最终与周围环境温度一致。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宇宙也在遵循着熵增定律,终将走向热寂与无序,这似乎是宇宙万物不可避免的命运。
然而,生命却像是一个奇迹,一个违背熵增定律的“叛逆者”。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从生机勃勃的植物到灵动聪慧的动物,生命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有序性和组织性。生物体有着精确的结构和功能,细胞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代谢、分裂和分化,器官之间相互协作,维持着生命的正常运转。
生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薛定谔认为,答案或许在于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它能够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他提出生命以“负熵”为食,即通过摄取外界的低熵物质(如食物、阳光),排出高熵废物(如热量、代谢产物),来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合成有机物质,这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降低了自身的熵。而动物则通过摄取植物或其他动物,获取能量和物质,维持生命活动和身体的有序性。
但鲍尔认为薛定谔虽然提出了关键问题,却给出了过于机械化的解决方案。鲍尔进一步揭示,这种逆熵能力绝非简单的能量转换,而是源于生命系统独特的层级架构:
分子层面的随机性利用。与传统认知相反,生命并非竭力消除分子噪声,即便组件中存在噪声或者发生某些变异,这类宏观节点都能可靠运作。
细胞尺度的自主决策。每个细胞都像微型"逆熵引擎",能根据微环境调整代谢策略。
组织层级的抗脆弱性。当干旱让草原枯萎,一些植物的根系会通过化学信号协调资源分配,这种群体智慧使生命系统在扰动中保持稳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地球生命已经持续存在了近40亿年,生命的韧性非凡!
我们曾以为生命是一部精密的机器,后来以为它是一台复杂的计算机。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生命更像一片永远在生长的森林,每个细胞都是一棵会思考的树,它们彼此竞争又相互滋养,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在有限中追求无限。
我们真的是基因的傀儡吗?
这片在混乱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森林”,既展现着逆熵的奇迹,也暗藏着更深层的谜题:维系这一切秩序的核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基因在幕后操控着每一片叶子的生长方向吗?我们真的是基因的傀儡吗?
在探索生命运作机制的道路上,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道金斯在书中提出,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完成草图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豪情万丈地宣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学习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曾让人们满怀期待,以为我们即将揭开生命的所有奥秘。科学家们原本预计人类大约有10万个基因,然而结果却令人惊讶,人类基因的数量只有2万个左右,与一些简单生物的基因数量相差并不悬殊。这一发现让人们开始反思,基因似乎并不能完全决定生命的一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命并非仅仅由基因决定,环境、表观遗传等因素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观遗传是指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基础上,调控基因表达的现象。
父母的生活经历,如饮食、压力、环境暴露等,都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标记传递给后代,影响后代的基因表达和生理特征。在纳粹占领荷兰期间,那些因为封锁食物而在食物短缺中孕育下一代的女性,她们的孩子长大后出现肥胖、心血管疾病等代谢问题的概率明显增加,而且这种影响还延续到了再下一代。这说明,环境因素可以在基因上留下“印记”,改变生命的轨迹。
此外,基因的表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细胞的需求和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果蝇为例,致癌基因和无翼基因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表现的效果不同。在后来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又发现这样的基因不止这一种,类似的基因其实是一个家族,这个现象在生物学中到处都有。
基因确实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命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但基因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主宰。鲍尔说道:“基因不能产生生命,相反,基因依赖生命。”科学哲学家詹姆斯·格里塞默极为直率地表达了这一点:“基因根本不是主宰一切的分子,它们是发育的囚徒,被囚禁在森严牢狱的最深处。”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曾观察到一个奇妙现象:当酵母细胞处于饥饿状态时,一种名为Gcn4的蛋白质会主动附着在200多个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唤醒那些负责氨基酸合成的基因。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基因的激活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细胞内的营养水平灵活调整。这哪里是基因决定蛋白质,分明是蛋白质在指挥基因该何时登场。
如今看来,基因并非“主宰者”,更像是一本被反复批注的词典,没有哪个基因能独自决定“我要长成一朵花”,就像没有哪个汉字能单独写出一首诗。
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从鱼鳍到人手,从鸟翼到蝙蝠翅膀,生物学家发现这些看似不同的器官,都由相同的“模块”发育而来。这种模块化设计赋予了生命惊人的适应性。当环境变化时,生命不需要推倒重来,只需调整模块的组合方式。恐龙的鳞片逐渐演化成鸟类的羽毛,前肢变成翅膀,这种改造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
强大稳健性是生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干旱、洪涝、高温、低温等自然环境的变化,还是病原体的入侵、自身的损伤等内部因素的影响,生命都能够通过各种机制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
动物在面对病原体入侵时,免疫系统会迅速启动,识别和清除病原体。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各种免疫细胞相互协作,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防御网络。生命还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当生物体受到损伤时,细胞会通过分裂和分化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器官。皮肤受伤后,表皮细胞会迅速分裂,填补伤口,使皮肤恢复完整。植物的应激反应更具诗意。当树木遭遇虫害,会释放挥发性化学物质警告周围的同伴,邻近的树木接到信号后,会主动增加叶片中的单宁含量,让害虫难以下咽。这种无声的互助,让整片森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御网络。
此外,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渠限化现象。这意味着生命的发展并非无限可能的,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细胞会按照特定的路径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而不是随意发展。这种渠限化使得生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确定性。
渠限化也与生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密切相关。它使得生命系统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下,发展出最适合生存的特征和能力。不同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通过渠限化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以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例如,鸟类进化出了翅膀,使其能够飞行,适应空中的生活。鱼类进化出了鳃,使其能够在水中呼吸,适应水生环境。
生命的未来:重新定义可能与边界
当我们突破基因决定论的桎梏,生命科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合成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颗新星,正逐渐崭露头角。这是一门汇聚了生物学、工程学、化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前沿学科,旨在通过对生物系统的设计和构建,创造出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生物功能和生物系统。
2010年,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领导的研究团队成功合成了第一个人工合成基因组,并将其植入到一个去除了遗传物质的细菌细胞中,创造出了第一个“人造生命”。2021年,我国科学家将酿酒酵母的16条染色体融合成1条,这个“极简酵母”不仅存活下来,还能正常繁殖。
这些突破并非简单的基因编辑,而是重新设计生命的底层逻辑。科学家们正在尝试构建具有全新功能的生物系统:能检测土壤重金属的细菌,能生产抗癌药物的酵母菌,甚至能分解塑料的工程菌。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命的本质,还为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疾病治疗等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糖尿病患者需要的胰岛素曾经依赖从动物胰腺中提取,如今则可以让工程菌在发酵罐中大量生产。这种将生命改造成“微型工厂”的技术,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缓解人类的痛苦。
与合成生物学并驾齐驱的还有再生医学。蝾螈能再生断肢,海星能重建内脏,这些生物的再生能力曾让人类羡慕不已。如今,致力于利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促进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再生与修复的再生医学正在让这种羡慕变成现实。日本科学家成功将皮肤细胞重编程为诱导多能干细胞,这种细胞能分化成各种组织器官,为器官移植带来了曙光。
除了干细胞,再生医学还涉及组织工程、生物材料等多个方面。组织工程通过构建三维支架,并在其上种植细胞,模拟人体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实现组织的再生。生物材料则为细胞的生长和组织的修复提供了良好的微环境。科学家们开发出了各种生物可降解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在体内逐渐降解,不会对人体造成负担。通过将生物材料与干细胞技术相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组织和器官的再生。
如今,具身智能进入了百花齐放、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有一些科学家却在尝试另一种思路:用肌肉细胞驱动微型机器人。这些“生物机器人”既有机器的精确控制,又有生命的自主修复能力,它们能在体内精准递送药物,或是在环境中检测污染物。
更具颠覆性的是“脑机接口”技术。当瘫痪患者通过植入大脑的电极控制机械臂,当渐冻症患者用意念拼写单词,这些突破不仅改变了残障人士的生活,当机器成为身体的延伸,当电子信号与神经冲动交融,生命的定义正在被重新书写。
如果基因不是命运的主宰,那么我们在编辑胚胎基因时,是在纠正错误,还是在重写人类的未来?如果意识源于细胞的集体智慧,那么AI是否也可能“觉醒”?
《生命传》最终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深远的思考:当我们越来越擅长“改写”生命时,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本质?鲍尔在书中提醒我们,科学的发展不应只关注“我们能做什么”,更要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