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8-01 15:19

![]()

2020年荷兰王室曾在海牙王宫花园拍摄全家福。阿根廷八卦新闻杂志《Caras》选用这组照片作为封面,主打大公主阿玛利亚,配文是“阿玛利亚公主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大码身材”,还着重突出“大码”一词。
此举招来无数批评,人们认为杂志如此大张旗鼓评论一个当时才16岁的孩子的身材,完全就是羞辱。在现实中,这样的恶意无处不在,有时会以励志的方式呈现,很多人将之称为“身材管理”。
身材焦虑和容貌焦虑在全球各地和各个阶层都或多或少存在。它的本质是极端的审美定义,比如中国社会对“白幼瘦”的吹捧,西方社会对健康肤色的刻意赞美,部分群体对体脂率的极致追求。个体对自己有所要求当然是个人自由,但一些社会和部分群体将之视为衡量他人的标准,就会造成扭曲。
早在1991年,英国学者娜奥米·沃尔夫就在《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一书中写道:
不少女性尽其记忆之所及,写信或亲口向我吐露她们经历过的恼人的个人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她们从那种被确认为美貌神话的东西中脱身,找到自我。将这些女性联合在一起的并非她们的外表: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女性,都向我诉说了对衰老的恐惧;无论是苗条的还是肥胖的女性,都提到了因努力去满足纤瘦理念的要求而遭受的折磨;无论是黑色人种、棕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的女性——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时尚模特——都承认从能有意识思考的那一刻起,她们就知道理想的女人是个高挑、纤瘦、白皙的金发女郎,她的脸庞上没有一丝毛孔、不对称或瑕疵,她是一个完全‘完美’的女性,是她们无论如何都认为自己不会成为的那种女性。
在娜奥米·沃尔夫看来,“女性永远不够美”,继而将美貌视为“义务”,把镜子变成刑具,将“变美”视为终身工作,是消费时代的一整套谎言。容貌焦虑的痛苦,其实只是某些人的生意,允许自己“不完美”,实际上是针对颜值霸权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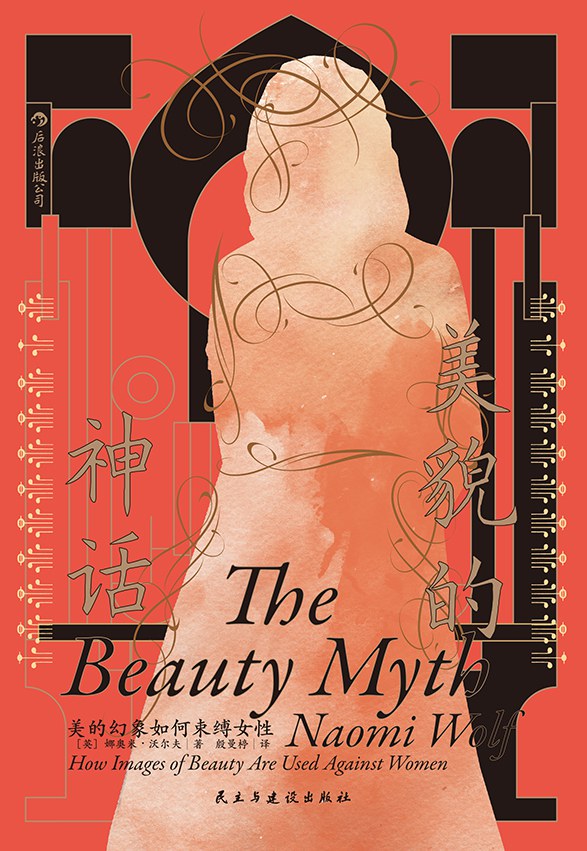
《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
[英] 娜奥米·沃尔夫
殷曼楟| 译
后浪|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5月
30多年后的今天,《美貌的神话》已是当之无愧的“觉醒之书”,被《卫报》列入“改变世界的10本女性主义经典”。它被牛津和哈佛等高校列入性别研究指定教材,因为它引发的社会讨论,促使多家时尚杂志取消过度修图,也侧面推动欧美立法限制整容广告对未成年人的投放,并为反外貌歧视运动提供理论基础。
但容貌焦虑仍然桎梏着无数女性,社交平台上的美颜滤镜、医美广告和算法推送,强化着对“完美”的追求,即使商家对这种完美不可能实现的事实心知肚明。除了消费主义的侵蚀之外,社会的“凝视”也构筑着这道焦虑之墙。社会对女性容貌和身体的规训,依然显得根深蒂固。
束缚女性的枷锁中,对美貌的苛求最为顽固和隐秘
如果基于文明社会的正常价值观,减肥、健身、追求容貌美都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将审美标准单一化,将“身材管理”极端化,就会造成自身的焦虑或对他人的羞辱。
也就是说,批评这种现象,并不是批评“美”,也不是批评“追求美”的某个具体行为,而是批评单一和极端化的倾向。正如娜奥米·沃尔夫所言:“评论者经常或是蓄意或是漫不经心地(但每次都是错误地)认为我宣称女性不应该剃腿毛或涂唇膏。上述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为我支持的是女性具有选择她自己想要的外貌的权利,具有选择她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权利,而不是去服从市场力量以及某个数十亿美元的广告产业所规定的标准。”
在沃尔夫看来,化妆品广告等消费场域对“美”的定义,营造了关于美貌的理想形象,进而让女性相信个体应努力符合这种形象,但这实则是规训女性的社会暴力,不但制造焦虑,也抹杀了过往女性解放曾经给女性带来的自由。
即使到了今天,女性的权利和境况已经大大改善,但狭隘的“美”仍然框死了太多女性的认知乃至人生。女性看似拥有了选择的空间,但不管“是否化妆,体重是增加还是减少,是动了手术还是没动手术,是盛装打扮还是衣着朴素,以及是让我们的服装、脸孔和身体都成了艺术品,还是全然忽略装饰”,真正的问题仍然是“缺少选择”。
但若认为这一切都是消费主义的陷阱,显然是没有对准靶心。《美貌的神话》试图推导出这样一条路径:当女性从家庭生活中走出,争取到工作、选举等越来越多的权力时,“美丽”作为反对女性进步的武器,意图再次控制女性。
父权社会与资本社会合力为女性建立了美貌的标准和规则,中国社会推崇的“白幼瘦”就是典型例子。为这套美貌标准配套的,还有各种衣着穿搭、化妆技巧和修图技巧等。女性获得美貌,就会获得所谓的“资本”,以美貌换取有限的机会、社会关系、虚妄的安全感和自以为的认同感。这些“收获”会让不少女性误以为自己得到了“独立”,实际上仍然处于父权社会凝视的斗兽场,处于残酷的雌竞中。
《美貌的神话》以“工作”“文化”“宗教”“性”“饥饿”“暴力”这6个领域呈现女性在美丽陷阱中的命运。
在职场和社交领域,女性的美貌成为被男性凝视与筛选的标准;在文化领域,广告和大众媒体的刻意渲染和滚动轰炸,使得美貌成为女性的“自我审查标准”;在宗教领域,美貌和“身材管理”被视为“自律”,甚至成为许多女性自我价值认同的来源;在性领域,美貌成为被物化和被羞辱的诱因;至于饥饿,那些瘦身女性在所谓的自律和羞耻感中一次次自我规训,以“抵御”饥饿感;暴力则无处不在,从现实到网络,从嘲笑、恶意评价到“物理攻击”,女性时常会因为“不够美”或“太美”而遭遇各种侵害。
在沃尔夫看来,在此之前,“母亲神话化”“家庭神话化”“贞洁神话化”“被动与依赖神话化”早已先后登场,他们通过强调母亲的“无私奉献”、女性应该对家庭“无条件付出”、女性应该为自己的“贞洁”负责、女性依赖男性所以理应顺从,来实现控制女性的目的。当这几个神话一个个被揭穿,“美貌的神话”便登场了。
早在工业时代初期,“美貌的神话”其实就已经启动。从影印技术到摄影技术,再到其后的影像技术和如今的美颜软件,技术的变革一再加强着“理想美女”的形象固化。
走出家庭、步入职场的女性们,往往还没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才智,便又陷入控制饮食和提升颜值的怪圈。数据显示,时尚模特体重比正常女性要轻23%,追逐模特身材必然导致与吃相关的疾病呈指数增加,当食物和体重破坏了女性心理平衡后,大量神经衰弱症患者出现。正如书中所说,节食是“女性史上最有效的政治镇静剂”。
在女性被封闭于家中的时代,女性的美仅仅源于其行为举止,社会大众也并没有对女性美有过分狭隘的定义和要求,但在“美貌神话”的时代,女性面对的是对外貌的苛求。那些“丑女”“老女人”之类的定义和恶意,是男权指挥棒下的定向伤害,最悲哀的是,许多女性也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物质上的日益丰足并没有让这些女性走向更加独立的一面,反而心灵更加脆弱,很容易遭遇打击。沃尔夫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被营造的恐惧,利用了女性的羞耻心。
当“美貌指数”成为社会的货币体系
沃尔夫认为,现代西方经济非常依赖于女性的持续消费,而这种持续消费所依托的就是“美貌神话”营造的氛围。她继而认为,社会经济的本质是依赖奴性的需要,营造奴性的美好想象,进而使得奴性机制顺利维持,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女性为了满足男性的构想,迎合狭隘的“美”并为之付出一切,放弃自己最不应该放弃的那些东西——比如独立性和尊严。
在这个机制之下,女性的“美貌指数”成为社会的货币体系。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原本是女性权利的关键一步,使众多女性获取经济上的独立,继而争取更多权利。但“美貌神话”引入之后,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和财富往往或多或少由美貌决定。模特、娱乐圈这样的行当自不必说,颜值和身材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第一竞争力,这些舞台上的女性在薪酬体系里会占据相当高的位置。
即使在政坛和公司,美貌也非常重要。1960年代,大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步入西方职场,这被视为改变女性地位的重大机遇,但与此同时,空姐、行政秘书等职业都被赋予性感意味,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甚至成为色情片重要的题材对象,这也使得众多年轻女性被钳制,逐渐接受这些工作岗位的“性感”束缚。
喜欢抬杠的人会举出不少反例,认为总有一些无视美貌神话的优秀女性脱颖而出,但她们付出的努力往往要比同等智力、学历和能力条件的男性或美女大上很多倍。而且得到上位机会的优秀女性,也往往要妥协于社会的美貌需求,引入美貌女下属,以便于工作中的“更好沟通”。女性为了职场竞争,将大量收入投放于养颜等方面,早已是常态。
历史上也是如此。沃尔夫写道:“一个世纪前,正常的女性活动,特别是争取权力的那些被认为是丑陋和病态的,一个女性如果阅读太多,她的子宫就会萎缩。如果她坚持阅读,她的生殖系统就会崩塌”,维多利亚时代会提议人们多去思考高等教育对女性生殖器官造成的损害,公然宣称“延长工作时间会导致女性骨盆畸形”“女性接受教育将会让她们失去生育能力”“一个女性表现出对科学的兴趣,她的性将会出现问题”。
这些宣扬一方面是男性对女性“品质”的要求,一方面也是资本的驱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体系,将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或心理需求都视为疾病,继而让她们求医问药。如今也一样,外科手术时代对“美”的定义,催生了减肥药、整容手术等暴利行业。在美国年增长率达到10%(其他国家甚至更高)的整容行业,实际上提高了女性的痛苦下限。而且这个痛苦并不仅仅是忍受手术本身带来的生理痛苦,还有手术之前的长期自我否定带来的心理痛苦。沃尔夫坦言:“一个健康的身体反应让它避开疼痛。但美丽思维是一种麻醉药,它有能力通过麻痹感觉,让女性更像物体。”
美妆的凝视,诠释面孔与秩序的关系
在《美貌的神话》之后,许多后来者的著作都诠释了所谓“美”对女性的规训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化。
奥地利学者伯娜德·维根斯坦在《美妆的凝视》一书中写道:“柏拉图关于‘美与善’的理想,激发了从十八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发展的美妆的凝视。这种理想引导了对美妆的凝视技术上的利用,以求将异常正常化,其程度之强,以至于内在化的美的理想,时常反映和激化政治和身体上趋于同质和平庸的做法,甚至是对文化、伦理和种族他者性的消除。”
这段看起来艰涩、读起来也颇拗口的话,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直观的呈现,当属美颜镜头下清一色的脸庞。近年来的国产电视剧,常令人有“分不清谁是谁”的感叹,女主女配清一色的脸型和五官,辨识度确实很低。审美的同质化必然造成平庸化,“分不清谁是谁”就是平庸化的体现。
“美妆的凝视”这个书名诠释了面孔与秩序的关系。维根斯坦认为,“美妆”一词的语源可以追溯到希腊语的“KosmetikÓs”,有修饰之意,同时又派生于英语单词“cosmos”,指的是事物由此开始并被准确地赋于秩序。也就是说,“美妆”早于秩序却又与秩序相关。凝视不仅是一种双向互涉的行为,是看与被看的辩证交织,也是一种统治和控制的力量,是主体向他者的欲望之网的一种沉陷。
维根斯坦将“美妆”和“凝视”这两个定义结合后,认为“美妆的凝视”会引发人的身体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决裂。它会加速自我重生,同时也建构自身的媒介性。这个定义同样可以举例说明:一位女性通过化妆、整容等手段“脱胎换骨”,但也因此重新建构了自我形象,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大概率实现人生的改变。
但“美妆的凝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下,人的身体不但被重新建构,甚至也被物化、被规训、被操控,甚至被阶级化,成为社会等级或阶层区分的标准之一。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里也指出,对女性美貌的塑造,实际上是在虚构一种女性换取社会机会的“伪自由资本”,让女性在不平等中通过被凝视换取生存空间。
比如在韩国,化妆简直已经成为“全民运动”,被上升到礼仪高度,使得化妆从自由变成束缚。这种束缚的本质,是将女性自身置于他人的评价体系中。化妆的“强制性”,离不开商业社会的推波助澜,它们制造容貌焦虑,使消费者身陷其中。它更将女性彻底物化,以“不化妆见不了人”的思维操控女性。
在维根斯坦看来,无论专制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异化了“美”。所谓“美妆的凝视”,最终也揭示了人类生存于枷锁之中的残酷事实。当下世界盛行的医美、电视真人整容秀节目等,都让世界变得物化。医美这种技术手段对人的改造,本质上是技术社会对人的全景凝视和操控规训。
《美貌的神话》和《美妆的凝视》都印证了一个道理:美貌神话与女性权力进程始终同步,每当女性权力取得突破,试图撼动社会结构时,社会便会出现新的规训方式。当下的“美貌神话”,使得女性被强制饰演多个职业角色,包括主妇、事业女性和美女等,也导致巨大消耗。即使女性达到了这个要求,女性杂志、美容和药品行业、整容行业等又会制造下一个“女性缺陷”,继而推销新的产品。对于女性来说,服从“美貌的神话”,意味着无休止的内耗。
“服美役”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限制了女性的权利。真正的权利是“可以选择化妆,也可以选择不化妆”“可以追求瘦,但不瘦也不会被嘲笑”……但“美貌的神话”通过“分散女性的精力和时间,让女性无暇去追求性别平等,男性主导的社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加强”。
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里提出了期望:“当一个女性觉得每个女性对待自己身体的做法没有勉强、没有胁迫都是她自己的事时,她就赢了。当众多女性个体让自己免受美丽经济影响时,那种经济就将会开始消失……一旦我们突围并改变了规则,有关自身美貌的意识就不能动摇,让我们歌颂那种美丽,装扮它、炫耀它,陶醉于其中”。
毕竟,“粉饰女性面孔以掩盖其年龄就是抹杀女性的身份、权力和历史”。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