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如果说,读一本好书恰如一次愉快且收获颇丰的精神旅行,那么,读完《中国不高兴》的过程则如同从一个庞大而肮脏的垃圾场经过,让人只想尽快逃离。
林昭死了,遇罗克被害了。摩罗成为了近年来文人样本的又一现实模型。他用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以川剧中的变脸“绝活儿”左右逢源,宣告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在这种转变的背后,现实利益的考量,投机心理的驱使或许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从批判性文人,摇身一变为“民间纵横家”,摩罗非此即彼的个性再次显示出文人思维的单一性和贫弱,这导致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怪王小东、宋晓军、宋鸿兵、刘仰等人为摩罗的“加盟”而弹冠相庆。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奇异文本。
断章取义谬指五四先贤
在早期摩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对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为其《耻辱者手记》所做的序言中,誉之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罗正是以此形象而赢得了一批读者。而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的无理责难固是前无来者,所泼的脏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罗看来,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体西用”论者,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保持了尊严。到了五四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大量中国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大崩溃。“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17页)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之说,把西方文明仅仅视作器物、技术层面的领先,仅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明皮毛。学习西方更为彻底,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跛腿改革“洋务运动”遭遇了失败,恰恰是忽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明成果如宪政、法治等因素而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及其夭折。
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几代人的政治变革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认识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因为中国的宪政改革因为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支持而失败,知识分子这才将目光投向了文化改造和思想启蒙。陈独秀、胡适等人为国民争取自由、民主等权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并加以移植。
在具体的操作上,胡适终其一生都在反对专制,呼吁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言论自由等等。在鲁迅那里,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摩罗赖以成名的《耻辱者手记》,正是从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五四这一代人所作所为,正是摩罗在本书中所说的“内争人权,外争国权”,何曾“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
另一方面,稍具思想史意识的读者均不难想到,从魏源、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后者总是从前者那里继承相应的思想遗产,在前者试错的基础和历史教训中不断前行,显然不可能完全断裂或横空而出。摩罗在梁启超和胡适、陈独秀、鲁迅之间强行画出一条界线,对前者赞誉有加,对后者妄加雌黄,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
而摩罗把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与反省》中的片段,拿来作为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证据,并明显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进行刻意曲解。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写于1928年6月,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参赞安诺德制作了三张图标,第一张表是中国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张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工业状况的比较;第三张是美国在世界上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适比较了美国在生产力上的领先,外国工人与中国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以及招商局文件显示的官员自肥和腐败等现象,然后从物质(生产力)、精神(公德)等方面进行对比,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们的“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显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 他以此为“据”接着对胡适上线上纲,“这种荒谬言论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状态的写照。张三持刀砍伤了李四的头,刑警准备拿办张三,胡适却拦住刑警的手,说,‘错不在张三,全怪李四的脖子不是铁做的。否则不就没事吗!所以,你只能拿办李四。’好一个糊涂的胡适!” 显然,摩罗这样的遗漏是主观的恶意而为之。这种手法,与秦桧为岳飞罗织的罪名“莫须有”何其相似!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翻版。
接下来一段,摩罗继续引用,“帝国主义三扣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不责人……”(23页)接下来的后一句“要自觉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罗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责胡适“糊涂太甚”。
胡适的《答梁漱溟先生》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中国国内的革命与战争现状,而胡适一向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帝国主义。早在1922年10月1日《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后,胡适就说过,“我们很恳挚地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方向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摩罗断章取义和刻意曲解后,对胡适的语境和原意进行了“巧妙”的“移植”。 只要仔细看完胡适的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会得出摩罗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结论。有了往胡适身上“栽赃”的做法,摩罗接下来指鹿为马,用同样的手法解读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对鲁迅进行“精神弑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按照摩罗对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党史专家金冲及(1930年出生)、鲁迅研究专家朱正(1931年出生)、经学史家朱维铮(1936年出生)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学者和文化人都属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可事实却是,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相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摩罗恐怕很难有希望赶上。
另一方面,他们也决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辈人,均属于蔡元培建构学制之后受教育的学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信徒并对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罗对此作何解释?摩罗还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80页),并对文化信心问题危言耸听。而事实却是,不仅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对中国文化信心十足者大有人在。
摩罗在书中称,“五四运动期间刚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爱国主义苗头,这些精英人物立马上阵,扑而灭之。”对于这一问题,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清晰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认为民族国家观念是导致这场世界战争的直接根源,进而将“国家”当成批判,鄙弃的偶像。”(43页)其后,“国家”让位于“社会改造”。
被摩罗推崇的梁启超,早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以为报国者》中认为,“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论述中,‘国家’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550页)“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540页)其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主流,国共两党相继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  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谵妄和语无伦次,却让我相信一个人的思维混乱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谵妄和语无伦次,却让我相信一个人的思维混乱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摩罗引用胡适《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证”是,“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23页),以此指责胡适的“荒谬言论”和“糊涂”,而这一段最后两句“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却被摩罗故意漏掉。
摩罗引用胡适《信心与反省》(24页)中的一段詈骂胡适“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则更是可笑。胡适在该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即“一切所谓发明创造都从模仿来”,并且之后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说明了虚心学习外来文化长处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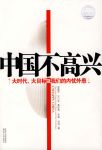 摩罗罔顾作者原意,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摩罗罔顾作者原意,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除此之外,摩罗还指责蔡元培1912-1913年建构的学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78页)。“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80页)
由此可见,对“国家”的厌恶,乃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反省世界局势之后的自动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何来“精英人物扑灭”之说?
另一方面,摩罗宣称胡适等人“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并进行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当他以极端的情绪对五四先贤口诛笔伐的同时,偏激和苛责之处,比五四先贤对传统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之谓也。
- PMI回升利好股市 板块“几家欢喜几家愁” 2010-09-02
- 【独家】微软亚太研发基地扩张 华南总部落户深圳 2010-09-02
- 地方炼厂获政策利好 国家调整燃料油消费税 2010-09-01
- 372家门店 2010-08-31
- 张鸣:吃遗产的败家子 2010-08-30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