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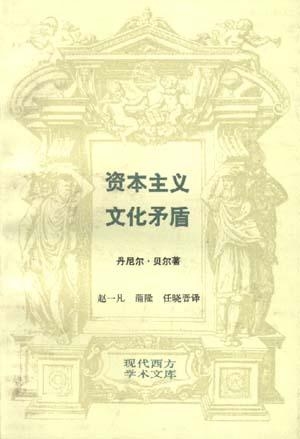 人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文化时,会想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讨论;在讨论未来社会的类型、服务性行业时,也会想起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这一流行颇为广泛的概念;在讨论“左”与“右”的派系斗争时,又会想起贝尔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论。
人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文化时,会想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讨论;在讨论未来社会的类型、服务性行业时,也会想起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这一流行颇为广泛的概念;在讨论“左”与“右”的派系斗争时,又会想起贝尔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论。
但很奇怪的是,贝尔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分析大师,其理论和学术贡献却在专业学科教材内鲜有系统的总结和讨论,人们似乎只是偶尔想起有那么一个喜欢提出各种宏大概念的作者。在著名的乔纳森·特纳的《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社会学》中,丹尼尔·贝尔甚至都没有被正式提起,而在波普诺的《社会学》、马尔科姆·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布莱恩·特纳的《社会理论指南》中也只是稍微涉及贝尔的文化批评。
2011年1月25日,贝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家中去世,享年91岁。人们提起这位逝去的大师时把他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者”。的确,在众多的社会学理论派系里面,贝尔很难被归类,他既不是结构功能论者,也不属于社会学冲突学派,更与所谓的社会学互动论无关,人们只是把他称为“批判的社会学家”。对于涂尔干以降,到帕森斯的功能论,贝尔颇多非议,他强调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分工而增强社会的团结,反而因为分工的细化导致了“角色”和个人的分离,造成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
但是他也不属于马克思以降,到马尔库塞代表的冲突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堕落和感官文化并非单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而是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有关,而且他强调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反作用。不过这种“反作用”也没有让他成为类似布迪厄和吉登斯那种“行动与结构的互构论”,他强调的文化潮流和人性异化的欲望力量对于个人的无情裹挟。而贝尔对自己的定位也颇为暧昧且多属价值立场而无关学术:经济学领域内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另外,或许是贝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气氛的影响,贝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颇为庞杂,而他从来也没有局限于任何一个狭隘的学科之内,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未来学、文艺理论、文学、文化批评,经济学等等都是他的理论来源。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为贝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出版于1976年,这一年,贝尔已经因为1960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声名鹊起,早在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就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所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充满自信且雄心勃勃的学者,他试图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等最优秀的社会学大师对话,并试图打破令人窒息的学科壁垒,恢复19世纪那些思想巨人们宏大的理论气魄。正如赵一凡在中文译本的绪言中所言:“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的崇高地位,建立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在资本主义的批评史中,马克思以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矛盾而著称,韦伯以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著称。所以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露的现代世界“享乐主义”文化鄙陋更像是对韦伯的资本主义禁欲主义精神的反驳。但其实不然,贝尔的理论更像是一个对于马克思物质决定论的回应,并把马克思论述逻辑运用于文化研究之中,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结构中隐藏的必然爆发的经济矛盾,那贝尔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掩藏的必然爆发的文化矛盾。他运用的批判工具既包括康德和韦伯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新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文化困境的中和。而他提出的“公共家庭”却是以熊彼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设想的改造为基础的。不过贝尔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典型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研究,这不仅表现在他把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政治与文化三个体系,并认为三个体系都有独特的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又遵循各自的“轴心原则”。大致说来就是,经济-技术体系遵循效益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政治系统遵循平等原则;而文化系统遵循的是自我欲求的扩张原则。
贝尔也像韦伯一样热衷于文化背后的“意义”和文化行为背后的动机分析。当然贝尔的文化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指的卡西尔所谓的“表现的象征主义”,即“绘画、诗歌、小说或由祈祷、礼拜和仪式所表现的宗教含义,这些都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就是文化系统的自我扩张与经济技术结构中的谨慎和工具理性积累原则之间的矛盾;政治官僚机构必然的等级分层与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自我完满与现代分工的角色异化之间的矛盾。
贝尔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潜藏于资本主义两大宗教基础之上,这一点贝尔借用了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作为资本主义伦理基础的判断以补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观点。按照贝尔的理解,资本主义两大伦理基础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强调享乐的、放纵的、感官的文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攻击。
而在20世纪的60年代,贝尔认为这种矛盾已经被彻底激发出来,最起码是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60年代的文化具有一种新的,也许是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但是贝尔没有交代为何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紧张关系直到60年代才彻底的爆发并趋于消失,它仿佛只是黑格尔辨证逻辑的自然展开。贝尔细致地描述了60年代的文化情绪及其背后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60年代的美国,当艺术的形式盖过内容时,真正的艺术消失了;当个人的感官成为标准时,似乎每个人都是天才;在自我与世界的距离消失之后,连张扬的自我也消失了;飘忽不定而暴力的情绪成为我们的新崇拜,甚至我们崇拜的就是飘忽不定和暴力本身。所以贝尔担心的似乎不是“矛盾”本身,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矛盾的消失,担心涂尔干神圣和世俗的区分的“距离的消失”,“我们能够(是否应该)重建起区分神圣与亵渎的体系吗?”。
这种文化的矛盾扩展至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抱怨,官僚组织的效率原则无法提供价值上的判断,政治中关于平等的承诺也无法在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求文化中得到满足。贝尔对于政治的讨论比较琐碎,黑人问题、世界经济、知识分子的异化、越南战争、私人暴力、青年人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等等都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并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论述。在最后一章中,贝尔讨论了他的“公共家庭”和“财政社会学”的设想。在贝尔的设想中,所谓的公共家庭结合了市场经济和家庭经济的特点,“是满足公共需要和欲望的媒介,与个人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
贝尔主张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财政社会学”,主张经济的再分配,并认为它不仅要提供资本的积累,也要满足政治合法化的需求。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变成威廉·詹姆斯所谓的“道德性替身时”,却没有人愿意为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负责。而个人的欲求又在文化自我的影响下不断膨胀,人们开始不再信仰政府的所作所为。在贝尔看来,如果不想求助于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此一矛盾,“公共家庭”就是唯一的出路。它一方面限制个人的欲求,一方面也满足个人的自由。
很难给贝尔的理论给出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就像他给自己的价值定位那样,显得颇为多情而暧昧,现实的描述与未来的预测相互交杂在一起,价值判断与经验研究也并非那么清晰。他想用简单的理想类型来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同时又不想错过借鉴任何一个有创意的理论见解。尽管如此,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他对现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意义解读和动机分析,还是常常让人想起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天才式研究。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