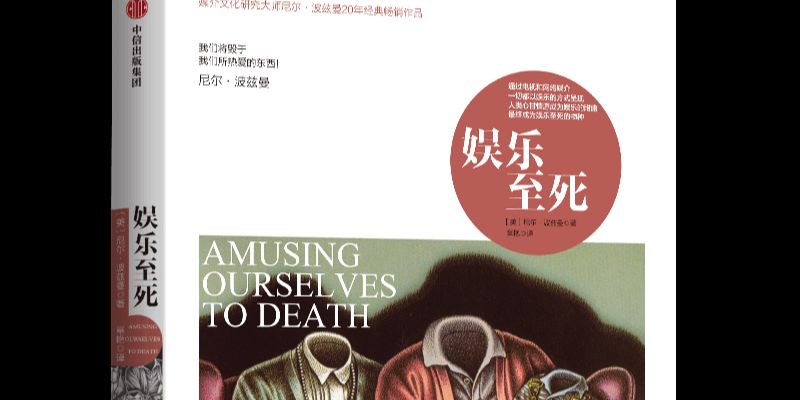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
过去四十年间,媒介领域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三级跳”:从广播电视时代的“接收”,到PC时代的“搜索”,再到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推荐”,技术的更新与信息的膨胀共同编织出大众文化的光鲜图景。
算法推倒了专业机构与大众之间的高墙。任何公共话题都能成为爆点,透过屏幕,人们一次次围观,一遍遍狂欢。
连最严肃的事物都在被攻克。特朗普也许是最具娱乐效应的政治人物,每一天,都有海量用户在其社媒底下聚集,或大肆吹捧,或百般嘲弄。但放眼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政客正在加入这一行列,其原因也很简单:娱乐化真的有效。
距离尼尔·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奥威尔的预言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赫胥黎的预言则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事到如今,已有完整的一代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抛入了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哪怕有人已经有意识地与狂欢保持距离。
究竟是我们选择了娱乐,还是娱乐重塑了我们?我们还有没有再次选择的权利?
值此《娱乐至死》出版4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冠军老师为本书写作了一篇书评,谈谈四十年来的变化,和我们当下的处境。
以下为吴老师的书评全文。
1984年,辩论舞台上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面对电视镜头金句迭出,赢得全场笑声。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其出版于1985年的经典名著《娱乐至死》中,并没有分析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政治学界的关注),而是聚焦里根如何倚靠电视屏幕上的“幽默剪辑”来击败对手。波兹曼提醒我们看到:在电视镜头下,政治辩论变成长镜头特写、段子金句与声调管理。这位媒介生态学创始人警告公众:严肃的日常现实会被电视场景化、情境化、娱乐化,而政策讨论则会变成脱口秀桥段。
波兹曼深受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后者的核心学术贡献,便是提出了“媒介即信息”这个重要命题,亦即,社会总是更多地受到媒介之“性质”的塑造,而不是媒介上的内容。波兹曼则进一步提出,媒介是一门“隐形课程”。我们以为是具体的内容在教坏年轻人,但其实,媒介本身就在“教”坏他们。
如果说技术指的是机器和硬件系统的话,那么,媒介就是技术创造的社会和知识环境。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技术中立”本身是一个神话,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电视屏幕的默认姿态,便是朝娱乐方向倾斜、追逐最大黏性,若不主动设计“减速带”,公共领域终将变成综艺舞台,政治则变成“演艺事业”(show business)。电视的基本特征是不连续性,而不是连贯性,电视屏幕呈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波兹曼已观察到:书籍正在被电视所取代,沉迷电视屏幕的年轻人无意愿也无能力阅读任何书。距离《娱乐至死》的出版,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今天,人们只要一睁眼,触目可及处皆有屏幕,各种尺寸的屏幕——屏幕已从中产阶级的客厅走向每个人的手掌中,乃至眼镜中。当年波兹曼在时代广场夜幕中瞩目观瞧并促发他写作《娱乐至死》的那块巨屏,今天依然伫立并且分辨率变成了8K。波兹曼曾深有洞见地指出,里根时代竞选广告把复杂政策浓缩进30秒短片。而今日的竞选营销,则直接把政策议题变成“#挑战话题”或“#表情包梗”——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八秒竞选短片”风靡TikTok,政治纲领被拆成表情包+口播金句,配上快剪鼓点,候选人在八秒内控制你的眼睛。
曾长期担任真人秀《学徒》主持人的特朗普对镜头语言的强大掌控(尤其是独特的表情管理与身体姿势、言语风格),使得其政治对手(不管来自共和党内还是民主党)纷纷败下阵来。特朗普每条社媒帖子都具有“爽文”结构与语法,爽点暴击带动巨量推送。公众沉迷不断刷新的刺激而无暇深究事实。特朗普以高频社媒轰炸维持议程主导权,也迫使反对者在同一节奏里应战,于是整个公共领域都被裹挟进“高密度—低深度”的信息闪击战,人们的注意力被切成无数碎片,再难完整地追踪任何复杂议题生长。
2025年1月20日,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尚未散场,便签署第14172号行政令,要求内政部长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洲湾”。该行政令的法律效力尚待国际法确认,但它的传播效力却已即时兑现:白宫官方账号推送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挥毫签下“美洲湾”行政令的20秒短片,配着劲爆鼓点在社媒平台秒级刷屏,在TikTok当日获得1200万播放,相关话题“#GulfOfAmerica”霸榜热搜。场景化的身体动作进入屏幕即产生情绪价值,司法正当性却不被看到。政治学界在激烈辩论此举是否算是构建某种无视法律的“话语主权”抑或“外交霸凌”。波兹曼主义媒介生态学分析视角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当特朗普主义政客把该“重命名”行为包装成了可被不断转发、剪辑、配乐的“视觉钩子”后,该行为的法律争议很快被彻底覆盖,没人再去关注。
波兹曼把媒介视为一种塑造思维的隐形课程,它教人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讨论公共事务。在《学徒》这个爆款综艺节目(2004~2017,特朗普于2015年退出)里,特朗普与剪辑师们共同发明了一种三幕式语法:夸张对抗→高光时刻→“You're fired”的瞬间决断。他随即把这种语法带进政治舞台:政治辩论变身火药味十足的收视大战,总统记者会则被压缩为“十秒金句制造机”。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上,特朗普在社媒平台上自诩“国王”“超人”——这些政客不再假装进行理性争论,而是精明地把公共事务转化为角色扮演。担任美国的总统,变成了想尽办法当好一个超级媒体明星;椭圆形办公室本身亦已变成一款7×24小时在线的“娱乐—政治操作系统”。今年7月17日,《华盛顿邮报》用“世界正被屏幕噎住”这个标题来概括波兹曼四十年前的洞见,惊叹于这本书的持续穿透力。
媒介的“娱乐至死”逻辑并未过时,反而在平台算法加持下被推向了极致。
波兹曼关心的并非“媒介好不好”这样的二元框架下的价值判断。他关注的是,作为认识论的媒介(media as epistemology)如何悄无声息地重组人们的世界观与精神气质。“媒介即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介,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组织和改变我们思维方式与认知能力的力量。在生成式AI时代的当下,这个力量比起四十年前更要强大得多。
2025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签下《下架法案》(TAKE IT DOWN Act),这是一部直接针对“深伪”(deep fake)影像的美国联邦法律,它要求平台在48小时内下架非自愿的合成影像,并将故意发布者列为重罪 。同年7月20日,特朗普在其本人创建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转发了一个视频短片,在第44秒处显示特朗普和奥巴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随后三名穿着联邦调查局夹克、戴着墨镜的男子抓住奥巴马并将他拖倒在地,坐在旁边的特朗普则面露笑容,然后视频切换到奥巴马在狱中身穿橙色连身衣狱服。这个特朗普亲自转发的视频,引发主流媒体一整天的连环辟谣。真相的澄清速度已明显赶不上谎言的复制速度,深伪技术把“看见即相信”变成“看见也要怀疑”,公共理性被迫在怀疑与疲惫之间摇摆。
媒介即认识论。媒介形态决定民众如何用什么方式“认识世界”。四十年前波兹曼已担忧电视会把政治争论简化为“谁的形象更迷人”,而深伪技术则让“形象”本身可被随意生成、随时撤换。事实的存在感被稀释,“现实感”退化为不断生成与片刻即逝的视觉体验。以1992年著作《理性公众》为学界所熟知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夏皮罗,在其2022年文章《谎言、弥天大谎与美国民主》中这样评论道:“自2016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获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被公开表达,并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如此显眼。”
夏皮罗认为,当下美国政治学中的辩论已经变得可笑:政治学家辩论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公众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单方面利益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否是不平等的”。然而,谎言在电视屏幕与各种社媒平台肆无忌惮的蔓延,使得“公众意见”本身被操弄与扭曲。
夏皮罗认为自己早年提出的“理性公众”概念,已然毫无价值,被当下公众“关于真相的分歧”有效地瓦解了。
波兹曼四十年前就曾提出:当信息以爆炸性数量溢出,筛选与整理成本将转嫁给受众。若无相应的批判技能,信息就像糖衣——甜而空洞。而在出版于2024年的著作《智人之上》里,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仍观察到一种“天真的信息观”在盛行:“这种观点认为,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能得到力量与智慧。”
持有这种“天真信息观”的代表人物有贝拉克·奥巴马、扎克伯格以及雷·库兹韦尔。这些当代美国政经界精英认为,只要信息足够多、自由讨论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谷歌的使命宣言简洁地表达出了这种天真信息观:“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
然而,信息数量堆上去,却并不意味着就能抵达真相,更不意味着谎言会无所遁形。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深具洞见地提出:“真相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介的性质。”而电视屏幕的“性质”,便是具有娱乐化的倾向——它自动奔向娱乐,除非我们主动设计别的可能。
那么,算法支配、深伪横行的社媒平台的“性质”呢?如下事实,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该媒介的性质:特朗普将他所创建的那个社媒平台,称作“真相社交”。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