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9-06 01: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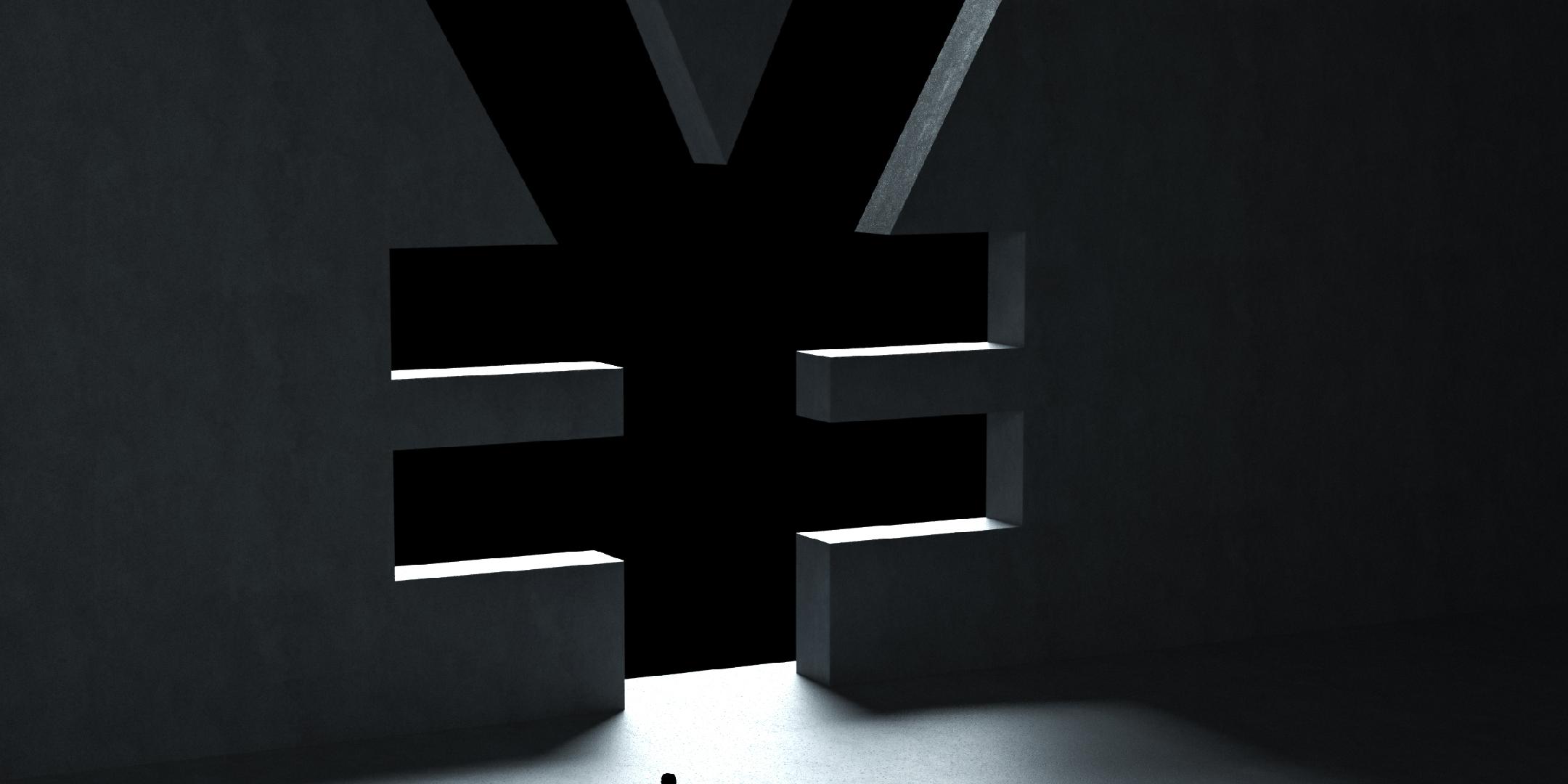
缪因知/文
今年,我国出现了两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首案”——上市公司内部人因违反增持承诺和不减持承诺,被法院判决赔偿数百万元。这两起案件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等敲响了“承诺不可轻做、不可轻违”的警钟。
这两个首案处于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前沿领域,其反映的追责趋势是否会进一步扩张,又是否应有合理限制,值得深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与文中提及的任何公司、个人及其亲友、员工、代理人均无往来。
增持承诺不兑现:视同虚假陈述
2021年6月15日,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兼总裁袁某、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罗某计划在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亿元。此后,金力泰两次公告称,袁某、罗某的上述增持承诺履行期限分别延期至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2022年9月30日,金力泰公告称袁某、罗某未能在延期期间完成增持计划。同年10月20日,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对袁某、罗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同年12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对袁某、罗某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2024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将本案作为首例因上市公司董监高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引发的证券侵权纠纷案件予以受理。原告刘某某、郑某某主张,他们因上述股份增持承诺购买了金力泰股票,该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要求金力泰、袁某、罗某共同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等共计900余万元。
被告辩称,他们已按照规定及时将增持意愿、资金筹措情况以及因资金筹措困难导致延期等情况书面告知金力泰,因客观上履行能力不足,无法再履行增持承诺,不存在主观上“忽悠式增持”的故意或过失。对此,公司也及时发布了公告。股价下跌主要是由于市场整体及企业自身经营等其他情况导致,并非两被告不履行增持承诺所致。
2025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开承诺涵盖股份限售承诺、业绩承诺、股份增(减)持承诺、分红承诺、股份回购承诺、法定义务重述承诺等多种类型。不履行公开承诺的法律责任属性无法一以概之,应结合承诺主体及内容、相对人是否确定、未履行承诺的原因、承诺主体的过错等因素综合考量,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典型证券侵权行为,也可能无法归入证券特殊侵权范畴,抑或构成违约行为。
对具体行为应结合增持行为特点、承诺的行为性质、承诺时的履约准备、延期事由、未履行承诺原因等综合判断。袁某、罗某在首次作出增持承诺时并无资金准备,在后续延期过程中也未积极筹措资金,且在面对交易所质询时,以过桥资金制作“虚假”存款证明,故难以认定其有增持的真实意愿。从增持主体、承诺增持金额、市场影响力等角度看,这一公开增持承诺信息的披露,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预期产生了严重误导,虚假陈述行为成立且具有重大性。换言之,法院认为这两位高管并非真心准备增持,增持未兑现是主观而非客观因素所致。
至于公司,法院认为其尽到了基本的审查义务,亦无证据证明其明知或应知袁某、罗某存在虚假陈述,故不应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损失核定,一审判令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赔偿两原告投资损失 506130.96元、277406.42元。而且,由于本案采用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审理,后续还会有不少其他原告提起的同类判决会参照此判决结果。
本案在责任定性层面争议较小。在定量层面,两人实际增持0股,属于100%未履行承诺,不存在减轻责任的理由。法院将不履行增持承诺视为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利好信息。承诺到期未履行后,本案又属于股价下跌的典型场景。所以,法院在利好信息破灭时,要求承诺人赔偿投资者“买高卖低”导致的损失,逻辑较为通顺。后续出现其他案件同类判决的概率较大。
不减持承诺被违反:可以进行场景三分法吗?
需要注意的是,金力泰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新证券法新增的第84条第2款。该条款行文较为宽泛,其内容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任何承诺未来都有可能招致赔偿责任或赔偿诉讼的风险,比如控制人、董监高承诺完成某项并购重组,甚至承诺守法合规。
和增持股票承诺最接近的,当属不减持的承诺。从法律构造上而言,承诺增持但未履行,和承诺不减持但未履行,本质是一样的。股票和一切商品的基本规律是供求影响价格。有人承诺增持,股价就有向上的动能;有人承诺不减持,股价就有维持的力量。除了资金因素外,董监高、实控人等内部人的承诺,也会给外部投资者带来一定的信心。一旦打破承诺,股价就会下跌,这与吹嘘公司利润有1亿元,但后来被揭穿的情况类似。
此前,对于违诺减持的行为,一般追究行政责任。相关行政罚款虽然金额不菲,但与民事赔偿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尚无投资者提起赔偿诉讼的案例。不过,已经出现了由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特殊约定,而判令违背不减持承诺的股东赔偿的案例。
2025年7月发布的南方某省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审判白皮书中,第一则案例就涉及减持承诺的赔偿判决。法院称之为“上市公司诉股东违反限售承诺民事责任第一案”,甚至认为该案“对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证券违法行为非法收益的认定均具有参考意义”。
该案中,禾某公司于2017年上市时,公司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董事夏某在招股书中承诺:上市36个月后的两年内(即第四、第五年),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上市前股份数量的15%;如违反承诺提前减持股份,应向投资者道歉、回购同等数量股份,并将减持收益返还给公司等。
2019年8月,夏某和妻子丁文某离婚,夏某将630万股股份转给丁某。一般来说,限售股份由于离婚、继承而转归他人,未必一定会伴随限售义务的转变。但本案中,丁文某出具承诺函,确认继续遵守夏某之前做出的限售承诺。2021年7月至11月,丁文某违反限售承诺提前减持股票,减持价款约5100万元。2022年,该上市公司依据上述限售承诺函诉至法院,要求丁某向公司返还违规减持股份价款。
法院审理认为: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自愿作出的限售承诺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律规定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虽然法律未必明确要求违规减持需承担何种具体责任,但违规减持行为本身具有不当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东承诺违规减持收益归公司,上市公司据此要求该股东支付违规减持收益的,应予支持。
值得疑问的是,应当向公司返还的违规减持的股款如何计算。法院认为:违规减持股票收益的计算方法并不唯一,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确定。违规减持行为发生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股价下跌。此时,违规减持收益的计算方式可以是“违规减持所得”和“合规减持应得”之间的差额。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高位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8元,那么违规减持收益就是2元。
第二种情况是股价上涨。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高位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12元。从结果看,股东提前卖出是吃亏了。不过,有些公司给股东的承诺模版里会写:如果违反不减持承诺,就在若干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将所持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若干个月等。
法院认为可以参照限售承诺人在回购义务产生之日应付出的回购成本和其违规出售股票价款之间的差额确定违规减持收益,该差额是限售承诺人得以避免的一项支出,可以作为确定其收益的参考依据。比如,减持后股价在10个交易日内涨到11元,股东违规减持后本应承诺在10个交易日内赎回,但坚持不回购,就产生了每股1元的违法收益。
本案即是如此。2020年7月28日为限售起始日,交易均价为7.76元/股;2021年7月28日为被告股东减持起始日,交易均价为18.64元/股;2021年9月18日公司发布的《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指出丁文某违诺减持;2021年11月18日减持终了日,交易均价为39.18元/股;2022年7月27日(限售期满日),交易均价为37.64元/股。
2021年7月28日至2021年11月 18日期间,丁文某累计减持3065200股,减持所得金额75744958元,均价24.71元/股;其中合规减持即本来就能减持的股票为945000股,所得金额24323870元,均价25.74元/股;超过合规比例之外的减持股票数量为2120200股,所得金额51421088元,均价24.25元/股。
一审法院认为丁文某应该在公司公告指出其违诺减持之日(2021年9月18日)起,按照此前10个交易日内回购的承诺,不迟于第10个交易日(2021年10月12日)的交易均价为基准,计算出其所得收益为6926365.51元〔(超比例减持年度所得股票额75744958元÷卖出股数3065200股—2021年10月12日成交额91840000元÷2021年 10月 12日成交量4282700股)×超比例股数2120200股〕归公司所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未将丁文某合规减持的股票数量和所得款予以剔除,所以按照违规减持所得51421088元减去回购义务产生日(2021年10月12日)丁文菁应付回购价款45457088元(该日股票成交均价21.44元/股×违规减持股数2120200股)计算,酌定违反限售承诺的收益为596.4万元。根据限售承诺,其应向公司返还该笔收益。
第三种情况是违规减持价格和后续股价持平。法院认为,此种情况下可以参考违规减持价款的资金占用费确定违规减持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算法的逻辑并非完全一致。第一种股价下跌的情况指向股东“偷跑”的违法收益,相对容易理解。
第二种股价上涨的情况中,违规违诺减持股东并无明显法定的回购义务。如果不曾承诺回购,就不能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如果说同样是违规违诺减持,有承诺回购的股东有违法收益,未承诺回购的股东无违法收益,这似乎也不通。
而且,股东承诺不减持和回购在前,减持行为发生在后,承诺甚至减持时当然无法预判未来股价。如果在股价上涨情形中原告和法官拿回购说事,那么在下跌情形中,做过回购承诺的股东是否也能主张按照“回购义务产生之日应付出的回购成本”计算呢?
甚至,如果股东在股价下跌后的确回购了股票、补足了原来的持股量并承诺继续锁定,难道就不能“洗白”了吗?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8元,违规减持收益是2元。后来又于限售期满或未满时的9元价位时回购补足数量,能否主张实际违法收益最多是1元?
第三种股价持平的情形其实和股价上涨的情形一样,未必不能说违规违诺减持并未产生对股价的不当压力。就算这是违法行为,也不一定有重大性作用力和对他人的实际损害。
坦率地说,本人不太理解“违规减持价款的资金占用费”标准。新老股东都是用自有资金买股票,没有占用公司资金。违规违诺减持所得的股价款也不是来自公司,而是来自其他投资者即接手这些股票的买主。如果没有这笔减持,那笔资金当然还在其他投资者手里。但现在有了减持交易,原股东卖股得钱,就算提前占用了新股东的资金吗?
的确,股价不涨不跌,新股东买了个寂寞,这笔投资不算很成功。但说违规减持的股东占用了新股东的资金,这算是一种有新意的说法。一分钱没出过的公司去收取这笔“资金占用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好在证券公开市场交易是匿名化的,没人知道违规违诺减持股东的接盘侠是谁。如果违规违诺减持是通过大宗交易之类给特定人的,该新股东回头起诉公司要求拿那笔“资金占用费”,法官又该如何回应?
更宏观的一个问题是:法律规则应当有一致性的逻辑,而上述三种计算方法的逻辑有待统一。为什么股价持平才考虑资金占用费,股价下跌或上涨就不考虑了?为什么股价上涨和持平时不考虑回购义务标准?
三种情况三种算法,给人一种未必正确的感觉,似乎就是为了寻找收益而寻找收益,总之一定要找出某种收益以便判令赔偿,而不是依据一种客观平实的计算方法,不带预判地去计算有没有收益、有没有损害。这个思路一旦打开,违诺不增持的案例也会变得更复杂。
增减持赔偿责任应有合理限制
近年来,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张,法院对于在各种新型案例情形下确立首案也颇有积极性。但无论如何,审判都应当遵守法理法律,并注意利益的平衡。
法院接受新型案件,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纠纷。但案情是特定化的,法律是中立的,并非每一个场景的首案都必须给出有责结论,才是值得一提的首案。依法指出特定情形下无责,同样是一个有益的首案。法院必须依照法律判案。如果法律本身规定得不够周全,哪怕存在漏洞,法院也不一定要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去在个案中“惩治坏人”。否则,以后遇到近似案例时,就不一定能自圆其说。
违诺不增持或减持是近年才出现的边缘性、新型证券违法案型,其危害程度未必比得上财务造假等传统硬核的虚假陈述情形,对此应慎重处理。
首先,应当合理看待具体增减持行为的作用力。违背承诺自然是不对的,违背承诺的行为者一般也会承担来自监管者的行政责任,并非可以轻松避责。但民事侵权责任依法需要以因果关系、过错等因素为基础,也应当考察相关行为本身有无重大性。
中国的虚假陈述赔偿制度本身适用了大量推定,如推定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决策造成了影响,推定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故而在适用时应当有合理限制。小股东(如持股1%以下者)违背诺言不增持或减持的行为,或者相对于公司市值案涉金额不大的行为,或者承诺未完成比例较低(如低于10%)的承诺,本身对市场交易和其他投资者决策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如破产、失业等)而非因主观过错而不能履行承诺的,也可予以免责。
其次,对于违反承诺案件,应当优先允许当事人以继续履行承诺的方式来纠正行为的影响。财务造假之类的传统虚假陈述做出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改口来完全消除影响。但增持减持和其他很多类型的承诺未必不能通过补充履行、矫正履行(如回购),特别是及时实施此类履行来弥补,此时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再追究赔偿责任,除非投资者能起诉证明延迟履行承诺本身造成了一部分独立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事实上,违规违诺不增持或减持的行为本身存在着实际作用力,对股价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传统虚假陈述。比如对于虚报利润,可以推定后来的股价下跌源于此等不实信息被揭露的作用力。但说增持却又不增持,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无资金托举,而不能全部怪罪于此前陈述的信息不实。
证券价格说到底是取决于其价值基本面,不能只靠内部股东的托举。如果基本面不行,仅靠内部股东增持或不减持,反而会制造虚假繁荣和未来股价进一步崩盘的风险。只是由于我国的董监高和内部股东股份限售制度异常严格,独冠全球,所以内部股东的增减持仿佛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基础性制度”。此中的法律问题辨析较为复杂,限于篇幅,暂不展开。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