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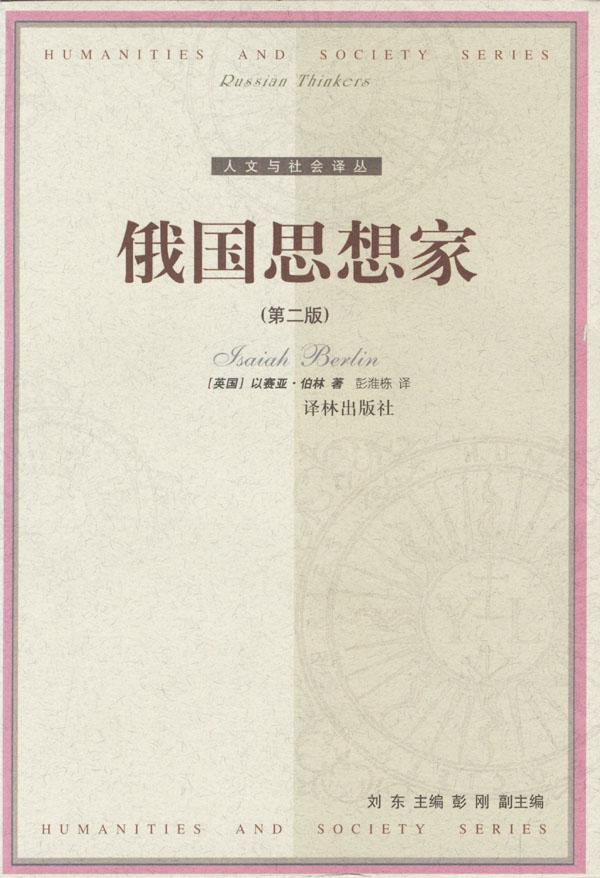
1
1836年,因为一篇文章触怒了俄国政府,《望远镜》评论被勒令永久停刊。当局也没有放过在文章里严厉抨击俄国文化和制度的作者恰达耶夫:警察将他软禁在家,宣布他“已经疯了”,严令禁止关于他的任何公开讨论。可恰达耶夫毫不屈服,他依然刚正不阿,风骨凛然,一直持续到1849年。
那一年,他已经不再是警察严加看守的“登录在案的疯子”,但有一天却忽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歌颂起沙皇的“英明果敢”来了。而且,当得知赫尔岑在海外出版的一本书里称赞自己后,恰达耶夫迅速给警察头子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被这种卑鄙的、声名狼藉的人赞扬,实在是感到“恼怒和耻辱”,并一再强调自己对尼古拉一世忠心耿耿,绝无贰心。这位著名的异议分子忽然变得如此卑躬屈膝,就连他亲密的侄子都对此迷惑不解,问道:“何故自贱如是?”恰达耶夫回答:“不得已,蝼蚁尚且偷生。”
2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里,把1848至1855年那段时间称为“十九世纪俄国蒙昧主义长夜里最黑暗的时期”。在那8年里,就连恰达耶夫这样的自由斗士,都被寒冷的西伯利亚平原和高高的绞刑架吓得肝胆俱裂。黎明遥不可及,“革命的多头怪兽”发出越来越沉重的喘气声。
是否反抗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反抗。此时,俄国“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已流亡或被流放、杀戮和噤声。虽然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恪守良知,但他们已经不能重新凝聚成一股独立于政府和民众之外的力量,大多数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被逼成了革命党,连原来最温和的知识分子也是。
当独立的“知识阶层”瓦解后,剩下占人口95%的不识字的农民,如哈耶克所说,往往“更倾向于接受破坏性强的任务——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或是对别人幸福的嫉妒——远胜于接受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对非我族类者的杀戮,是所有志在激发群体运动的学说的必要成分。”而且“最容易煽动的是那些对某一观念半懂不懂的人,他们最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并形成整体,因而是极权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
3
这时恰好有一个德国人的主义,它兼具数学班精确的逻辑和无可辩驳的道义魅力,迅速俘获了许多民众和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更严格地说,是马克思的学说加上列宁“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纲领的综合体,用阶级把“同志”和“敌人”截然分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无调和的余地;它继承了黑格尔“正题与反题的冲突是进步的原因”思想,认为矛盾冲突是历史的推进器,所以暴力和革命是值得歌颂的,指责它的残酷和不人道,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罢了,改良主义则幼稚得很;它认为历史是遵循永恒规律的,找到后只要沿着它的轨迹走就行了,地上的乌托邦是可以据此被建造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起的却是宗教的作用。尤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苏联,它对那些几乎陷入绝望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而言,不啻于黑夜中茫茫海面上唯一的光亮,带领他们穿过迷雾,绕过尖锐的悬岩和凶险的暗礁。可是,那时有几人知道,在夜晚发亮的不一定是灯塔,还有可能是独眼巨兽的眼睛。
4
伯林很少著文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往往借由爬梳其他思想家著作的方式。他的再阐述往往比原著清晰易懂,但绝不是为了重温或浅说,而是为了解构与重组。伯林在《哲学与政府压制》一文区分了两种思想家,一种“重新阐述了问题”;另一种“做得恰好相反,即当发现某种情形下对问题的某些武断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他们就以某种强烈震撼的手段颠覆了原来的综合。”他自己无疑属于后者,与大部分思想家关心“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该怎么往那里去?”不同,伯林更关心的是:“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
比如在《俄国思想家》里,他就以一个流亡的俄国后裔的身份,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俄国推翻了沙皇专制后,又建立起了列宁所说的“接收了沙皇主义再加上一部分的苏维埃”的极权主义政权?
他把目光投向1830年至1848年,此时德国浪漫主义传到了俄国。其要义是:任何时代纷繁的表象下,都有一个内在规律。人类的所有观念都相互关联,都受某个一元的精神、理念或绝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是一个连贯、持续、能以理性分析的发展历程——这股思潮最早由黑格尔开启,并从孔德、马克思、斯宾格勒延伸到汤因比。不可否认,它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史研究。但要用它指导现实的话,正如汉娜·阿伦特认为,就正好为极权主义打下了根基,因为“极权主义法制就是藐视合法性,而通过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来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司法。它从不考虑对具体的个人适用与否。”
最早引进这种黑格尔式思想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斯坦科维奇(Nicholas Stankevich),一个现在已几乎被遗忘的名字,他的一个追随者是大名鼎鼎的巴枯宁。后者有一句名言:“先把地基清理出来。”至于清理完后建立什么制度?他认为现在不用管,到时自然有答案。革命的炮火中必然会诞生一个和谐、有序、平等的政权。只要掌握了历史规律,一切都不是问题。
然而,伯林却借由分析托尔斯泰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历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我们不能像牛顿发现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一样找到历史的定律。人所能获得的“历史经验”其实只是一连串外在的重大政治或公共事件,只是真实“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至于每个普通个体的内在生活,则是一概阙如的。在占有这么点资料的前提下,不管是谁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脉络与走向,都是一种僭越——认为人可以像神一样洞察一切,把有限的人摆在供奉无限超越性存在的神坛上。此时启蒙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非理性。
赫尔岑也是黑格尔史观的坚定反对者,他说:“历史很少重复自己,它只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而已。历史总是同时叩响几千扇门,最后到底哪一扇会开,有谁知道?”“把目标订得太过遥远其实就是没有目标,就是欺骗,真正的目标必须是切近的如果人真的只是朝向某个预定目标迈进,那就不会有历史,只剩下逻辑。”
赫尔岑没想到的是,1880到1890年间,将他视为先驱的民粹派,却已几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历史服从规律的学说。但他们做了些许改变,认为资本主义阶段不是如马克思所说那样不可跳过的。而且,即使民众尚未开化,民主革命也可以成功。尽管如此,民粹派的理念比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理念还是更接近马克思的原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们保留着对个人自由的坚定信念,即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布尔什维克,这点已经荡然无存。
在梳理思想史的过程中,伯林发现:很多思想家的学说经过一代代信徒们的微调,往往有可能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所以他认为,思想家无力为他们的学说在后世造成的影响负责,谢林、黑格尔、马克思那批一元主义者也是。虽然在二十世纪,那些打着他们旗号的人,像荷尔德林说的那样,“在试图建造人间天堂的努力中,把一个国家弄成了人间地狱。”
5
伯林毕生以多元论对抗一元论,以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他经常著文讨论一些相对冷僻的思想家:赫尔德、维科、马基雅维利等,其目的就是勾勒出西方思想史上与主流一元论相对的多元论思想。多元论认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终极答案。不同的善之间也并不一定相互兼容。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完全有可能走向矛盾冲突。
不是所有的善,都应该或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可是,那些有强烈价值追求的人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伯林在担任牛津大学教授期间,一次演讲时曾引用熊彼特的话,对此作出了回答:“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依然矢志不移,这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本质区别。”我想,这句话其实是有条件的:可以用来为你的信仰作牺牲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有必要的话。但绝不能强迫别人为你个人的信仰而牺牲,无论这信仰本身听上去有多么崇高。
- 买的要比卖的精 2011-04-15
- 以萨米亚特之名 2011-04-14
- 西方?什么是西方? 2011-04-11
- 贫瘠世界的挖掘者 2011-04-01
- 丹尼尔·贝尔:夹缝中的大师 2011-03-29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