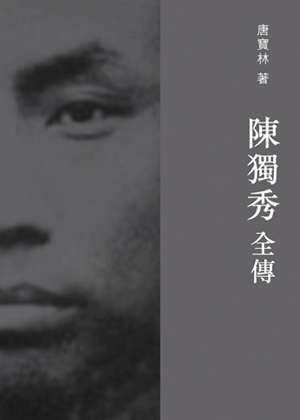导语:陈独秀的棱角,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鲜明标记,而这也是他作为政治人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从人格的角度来说,这种棱角是风骨,是儒家所谓“浩然之气”。从政治家的标准看,这是大忌。相比中共其他领导人,他没有周恩来的坚忍,没有朱德的谦和退让,没有毛泽东的强韧,棱角只让他自己在现实的挤压下鲜血淋漓。个性让他成为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也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y 张耐冬
鲁迅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如果孔子、佛陀、耶稣等“圣人”再生,也会被门徒们迫害打压,等他们死去再作为偶像抬出来。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为众人所不容的清醒者,被迫害也成了他们集体的命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如孔子、佛陀和耶稣一样在死后被神化为教主、供奉为偶像。在历史学家称为“极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纪,更有清醒者们先被众人心悦诚服地推为偶像,后因政治原因被矮化、被侮辱,乃至遭千夫所指的怪现象。
“陈独秀”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我们对其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课本里毫无生气的定性,而这定性大抵是负面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身上的若干标签:“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托派”。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类基本问题,却回答不出。
教科书里,“陈独秀”是一个思想不断退化、最终被时代洪流所抛弃的可悲角色,同时这一角色也带给我们离奇的诡异感:为何这位启蒙的导师,一手缔造中共并成为初期党首的陈独秀,居然接连犯下“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最终成为“反党”之“叛徒”?在旧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只能认为他原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无法坐实这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2011年,《陈独秀全传》出版,将这位近代中国“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生完整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唐宝林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有关陈独秀、中国托派历史的研究,曾任“陈独秀研究会”秘书长。1989年,他就以“从秀才到总书记”与“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为题,出版了《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此次《陈独秀全传》的撰写,是在三十年研究的基础上重理思绪,再次为陈独秀这位“终生的反对派”立传。
谈起这本书与此前观点的区别时,年过七旬的老先生直言,最初进行陈独秀研究时,他接受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中国托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后来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研读和采访当事人,他改变了看法。接触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后,他发现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陈本人对此并不赞成,中共在大革命中失败的最大责任在共产国际而不在陈独秀。再如《陈独秀全传》中对中国托派怀着救国理想进行不屈奋斗的精神表示同情,并认为托派人士对中国社会的很多认识具有预见性,对托派作为中共反对派的历史意义提出肯定,也是唐宝林对早期观点的修正。
此书问世前,关于陈独秀的传记作品并不算少,但大部分属于政治人物传记,对陈氏的非政治经历不求甚解。这类传记中的陈独秀,一般只有半张脸——“革命”或“妥协”的政治面孔。大部分传记也是以其在新文化运动至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对陈早期活动、晚年思想关注不多。
原本加给陈独秀的,有所谓“十大罪状”: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这十条罪名,有些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贴上的标签,有些则是政治敌手泼来的污水。莫须有的罪名容易清除,因立场不同被加上的称号不易去掉。因为伪造的罪名可以通过历史学考证的方式辨明真相,而立场差异戴上的帽子只能在政治学或党史编纂学范畴内解决。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十大罪名中的“主义”类词汇已经不再是关注的对象,而“汉奸”“叛徒”一类涉及到民族、国家范畴的罪名,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在涉及到陈独秀政治活动的章节,《全传》对标签进行一一驳正的段落,使得《全传》看上去不大像一部单纯的人物传记,也兼有史家论著的风格。对一般读者而言,叙事已足够。《全传》中的驳正内容,无疑是出自史学家撰写论文的专业习惯,这又与读者的阅读习惯有一定差距。若是作者辟专门章节,将批驳对陈独秀不实评价的文字汇集在一处,也许将使全书整体上更为协调。
读者希望看到的有些内容,也许不在作者的专业考察范围,故而点到为止,读来不甚尽兴。比如陈氏晚年时,为其诊疗的医生程里鸣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氏未直接回应,但以“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在半开时”一联相赠。此种意味颇值得仔细斟酌,比如陈氏是否以此来对自己半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总结?还是他对自己书生从政之举略有悔意?或是对自己后半生的祸福荣辱的感怀?读者总想看到对此联的评价,可作者未置一词。
真实的陈独秀,并非只是“党史”或“革命史”中的人物,因此他的很多人生选择,都出自其个性,而非百分百受到时代洪流的左右。据其晚年回忆,“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这一自述,足可以对其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态度做出一定的解释,而不完全归咎于中共建立初期经验的匮乏、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决策等理由。
另外,他自称“性情暴躁”,这一点却一直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人们往往只在一些轶事上谈到他的性格,诸如他收到沈尹默的诗作,直接跑上门去指责其字体“其俗入骨”,正体现了他直率冲动的性格,但对这种性格在他进行人生中重要问题的抉择方面的影响,却并不注意。其实,陈独秀在面临人生难题时,常有一种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惯性思路,如组建中共,是在北大以教务长取代文理二科学长(即对陈文科学长一职的实际解除)以后;转向托派,是在其遭遇党内处分、被解除中共党首职务之后。这种思路与他易冲动的个性有何关系,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并未受到关注,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单纯以革命史的角度作出的解释,即他的选择都是所谓大形势的变化驱使的,陈独秀个人并无太多转圜的余地,如此一来,陈独秀便成了革命的螺丝钉,除了完成自己嵌入某个具体时代任务的使命之外,再无作为人的个性可言,甚至连个人情绪都没有,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陈独秀棱角分明,且常有意气用事之举,这一点在1933年国民党开庭审判其“危害民国”的案件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陈氏故友章士钊为其辩护,章氏提出应由国民党与陈氏为首的中国托派联合“清共”,是为其脱罪,他竟拍案而起,当场直斥章氏之说。面对个人之生死,陈独秀尚且如此,又怎会在建党、组织托派等问题上全然没有个性的作用?
陈独秀的棱角,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鲜明标记,而这也是他作为政治人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从人格的角度来说,这种棱角是风骨,是儒家所谓“浩然之气”。从政治家的标准看,这是大忌。相比中共其他领导人,他没有周恩来的坚忍,没有朱德的谦和退让,没有毛泽东的强韧,棱角只让他自己在现实的挤压下鲜血淋漓。个性让他成为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也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既然是不合格的政治家,为何偏偏要选择政治?这是陈独秀一生最大的问题,也是所有评论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陈独秀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天才,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启蒙者,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假若没有成为职业革命家,他会成为大学者,也可能成为观察家与评论家。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他应该是卢梭,而不应该成为罗伯斯庇尔。可是,在20世纪上半叶,卢梭偏偏要兼任罗伯斯庇尔的角色,这也是陈一生中最奇诡的事。
回到陈独秀生活的时代,他的选择不足为怪。当时投笔从戎者甚多,若不参与革命只以启蒙为业,难入时代主流。作为陈北大时期的挚友,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积极参与政治,作为其早年的相识,刘师培这样的大儒也曾是革命者。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成为那个时代知识界的共同选择。于是,并未亲身参与政治的鲁迅,在去世后除了“文学家”、“思想家”外,也被加上“革命家”的头衔。
由知识精英充当政治家,不但是中国传统士人情怀的延续,也是近代中国尴尬的现实。从康梁变法开始,为变革而号呼奔走、为革命马革裹尸的,往往是知识精英。
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就无法让更多人了解启蒙者的思想,而启蒙者的思想得不到充分推广,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空想。陈独秀们的尴尬在于此。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很深刻,对时局常有惊人预见,可是他的应者寥寥,甚至还引起同道者不满,更不用说乡间父老。知识精英与普通国民的沟通不畅,于此可见一斑。
但卢梭终究无法成为罗伯斯庇尔。正如《陈独秀全传》所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时代,和共产党的毛泽东时代。蒋借着党国体制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毛则发动农民组建革命军队,政治强人取代启蒙者,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启蒙者,陈独秀都是落败者。
与陈独秀同样命运的,还有与他“道不同”的老友胡适。作为五四时代的思想巨人,胡适同样走上政治之路。虽不像陈独秀为此潦倒半生,但也伤痕累累。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中败下阵来的陈独秀,最终对政治的认识与胡适殊途同归。强调民主、强调健全代议制度,反对强权与专制,让这对在政治中分道扬镳的战友在思想上再度会师。不同的是,胡适从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中体会到中国实行民主与代议制的必要,陈独秀则是在个人的政治失败中痛定思痛,强调民主与反专制对中国的意义。
陈独秀去世后几年,同样基于亲身革命体验的乔治·奥威尔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1984》。虽然时空相隔,但其对民主与专制、议会与独裁等基本政治问题的见解,与陈独秀如出一辙。
真实的陈独秀,在政治上不成功,在启蒙上有局限,在性格上有缺点,但真实而丰满。同时,一个被贴满各种“主义”标签的陈独秀也存在着,并对公众产生影响。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1830年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作为一位与现代社会有密切关连的人物,陈独秀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是党史编纂学的对象,出于政治角度对其定性无法避免。但这些定性多少与陈独秀的真实形象吻合,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任务,也是公众了解陈独秀的要求。
耶稣曾对圣彼得说,鸡鸣之前,你将三次不认我。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遭遇北大解职;作为一手创立中共的党魁,被开除出党;作为中国托派的首脑,受到托派成员的孤立。三次大起大落,最终以晚年的凄凉收场,令人掩卷叹息。因其特立独行,注定要像卢梭那样独自吟行于河畔;因其思想深邃,注定要成为被抛弃的先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by 张耐冬
by 张耐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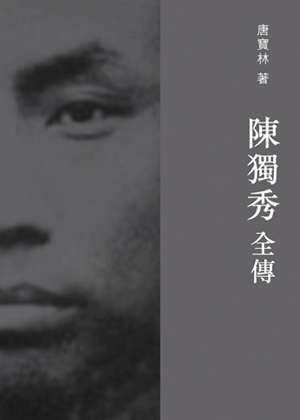
书名:陈独秀全传
作者:唐宝林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鲁迅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如果孔子、佛陀、耶稣等“圣人”再生,也会被门徒们迫害打压,等他们死去再作为偶像抬出来。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为众人所不容的清醒者,被迫害也成了他们集体的命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如孔子、佛陀和耶稣一样在死后被神化为教主、供奉为偶像。在历史学家称为“极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纪,更有清醒者们先被众人心悦诚服地推为偶像,后因政治原因被矮化、被侮辱,乃至遭千夫所指的怪现象。
“陈独秀”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我们对其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课本里毫无生气的定性,而这定性大抵是负面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身上的若干标签:“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托派”。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类基本问题,却回答不出。
教科书里,“陈独秀”是一个思想不断退化、最终被时代洪流所抛弃的可悲角色,同时这一角色也带给我们离奇的诡异感:为何这位启蒙的导师,一手缔造中共并成为初期党首的陈独秀,居然接连犯下“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最终成为“反党”之“叛徒”?在旧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只能认为他原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无法坐实这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2011年,《陈独秀全传》出版,将这位近代中国“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生完整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唐宝林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有关陈独秀、中国托派历史的研究,曾任“陈独秀研究会”秘书长。1989年,他就以“从秀才到总书记”与“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为题,出版了《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此次《陈独秀全传》的撰写,是在三十年研究的基础上重理思绪,再次为陈独秀这位“终生的反对派”立传。
谈起这本书与此前观点的区别时,年过七旬的老先生直言,最初进行陈独秀研究时,他接受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中国托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后来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研读和采访当事人,他改变了看法。接触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后,他发现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陈本人对此并不赞成,中共在大革命中失败的最大责任在共产国际而不在陈独秀。再如《陈独秀全传》中对中国托派怀着救国理想进行不屈奋斗的精神表示同情,并认为托派人士对中国社会的很多认识具有预见性,对托派作为中共反对派的历史意义提出肯定,也是唐宝林对早期观点的修正。
此书问世前,关于陈独秀的传记作品并不算少,但大部分属于政治人物传记,对陈氏的非政治经历不求甚解。这类传记中的陈独秀,一般只有半张脸——“革命”或“妥协”的政治面孔。大部分传记也是以其在新文化运动至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对陈早期活动、晚年思想关注不多。
原本加给陈独秀的,有所谓“十大罪状”: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这十条罪名,有些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贴上的标签,有些则是政治敌手泼来的污水。莫须有的罪名容易清除,因立场不同被加上的称号不易去掉。因为伪造的罪名可以通过历史学考证的方式辨明真相,而立场差异戴上的帽子只能在政治学或党史编纂学范畴内解决。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十大罪名中的“主义”类词汇已经不再是关注的对象,而“汉奸”“叛徒”一类涉及到民族、国家范畴的罪名,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在涉及到陈独秀政治活动的章节,《全传》对标签进行一一驳正的段落,使得《全传》看上去不大像一部单纯的人物传记,也兼有史家论著的风格。对一般读者而言,叙事已足够。《全传》中的驳正内容,无疑是出自史学家撰写论文的专业习惯,这又与读者的阅读习惯有一定差距。若是作者辟专门章节,将批驳对陈独秀不实评价的文字汇集在一处,也许将使全书整体上更为协调。
读者希望看到的有些内容,也许不在作者的专业考察范围,故而点到为止,读来不甚尽兴。比如陈氏晚年时,为其诊疗的医生程里鸣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氏未直接回应,但以“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在半开时”一联相赠。此种意味颇值得仔细斟酌,比如陈氏是否以此来对自己半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总结?还是他对自己书生从政之举略有悔意?或是对自己后半生的祸福荣辱的感怀?读者总想看到对此联的评价,可作者未置一词。
真实的陈独秀,并非只是“党史”或“革命史”中的人物,因此他的很多人生选择,都出自其个性,而非百分百受到时代洪流的左右。据其晚年回忆,“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这一自述,足可以对其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态度做出一定的解释,而不完全归咎于中共建立初期经验的匮乏、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决策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