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学鹏/文 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里面,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面,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
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是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其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不仅创新者得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的话,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现在,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出场了。
一
首先,阿吉翁认为“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他认为,创造性破坏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这篇论文最核心的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而是受到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地漠视、打击、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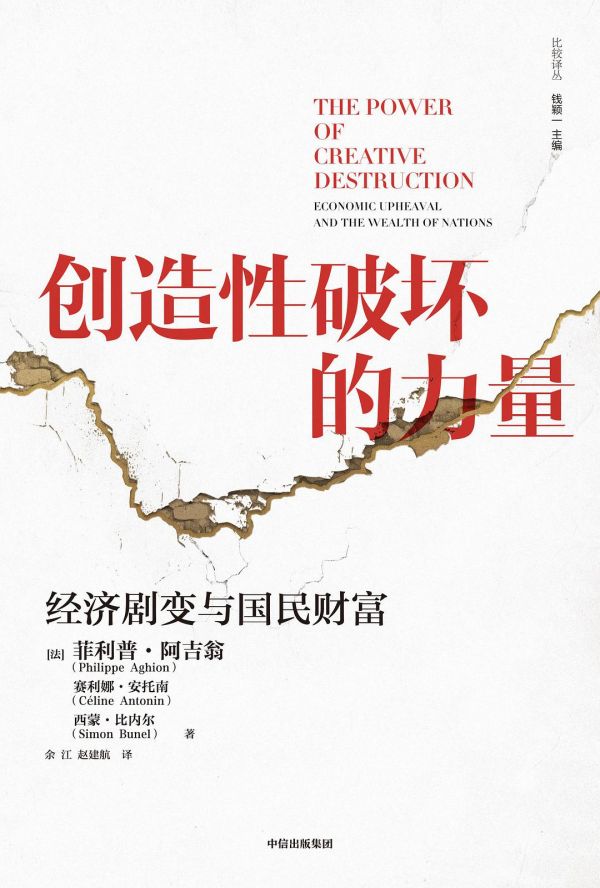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菲利普·阿吉翁 赛利娜·安托南 西蒙·比内尔 / 著
余江 赵建航 / 译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就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蒸汽机于1712年被发明,但50年后才被大规模应用,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最初,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但它是一个好例子。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也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但2011年4G网络开始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应用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而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与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再次,当基础创新不够强大,还没有广泛的应用时,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学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兴衰》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也是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体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王兴和整个社会都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后,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微信。所以说,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新进入者发动的,在位者也会观察、也在思考、也在创新。但的确很多远离前沿的企业不创新,他们就都死去了。所以,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列昂剔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机器正在不断替代人力,于是他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失业会越来越多。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悲观循环,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机器人的结合,再一次出现了对劳动大规模替代的问题,要不要对数字经济征收更多的税、要不要对机器人征税变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是灵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巨大的进化适应性,只不过,在浪潮2阶段,需要政府出手,需要政府来平滑这一阶段的“不适”,这是政府的责任。
二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产生了更多社会财富。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拿普通理发师的服务来说,众多创新企业得到更多的利润,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企业附近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增加了这些暂时没有发生创新部门的收入上涨。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创新产生的“额外”财富征税,缓解失败企业的员工的痛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标准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救助补贴制度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阿吉翁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政府要做投资型政府,对创新负责。
很多人会说,创新应该主要靠企业或者市场,怎么能靠政府?创新的本质是那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推动创新。他们是商人、是科学家、是发明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天才群体。而天才不是完全根据人口规模同比例产生,而是根据殷实家庭的规模同比例产生。背后的含义是,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橄榄型社会,做大中产阶级规模,让教育公平化,从源头部分增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另外,政府也要帮助大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非短期功利化”的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厚度,这样也会推动“浪潮1”尽快发生,因为浪潮1对应的是基础创新的突破,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通过企业来完成。
当然,这对政府也提出了“要求”,它得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能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捆绑的政府、不能是一个被游说势力操纵的政府。它要有开放性、要有透明度、也要受到监督和可问责。政府还应该是一个投资型政府,尤其是对国民教育进行投资,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坦率地说,就是投资“浪潮1”。
三
现在说说我对这本书另外一个体会:品位的重要性。
简单来说,到底是什么支撑了经济学的基础?底经济学要如何观察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
法国经济学家显然占据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不平等和创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之一。他“击中”了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痛点,引发了无数普通人内心的共鸣。而创新则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响亮的标语,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痛点,它推动了无数普通人建立自己的小企业。同为法国人的阿吉翁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他似乎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共融性,他刻画创新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讲述市场主体博弈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学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是被刻画成一个不变的外在力量,而是一个应该和市场、企业、竞争、和知识扩散同步“运作”的物种,政府也是一个进化的物种。这个物种进化要适配市场、企业和社会。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而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是什么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
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一场致病疫霉的水霉菌的“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导致100万人饿死,使得土豆在当时成为经济学家嘴里的“吉芬商品“:尽管价格上升,但人们反而还要多买一些囤积着。
同样的原理出现在政府这个“物种”中,如果是世袭制、终身制或者有限准入秩序,整个政府体系没有阶层流动,没有智识上的多样性、没有感同身受的多样性、没有跨越阶层的多样性、没有信息交互上的多样性。那么它就会被某种“病毒”毁掉,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多么尊贵和正确的“品种”。就像考拉或者猎豹一样,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很低,一直处于生物灭绝的边缘。
阿吉翁对创新浪潮的阶段化全景描述,在我看来,也有一种生物学气质。出现创新就像“基因变异”一样,新基因被引入基因库,但新基因不一定立即存活,或者立即壮大。这取决于基因的漂移和选择。如果能够克服适应问题,这些基因没有被清除,这种基因突变就会持续存在并且扩散,从而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以此标准重新来看待一些经济学家,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伟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两者品位不一样。哈耶克更高一些。米塞斯对人的规定是一种“先验性规定”;对政府的看待是一种“永恒恶魔化的角色”。在他这里,人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基本属性一样的物理人口;政府也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一个“永不悔改的恶魔“。所以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缺乏本源思考的自由主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姿态主义。而哈耶克认识到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系(其实缺乏“生物多样性”)。而市场经济和民主则没有这样的“硬伤”。同样的道理,芝加哥学派虽然也有很多教条的部分,但明显好于老凯恩斯学派。因为老凯恩斯学派的举动仅仅是一些“搅动”,不会增加“基因多样性”。
最后,谨此缅怀《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作者,刚刚逝世的杰出学者E.O威尔逊,他承受了很多的误解。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