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9-05 16: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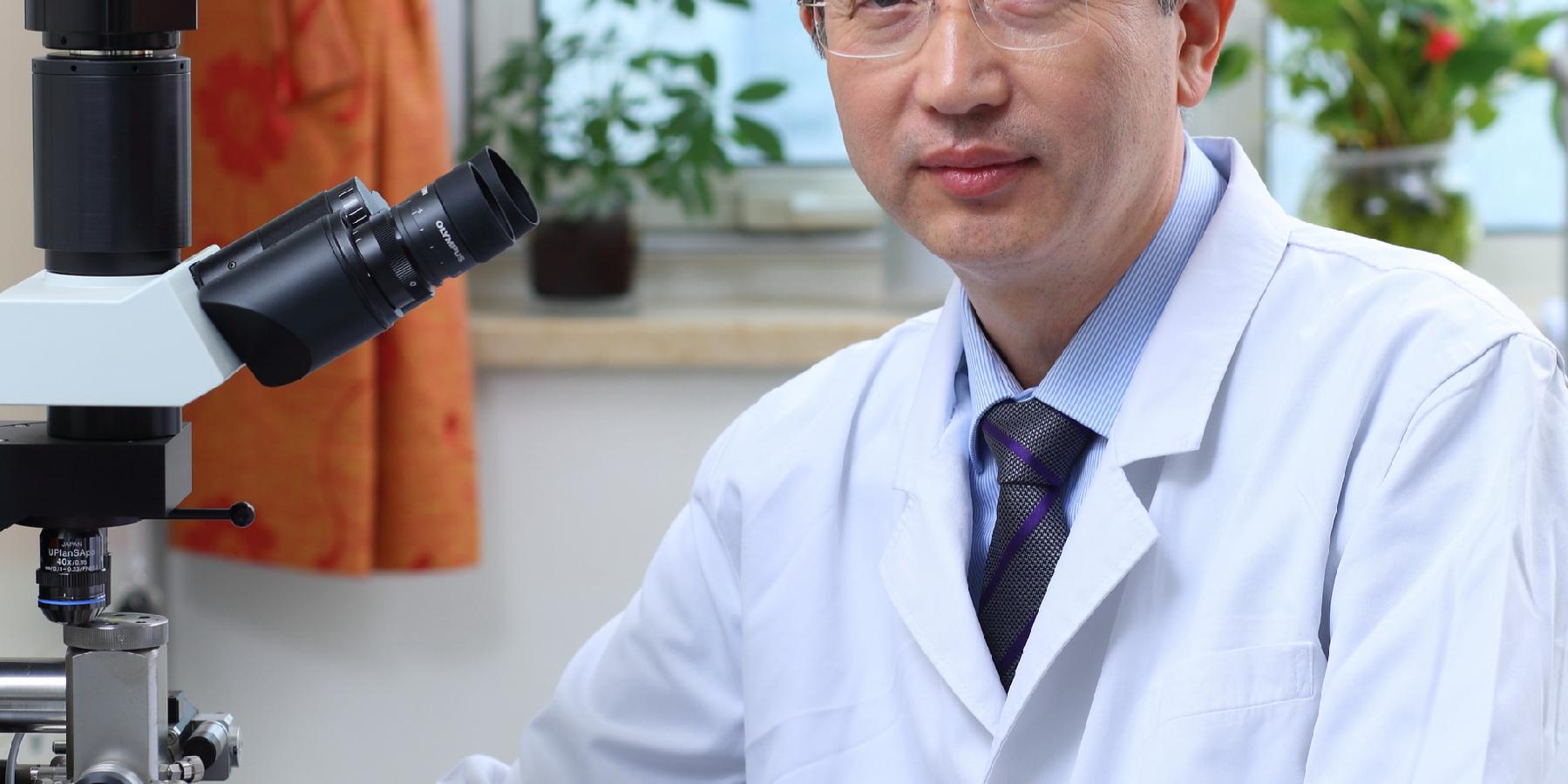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渐冻症专家樊东升记得他的很多病人。
8月29日,“2025北京榜样”公布,樊东升第一时间看到了名单,里面有他一位病人的名字: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创始人、“渐冻勇士”刘继军。
这是樊东升第三次有病人进这个榜单了。2012年,身患渐冻症仍坚持公益事业的设计师王甲被评为“北京榜样”。2022年,京东集团原副总裁蔡磊也被评为“北京榜样”,那是樊东升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病人。
樊东升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国最早开始渐冻症研究的专家之一。二十多年里,他接诊渐冻症患者逾万人,建立的渐冻症患者数据库有超过5000名患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渐冻症患者的医生。
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起病人时,樊东升语调柔和,不紧不慢,这也是他出门诊时的样子。坐在病人对面时,除了叮嘱他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那么焦虑外,他总会再给一粒“定心丸”,比如“你的情况总体还是好的”,比如“你的病发展没那么快,没那么糟糕”......
渐冻症被称为“最残忍的罕见病”,患病后,人会因肌肉萎缩逐渐丧失运动能力,身体像慢慢被冻住,所以患者也被称作“渐冻人”。除了蔡磊,物理学家霍金、人民英雄勋章获得者张定宇也都罹患渐冻症。在1869年被提出并命名后,人类和渐冻症的斗争从未停止,至今,现有疗法仅能有限延缓疾病进展,无法治愈渐冻症。大多数“渐冻人”生存期只有3—5年。
在不欺骗患者的前提下,尽量传递希望。对濒临绝望的人来说,医生的声音很轻,力量却很重。
从走进诊室并最终确诊开始,患者就成为樊东升战壕里的新战友。最近这两年,樊东升能传达给战友们的力量更多了,除了规范化治疗和安慰,他可以对越来越多的患者说:我们正在进行新药临床试验,或许你可以入组。
“当把所有治疗都用上,效果也不令人满意时,临床试验就给病人带来新希望。”樊东升说。
寻药
8月底一个上午,在樊东升牵头的多学科诊疗(MDT)门诊,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渐冻症患者对樊东升说,自己很想参与中国的一项新药临床试验。
最近,樊东升接诊了不少海外病人,甚至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患者。他告诉记者,许多海外病人前来,是希望加入在北医三院开展的一项新药临床试验,这款药由他和清华大学教授贾怡昌及神济昌华团队共同研发,今年8月14日刚刚被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试验。
“为什么外国病人会来?实际上我们这个研究的机制比较清楚,试验结果很明确。”樊东升说。
科学家早已发现,人体内一旦出现一种被称为FUS点突变的基因,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渐冻症,患者往往在两年左右迅速去世。十多年前,贾怡昌尝试将含有FUS点突变的基因敲入小鼠体内,小鼠却始终不发病。贾怡昌最终发现小鼠体内一种叫Trim72的基因有效阻止了小鼠发病,去除该基因后,小鼠出现了渐冻症症状。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渐冻症在研药物SNUG01诞生了。樊东升全程参与了这款药的临床研究。2023年5月,在正式IIT研究(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被批准之前,樊东升为一名病情严重到已经不符合临床试验入组条件的患者进行了同情给药。他说:“按当时的疾病发展情况,患者可能两三个月就不行了。现在,两年多过去了,他还存活着。”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目前同时有近10项渐冻症新药临床试验在北医三院开展,其中有跨国药企在中国开展的全球多中心研究,也有中国药企自主研发药物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几乎都由樊东升牵头。这些在研药物中,既有中药,也有小分子药物,还有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药物。
越来越多的新药研究正为“渐冻人”带来解冻希望。但在数年前,这种热闹是难以想象的。
十几年前,北医三院还没有开展过任何渐冻症新药临床试验。2014年,“冰桶挑战”公益行动让渐冻症被很多人了解,但中国渐冻症新药研发依然很少。2019年,蔡磊确诊渐冻症,这之后几年,他参与推动了一些新药管线向渐冻症的倾斜,一些原本不做渐冻症研究的科学家也把目光投向这里。
在全球,新药研发是一件公认极高难度的事。相比常见病,渐冻症新药的研发难度还会指数级上升。过去数十年,在人类前赴后继的渐冻症攻坚战中,只有“两个半”药物顺利诞生,一个是赛诺菲的利鲁唑,一个是日本三菱制药的依达拉奉,此外还有渤健的只对2%病人有效的托夫生注射液。
无数制药公司、科学家的尝试已经以失败告终。从概率上讲,当前在研新药最悲观的结局可能是,没有一款能顺利摆上药架。
但樊东升不这么认为。他注意到,经过长期努力,神经退行疾病研究正迎来突破期,已经有药物能真正延缓老年痴呆症发展。渐冻症比老年痴呆症进展更快,在临床试验中更易观察到用药差别,这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研发投入更快完成试验。叠加政策偏向、资本投入,渐冻症新药突破是很可能出现的。
几乎和蔡磊的大声疾呼同时,中国政府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了罕见病,推出一系列对罕见病药物评审审批和支付有利的政策,这让资本和企业更愿挑战渐冻症新药这种高难度、高风险的领域。
中国渐冻症新药研究起步比欧美晚至少十年,不过,庞大的人口基数给罕见病临床试验带来了独特优势。渐冻症全球患病率仅约4.5/10万,在欧美,由于病人少,渐冻症新药研究开展困难,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就曾有两项渐冻症新药临床因受试者不足被迫终止。中国约有20多万名渐冻症患者,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这让中国医生能更从容地为每种药物找到优质的受试者。
樊东升介绍,为应对入组难问题,欧美药企不得不进行“平台试验”,像共享单车那样去共享对照组。比如,5个临床试验原本各需100例实验组和100例对照组,共需1000个病人,在“平台试验”上,它们将使用同一个对照组,只需要600个病人即可。
共享对照组让临床试验得以尽多开展,但用这种办法研究不同机制新药的准确性不高。樊东升说,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言,渐冻症或许只是一种疾病,他们只需要医生为其招募一定数量的病人入组就行了。但对医生而言,病人和病人千差万别。
“什么试验用什么样的病人,是有讲究的。”樊东升说,渐冻症致病原因不清,异质性很强,这意味着有的药物也许对这个病人有效,对那个病人就无效了。到底什么病人最适合某个组,依赖医生的专业判断。
有的药和炎症机制有关,樊东升就会挑选对免疫反应更明显的年轻患者;有的药主要对大脑起作用,对脊髓作用较小,他就会找脑损害较重、肌肉萎缩较轻的患者;有的药主要针对周围神经,肌肉萎缩较重的病人就会更适合参与试验。
疾病的复杂,让病人和医生的价值在新药研发中凸显出来。精准入组最直接的结果是,临床试验的阳性率可能被提高,这意味着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病人,战友
每位病人入组前,樊东升都会交代:药物还在研发,有效没效还不知道;临床试验随机双盲,可能用的是安慰剂。
他也会强调,即使如此,入组也有意义:在试验中,病人可以得到医生对呼吸、营养的密切管理,这至关重要。另外,药物一旦被证明有效,即使是安慰组病人也有机会在药物上市前用药。
每年,樊东升会为至少500个新病人下渐冻症诊断。很多医学同行在碰到疑似患者时都会说:“到北医三院再看看,一是最后拍板,二是看那儿有没有新治疗手段。”
从全国各地来的“渐冻人”不断涌向樊东升的门诊,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有新药吗?能试药吗?
8月26日,一位患者家属在诊室门口等候樊东升,“其实我来找医生,是希望能让弟弟试药,可惜医生说我弟弟的呼吸、肺功能情况已经达不到入组条件了。我们都很想参加临床试验,起码能有生的希望”。
许多人把渐冻症视为绝症,把确诊等同于“判刑”。樊东升说,医生不能因为病人怕就不下诊断,不诊断就无法治疗,这会让病人的身体机能像自由落体一样掉下来。
“不是每个病人都是存活3到5年,现在生存5年、10年、20年的病人很多,每个病人都有好的一面。”樊东升说,得病是事实,但强调好的一面能给病人建立信心,做好早期治疗很可能获得较长生存期。缺乏经验的医生会认为确诊就无解了,说不出每个病人有什么不同,樊东升会把有根据的好消息挑拣出来,给病人抓得住的希望。
病人的离开,是渐冻症医生不得不面对的遗憾。樊东升更愿意去看遗憾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病人成为“渐冻症斗士”,和他保持长期联系:刘继军患病19年了,通过良好的康复和照料,他经常能戴上呼吸机、坐着轮椅出门转转,看看云彩和鲜花,西安病人张红带病生存超过20年,王甲确诊也快20年了,还有很多生存超过10年的病人。
这些病人在自助之外,还帮助着其他病友和人群:
刘继军和妻子王金环创办了东方丝雨渐冻症关爱中心,为病友争取了许多政府政策和医疗康复资源,给困难家庭提供呼吸机和免费药品,还代表中国和国际病友交流;
南通籍舞者葛敏在确诊后成为渐冻症公益者,她把病友写的东西集结为两册《因为爱,所以坚持》,每次出版,樊东升都会专门写序;王甲靠眼控仪写完20万字自传激励病友对抗病魔,还用稿费成立“王甲渐冻人关爱基金”;
曾在北大青鸟担任高管的“渐冻人”张红,在陕西成立渐冻人互助协会、组织病友活动,还给希望小学捐款......
在众多与渐冻症抗争的病人中,蔡磊是走得尤其远的那一个。除了公益活动,他还在推动渐冻症药物研究中起了巨大作用。
蔡磊的分型属于连枷臂综合征,这种分型原本可以有较长生存期,但他的进展却比樊东升预料中更快。“他特别拼,我们会让病人好好休息,但他全身心投入渐冻症事业,这对病情不利。”樊东升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我尊重他。”
2023年7月,樊东升和中国科学院药物所教授高召兵、清华大学教授贾怡昌联合研究团队在《细胞研究》发表封面文章,介绍渐冻症研究最新发现。樊东升建议用蔡磊的个人照作为杂志封面,在那张照片中,蔡磊昂起头站在金色的荒漠下,迎向太阳光的方向。由于杂志不接受真人肖像,这款封面没被采用。

“我们这样做是想向蔡磊致敬。”樊东升说,蔡磊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成功呼吁上千名病人同意病逝后捐献遗体,这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难得。作为医生,要和刚确诊的病人提遗体捐献话题,他总是难以开口。病人确诊后就离开了医院,往往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刻,没有和医生表达捐献意愿的机会。
大脑和神经系统组织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科学家可以尝试通过遗体标本追溯疾病源头。长期以来,中国科学家只能在老鼠身上做基础研究,动物和人之间隔着的巨大距离,会制约科学研究发展和新药研制。很长一段时间,樊东升只遇到过一个捐献遗体的病人,那是北师大一位教授。现在短短几年间,已有超过10位“渐冻人”完成了遗体捐献,成为珍贵的科研资源。
患病后,蔡磊很快意识到患者数据库的缺乏,是制约渐冻症疾病研究和新药研发的重要因素。确诊一个月后,他找到樊东升,说想做一个渐冻症患者的大数据平台。
这和樊东升多年的心愿不谋而合。做渐冻症研究头几年,医院没有电脑系统,病人一离开医院,数据就消失在人海中。20年前,樊东升找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计了一套数据库体系,此后20年里收集到超过5000名渐冻症患者数据,成为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中心渐冻症数据与样本库。不过,由于随访困难,这些数据不够动态,不少患者逐渐和他失去联系。
作为互联网老兵的蔡磊,在樊东升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全新数据平台,所有患者可通过平台自主上传病情信息,实时更新用药效果和病程进展。一两年内,这个平台就收集到了上万个真实数据,这是樊东升过去20年收集数据的两倍。樊东升对这些数据做过初步分析,和医院掌握的数据情况基本一致。
“最直观的价值是,只要在这个平台发布临床试验信息,大家都来报名了,入组速度非常快。”樊东升说。

找希望
樊东升出身于医学世家,爷爷、父亲都是医生。1984年,他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医疗系,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
选择神内,是樊东升觉得与大脑相关的医学很烧脑,也很酷。不过,20世纪80年代针对神经免疫类疾病治疗手段的匮乏,很快让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1987年,他选择进入北医三院神经内科,成为那里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神经医学专家康德瑄。
北医三院是骨科很强势的医院,收治从全国各地来看颈椎的病人。一天,一位骨科医生在闲聊中说起,他在颈椎病门诊发现大量被误诊的病人,做完颈椎病手术后,病人不见好,还继续加重,最后发现他们其实得的是渐冻症。这位医生对康德瑄和樊东升说:“能不能帮我鉴别开来,在手术前就告诉我那该是你们的病人?”
原来,颈椎病和渐冻症会有一些共有症状,比如肌萎缩、上肢下肢麻木僵硬。当时全球范围内都缺乏渐冻症的诊断标准,能识别它的医生很少,一些患者在做完颈椎手术后,反而出现说话不清、吞咽困难的症状。
在康德瑄的建议下,樊东升开始寻找线索。在遍寻北京市各个图书馆后,他发现一篇以色列文献中提到可通过胸段的椎旁肌区分颈椎病和渐冻症,因为前者的胸段很少出现退行性病变。
这给了樊东升启发。不过,只有较晚期的渐冻症患者才会出现胸段病变,这种方法难以用于早期诊断。经过一番研究和思考,樊东升想到,脖子上的胸锁乳突肌或许是更好的“钥匙”——它不会被颈椎病影响,但渐冻症患者此部位的肌电图会有明显反应。
答案就这样被找到了。樊东升发表在硕士期间的这篇论文,获得了199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通过胸锁乳突肌诊断渐冻症的准确率在98%以上,后来被纳入中国渐冻症诊断标准。直到现在,骨科大夫做手术都会非常谨慎,会让神经科提前参与鉴别,这避免了让很多病人花几万元做完手术反而病情加重。
这次经历也让樊东升找到职业信条:科研应该是为解决临床问题而做的,应该给病人带来好处,这是医生价值体现的重要来源。
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樊东升就主要接诊渐冻症患者。现在,在他的带动下,北医三院神经内科有约四分之一医生参与到了渐冻症工作中,许多研究生专门研究这种病,毕业后又留在了这里。
北医三院是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运动神经元病工作组组长单位,因此,樊东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定期培训全国专家,使诊断趋向同质化,让更多“渐冻人”能在当地得到较准确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这种培训也为渐冻症新药临床研究培养了人才,因为如果医生搞不清楚诊断,把被误诊的患者纳入临床试验,会影响试验的准确性。
现在,樊东升每周出两次门诊,一次普通门诊,一次多学科会诊,他要将诊断尽可能精准到各种不同亚型,避免诊断不确带给患者精神惶恐和治疗贻误,同时努力探寻针对这个世纪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为《因为爱,所以坚持》作序时,樊东升写道:“于我,(走进诊室的)是又一位不幸罹病的患者;而于患者,则是人生旅途上一个猝不及防的拐角......成为渐冻症研究者是一项多么奢侈而沉重的幸遇。”
经济观察报记者问樊东升,如果有一天渐冻症被攻克,或者有很好的药物出现,你还想做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就想做这一件事(攻克渐冻症),没有别的了。”听到这个问题,樊东升笑了起来,他觉得未来5到10年里,找到一些对部分渐冻症有效的药物,让患者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病情在3年、5年甚至10年里变化不太大,不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在他的构想里,未来渐冻症会被细分成很多不同的亚型,患者可以根据亚型来选择最适合的药。就像托夫生注射液能对2%的亚型有效,下一个药可能就会对另外某种亚型有效,当一个个新药出现时,医生可用的武器就越来越多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