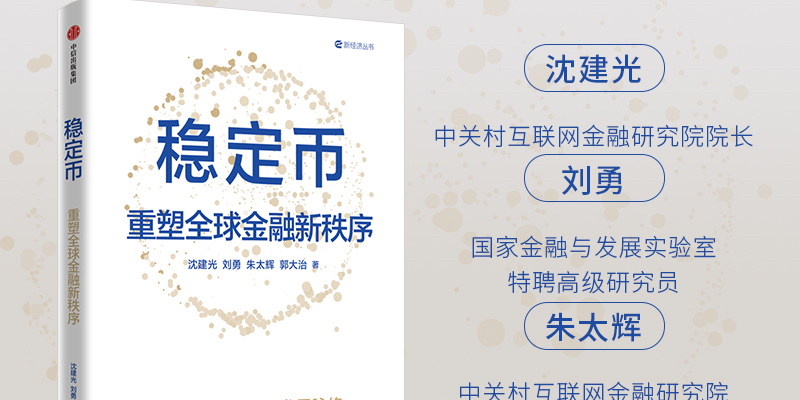
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经历深层变革的当下,稳定币作为加密资产与现实经济价值之间的桥梁,正迅速崛起为重塑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力量。尤其在2025年美国通过《天才法案》、中国香港颁布《稳定币条例》之后,多国纷纷跟进立法,稳定币不仅成为数字金融中的焦点,更被资本市场视为“金融的未来”。
在这一背景下,沈建光博士及其团队撰写的《稳定币:重塑全球金融新秩序》应时而出,系统梳理了稳定币的起源、业务模式、应用场景、风险挑战及全球监管态势,为读者构建了一套全面的认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为《稳定币:重塑全球金融新秩序》作序,他称这本书为“稳定币小百科全书”。
特此整理了李扬的观点,以飨读者。
现实的印证与思考:万物皆可“泛货币化”
客观地说,如今,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提供一个让大家普遍接受的货币定义。参照金融学教科书的定义,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定义的精髓是“一般等价物”,就是说,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定价标尺和交易中介;至于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定位,则显然需要与时俱进,因为商品货币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我以为,“一般等价物”凸显的是货币的计价和支付清算功能,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所有货币金融问题的方法论和基本路径。
历史上,凯恩斯对货币问题的研究有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凯恩斯系统地讨论了存款作为货币的存在形式问题。他指出,在现实情境中是贷款创造了存款,且大多数支付清算是通过存款在银行账户间“划转”实现的。由于存款是货币,且存款是商业银行的创造物,所以在我们国家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提出最多不同意见的当数商业银行,因为央行数字货币 ToC(面向最终消费者)的机制,冲击了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的机制,进而削弱了商业银行存在的根基。
第二,凯恩斯提出了“内生货币”的概念。货币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货币究竟有没有用”。
对于这个问题,向来有货币“外生”和“内生”两派观点——如果确认货币是“外生的”,则货币“无用”,其供给的增减主要影响物价;如果确认货币是“内生的”,就认为货币是“有用”的,因为货币是通过“贷款—存款”的过程创造出来的,而贷款不仅对实体经济有极大的影响,也对经济增长、利率和物价产生全面影响。
换言之,“内生货币”的理论构成当代央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就出自凯恩斯的研究。
第三,凯恩斯是黄金非货币化的拥趸,他主张货币应当“可管理”,其概念也应不断抽象化,具体可见他对货币的定义:“计算货币,即债务、价格;一般购买力所赖以表现的计算货币,是货币理论的基本概念。”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哈耶克,也对货币问题做过研究,且对如今加密货币频出的现象给出了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分析。这位“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认为:无论是谁,都能发行货币,关键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只要有人接受,发行的就是货币。这一定义凸显了货币作为信用的本质。
在哈耶克看来,没有必要在货币与非货币之间做出非常清晰的区分,需要研究的是被市场接受程度不等的一系列物品,如同我们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按流动性高低排序一样,这一系列物品被市场接受的程度会从高水平向较低水平递减,一直减至那些不能充当货币的东西为止。
大家不妨掩卷细思:从功能上说,不论是传统体制下的粮票和各类票证,还是现在我们随时随地看到的各种“积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都发挥了货币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都参与了“货币的创造过程”。
在前几年被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一书中,L. 兰德尔·雷也有一句十分简洁但值得关注的对货币的定义:“货币是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记账单位。”这个定义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在这里,货币被抽去所有的物理形式,仅仅留下“记账单位”的抽象概念。正是这种抽象概念,为货币的数字化打开了大门。
以上对几种货币学说进行的简单回顾,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货币及其创造并不神秘。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稳定币和“币圈”的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当然,作为货币经济学的研究者,我在各种非中心化的“货币”,特别是在稳定币的发展中,看到了货币消亡的技术基础和现实路径。
不存在“超主权货币”
有一种观点认为,稳定币是一种超主权货币,会对货币主权造成损害。
我们认为:货币作为社会经济现象,其本质是国家主权,这是货币的根本属性。只要世界还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货币的主权属性便不会被消灭,就不会存在“超主权货币”。
近年来,在货币方面固然有很多技术创新,但是都绕不开“主权”问题。
大家都看重稳定币的跨境支付功能,的确,稳定币使跨境支付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跨境支付背后还隐藏着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兑问题,大多数研究对此语焉不详。这也说明,论及跨境支付,货币之间的汇兑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举例来说,无论美国发行在技术上多么先进的“币”种,都不能直接用其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也都跨不过“汇兑”这个围栏;货币作为国家的主权载体之一,于此表现得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主要有两点:一是课税权,二是发钞权。这两项权力都是不能让渡的,失去任何一项,都会“国将不国”。
当然,问题还有复杂之处。我们反复指出:稳定币的主要功能就是支付清算,而支付清算又是货币的基本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币对各国主权货币制度是有冲击的。
前文说过,我国的业界和研究界过去不关注支付清算功能,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货币当局只在乎并严格管理两类事务:一是资金池,因为有了资金池就是商业银行,就必须按照银行来监管;二是可分割、可连续交易的借据,具备这个特点的借据就被定义为证券,也必须进入监管范围。
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仅凭借支付清算功能,就大规模切入货币领域,并对传统的支付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以说,我们后来的一系列清理整顿活动,乃至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都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稳定币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一国的货币主权,它是否构成走向超主权货币的必要环节,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货币是分层的”
稳定币是非常复杂的新事物,因此,对于它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开辟另一个视角,即货币的分层问题。
分层研究货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资本论》的第二、三卷用大量的篇幅研究金属货币、商业票据和纸币的混合流通问题,讨论票据清算所同商业票据这种“真正的商业货币”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层研究货币的范式,自然地,它们也是我们研究稳定币不可或缺的内容。
货币从来都是分层的,比如,按 M0(流通中现金)、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供应量)等次序排列并定期公布的央行货币供给,便是一个以流动性差别为标准排列的分层货币统计体系。
数字货币的出现使货币的“形式”日趋多样,也使货币的“分层”日益复杂。这就是金融学界将“金融”称为“上层建筑”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分层,居于最底层的都是那种“无交易对手方”的资产。这指的是其价值在体系外自行形成,构成一切交易的最终结算手段,不存在任何交易风险和违约风险的资产。比如曾经的黄金,现在的美元和人民币,它们的价值是自行决定的,其他货币都是它们的“借据”。
在金本位制下,第一层是金和银,第二层是商业银行发的汇票、其他票据等,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央行体制下,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因而“排他”地垄断着底层货币的发行权。
从本质上看,央行发行的货币是不需要交易对手方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固然给出了交易对手方,但那其实只是形式而已。
比特币、稳定币加入后,货币分层的情况会更为复杂,现在大家比较多地倾向于将黄金、美元和比特币列为第一层货币,这里“比特币”的功能类比黄金,堪称“数字黄金”,比特币存款、其他数字货币等是居于“货币金字塔”上面几层的货币。
稳定币只是在不断丰富的货币金字塔上增加了一层可以作为支付手段的事物而已。货币分层的理论十分重要,因为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各类金融创新活动;对于研究全球债务的膨胀问题,也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分析角度。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